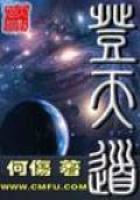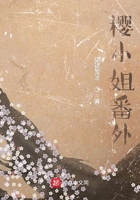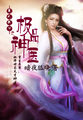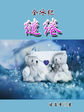如果从文化承传的角度看,这块高粱地对莫言的精神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先定的。这主要指的是“非典籍文化”(非文字文化)的浸润,是北中国那块特定地域所独具的乡风乡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神鬼传说、生产方式和生存景况等共同组构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定向遗传。也就是说,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个传说、一首民谣、一窗剪纸、一台村戏、一声号子、一缕炊烟、一点鬼火、一头牛犊、一条猎狗……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生具有某种别样的关联,它总是精心地保留着恒久的以往,并始终不渝地培植。
着未来,对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文化的浸淫与渗透。莫言作为一个受动体,还远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开始承受着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一种艺术创造的超前训练。他日后的文学母题、风格、情调和景观的形成与凸显,都不过是那种深长的文化积淀的外化罢了。“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和那“苦涩微甘的薄荷气息”浸透了莫言的灵魂,它们总有一天会在莫言的眼前辉煌起来,从莫言的心灵中荡漾出来,而成为莫言艺术世界一种悠长的情调和氛围。莫言也是深爱着这片土地的,无论它的美丽还是丑陋,辉煌抑或暗淡。这是莫言文化的根之所在,艺术的魂之所系。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幺在1985年蜂涌而至的外域小说大师中,莫言特别地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位“小老头”情有独钟?一一福克纳的“邮票说”对莫言的启迪是显而易见的,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对莫言营造“高密东北乡”的参照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拥有这样一块饱藏了独特文化意蕴的“高粱地”是上苍对他的恩赐。莫言是幸运的。
莫言又是不幸的。
说他幸运,是说他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文化(即乡土文化主要是“非典籍文化”)的天然产儿,因了高密东北乡那块高粱地的摇篮的滋养而发育得特别地健壮,说他不幸,则是说他为当代中国农民的一分子,其现实生存景况的窘迫和艰难给他童少年的心灵烙下了无数痛苦的印记。正当莫言出生的五十年代后期,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又开始陷入了政治风浪的颠簸,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直至“三查”、“四清”搞“文化大革命”,农民在政治上反复被愚弄,经济上不断被剥夺,发家致富的梦想终成泡影。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的莫言自然难逃厄运,还在少年时期,他就遍尝各种野菜,未及成年便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间种种惨痛的经历在他早期作品(如《枯河》、《秋千架》、《筑路》、《透叫的红萝卜》)中都有着最为真切的表述。
如果说物质的匮乏和肉体的重负对一个生性坚韧的少年来说还堪可承受的话,那么,精神的压抑和心灵的折磨对于一个渴望温情与爱抚的孩童就未免显得过于残酷与残忍了。少年莫言的精神压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治,来自于他的家庭的上中农成分。须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农村里的“上中农”是一个极其微妙又极其危险的阶级成分——你是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搞好了,你可以向贫下中农靠拢而成为依靠对象;反之,则可能成为打击对象,随时都可以把你升为富农,列入另册。因此,“上中农”都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悬悬乎乎如走钢丝的心态和过于谨小慎为的行为准则。莫言的家庭是这样,莫言的父亲就更是如此。他持身甚严,家教更苛,约束子女几乎到了“不准(在外面)乱说乱动”的程度。莫言自称幼时生性活泼,好说好动。这与他成年后寡言少语内向阴沉的个性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呵。塑造或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莫言来说,上中农成分压抑下的上中农的父亲无疑在无形中压抑和扭曲了他的天性。(而且据我的揣测,之所以如此,或许是有过现实生活中的沉重教训的。请想一下《枯河》中那个上中农之子小虎破了“家规”去和支书之女小珍玩耍,不慎闯下大祸,最后被迫自杀的惨剧吧)被这种“左倾”政治所扼杀的当然远不止是一个孩童的童趣和天真,还有人们之间的一种普遍关爱,甚至是亲人之间的一种基本情感。正如《枯河》的结尾所写到的,面对小虎的尸体,“他的父母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百姓们面如荒凉的沙漠”。“枯河”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人间温情的流失乃至干涸。也许比这个题目更具象征意味的还有小虎爬在树上时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画面:“他看到有一条被汽车轮子辗出了肠子的黄色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不见踪影”。一个弱小的生灵就这样无依无助,孤苦伶仃,身罹大难而处变不惊(甚至“也不叫”),视苦痛为平常,视生死若鸿毛。该让我们来悲悯它的麻木,还是赞叹它的忍力?作者在这里传达的是又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别无选择之后的无奈的认同?
《枯河》是莫言灰黯的童年记忆的一次艺术显影,也表露了他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直觉感知和把握。他是以痛苦为起点揭开他沉重的人生的帷幕,他的个体的人生体验的深度也就决定了他对巾国农民命运的把握的深度。如果说以此作为代价来看,这是莫言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当然,莫言最终是幸运的。这不是说他终究逃离了土地(并不意味着逃离痛苦),而是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痛苦产生艺术”,或如海明威所言: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也就是说:“愤怒出诗人”,“文章憎命达”,“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在一个优秀作家的身上,痛苦和艺术必定会呈现为成正比的能量转换。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喷涌,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掌握了解读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两把钥匙。更具意义的还在于,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将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势,终生影响和制约他的经验与思维。质言之,莫言在高粱地里一十年的生养劳作,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他此后文学世界的基本格局和气象。这要分三个层次来讲。第一,莫言作为自然之子,通过高梁地这个文化摇篮,毫无保留地拥抱或溶入丁深沉博大的农业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生生不息的艺术活力之根。第二,莫言作为农民之子,在感同身受了农民的苦难的同时,也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情感,包括他们的心态、思维、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等等,并终生不能割舍。从而使他获得了一个极其独特和宝贵的资格:农民代言人,始终代表农民自身对其历史和现实作出农民式的抒写和评判。第三,莫言作为缪斯之子,他的艺术个性和他的人格个性一样,都在乡村生活的磨砥中锻打完成。来自现实生存的全部的压抑造成他性格的双向逆反发展。一是压抑导致自卑,导致自我的龟缩,导致对强大冷酷的外部世界的逃避。(就像“红萝卜”里的黑孩儿努力逃离人世的困扰而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的心灵王王国里。“黑孩儿”不啻是少年莫言的自我写照——“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是压抑导致反抗,导致自我的膨胀,导致对道德的文化的现存秩序的英勇的反叛。(就像《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敢于蔑视一切人间法规而高扬自由生命的大旗)两点慨括而言,正是:物质的贫困培育了想象的辉煌,精神的压抑爆发为文字的张狂;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不平则鸣,一鸣惊人。遂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遂有汪洋恣肆的文体和语言,遂有惊世骇俗的审丑眼光、渎神精神和叛逆品格——遂有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一样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艺术世界。
最后再重申一点,本节开头以“右派”和“知青”作家切入乡土的视点来比较出莫言的独特,其实,把目光再放远大一些,扫瞄新文学迄今全部的乡土作家,就不难发现,像莫言这样从乡土中生长出来而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作家仍然是罕见的。在他身上当然也包含了农民的局限性(如狭隘的“中农意识”等,我将在后面谈及),但他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正在这里,他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农业文化和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绝好标本。他对中国乡土小说技术策略的革新也许正在被一些更加新进的作家所继续推进和完善(如一些“新写实”小说家),但他对中国农民的生命体验所达到的深度恐怕一时还难以被超越。
周涛:天山来风
虽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我在这里却不得不继续借用——因为它多少有利于我将周涛与莫言进行某些对比——如果说莫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块凝重的土地,那么周涛则给我们带来了一股飘逸的长风,前者得益于年深月久的淤积,后者则来自不同气流的对撞与交汇;莫言是纯正的农业文化之子,周涛则是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前者是根深叶茂的红高粱,后者则是随风而发的蒲公英……
周涛祖籍山西榆社“坂坡村”,出生于干部家庭,曾在北京度过几年少儿时光,9岁便随全家迁移新疆。像所有在都市度过漂泊不定的童年的人一样,故土的遥不可及所造成的家园感的缥渺与失落是他们的一般特点(譬如普遍不懂得一种“母语”——文言)。周涛也不例外。那么,和莫言相比,周涛的“根”在哪儿?
近40年的客居新疆,使周涛很自然地“反客为主”,他由衷地热爱这片土地,认同这片土地。将这片土地指认为自己的精神的归宿,他甘愿为这片十地的儿子。他不只一次颇为自豪地自我调侃为“西北胡儿周老涛”他也曾深情地宣称:“我记不清我最喜次新疆的哪儿。我在这儿活了30年以上,对它熟透了,你不能说你对你父母亲更喜欢哪个部分,是鼻子,还是眼睛,爱他们就是了,爱他们的一切,包括缺点和弱点。……她的一切,都和你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但是,新疆尽管可以是周涛现实的家和精神归依,然而究竟不是连着他祖先血脉的真正的“根”。1986年,当周涛犹犹疑疑地去到太行山绉褶深处那个“坂坡村”寻根问祖时,一下予就被一种“根”的神秘力量所击中(他4岁首次“回家”的种种场景和言行此时都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不就挺“神”的吗),浓得化不开的乡风,乡情和乡音就像久旱的甘露,滋滋地渗透他的灵魂,茫茫岁月千里关山造成的阻隔,瞬间就被血脉贯通。这次历时仅一昼夜的短暂寻访无疑给周涛的心灵带来了震颤与惶悚,他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领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平常话语后面的深文大意,并把它作为“题记”恭恭敬敬地抄录在为这次寻访而作的散文《坂坡村》的卷首:
“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或许正是从这一刻起,周涛才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一个根系于太行深处而长期跋涉在天山脚下的伊斯兰世界里的文化漂泊者。几十年来,恰是由于有了这个“根”(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还包括一个始终散发着山西老陈醋味的稳固的家,和日常接触的相当汉化的局部环境,都是“根”的外延)的维系。才保证周涛不被伊斯兰文化完全同化;而又是由于有了伊斯兰文化的比照,才更加显示出了这个“根”所包涵的文化意蕴的独特魅力。两者不可能彻底地合二为一,但却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发明,互相参照,互相吸引。周涛由此获得了奇妙的文化视角或优势。他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两种(西域和华夏,或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磨擦巾进行“嫁接”与“杂交”,既寻求遇合,更寻求差异——因为差异就产生距离,距离就带来审美的观照,和无数新鲜的发现…
和莫言以土著的身分歌唱本土的重要区别即在于,周涛并非土著(当然更不是观光客),而是始终和他歌吟的土地保持(并非人为地)了一种恰当的距离。正是因了这种“距离”。他才从许多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的大地、天空和雪山中看出别一样风景,从貌似平常的马群、帐篷和炊烟里读到另一种人生,一种沉重而乐观,坚韧而旷达的伊斯兰精神和草原文化气息。从而以《牧人集》、《野马群》、《神山》等诗集从一片毫无个性的颂歌声中突围出来,成为了“西部诗派”的重要开山之一。
与此同理,当周涛穿过30年岁月和五千里关山的时空距离重返“坂坡村”时,仅仅一夜之间,那无数深邃的记忆、精微的感受、奇妙的刺激、尖锐的发现和神思飞动的灵感纷至沓来,美不胜收。其原因盖在于一种“距离”——“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比我对这种僻远山村的古老文化更敏感、更感亲切。这并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来自新疆那样一个弥漫着伊斯兰文化氛围的西域,我虽非异国异种,却已在穹庐下一弯冷月的拱顶寺院下生活了三十年。”
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流,既因差异便于比较,也因距离产生审美。同样,它们的互渗会产生互补,溶合能催化新的共生。比如游牧民族天性的豪爽放达,面对严峻人生的战斗姿态,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强悍不屈的精神等等,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份值得永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精神财富。周涛就“毫无疑问地崇尚豪放派”,他说“我只能被它感动、击中,并且坚信这一脉精神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贵、最伟大、最值得发扬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文学性格。”其实这也是周涛的文化性格,而这样一种性格有幸在雄深辽远的西部地平线上生长,难道不会得到一种特别的、得天独厚的文化精神的浸淫、滋养和刺激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新疆,这块西域的神奇的土地,无论是作为人文地理还是自然地理,五十年代的红色政治将周涛全家放逐于此,都恰成了八十年代缪斯女神对诗人周涛的特殊馈赠,前者玉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契合了他的心理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