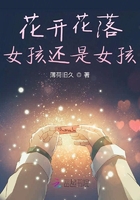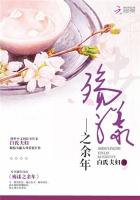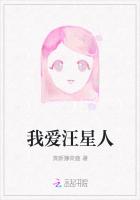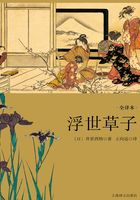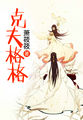巧合得很,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揣测和判断,朱苏进在1993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中篇新作《接近无限透明》,第一次在小说中动用了少年患病住院的生活经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作家自传来读,但作为作家少年时期的一段情感或心灵历程的披露,我却宁可信其真而不愿信其假。尤其小说中的少年“我”的住院遭遇又是那样的奇特和不平凡——其中有两件事恐怕是最为要紧的:一是“我”与小病友兰兰因同看太平间而导致夜间的恐惧,因恐惧而合床睡觉,遂遭到护士的误解、喝斥并被粗暴拆开;二是“我”为那个狂人、超人、众人眼中的精神病患者李觉所迷恋、所吸引、所点化,从崇拜始,经过“双重误解”,而遂以相互伤害终。这两件事中都有一个核心情节就是“误解”,而且都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对于孩童的误解。也许这种误解都是根据成人世界里的一般逻辑正常推导出来的善意的误解,但它对于一颗“接近无限透明”的童心来说却是十分残酷的,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伤害甚至是终生难以平复和弥合的。就像作者借李觉之口所说:“在你现在年龄段,可塑性最高,挥发性最强,心灵嫩得跟一团奶油似的,谁要是不当心碰一下你的灵魂,他的指纹就会永久留在你的灵魂上。”在此一阶段,少年初涉人世,不谙世事,来自人世间的每一个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每一份真诚、友情和爱心,每一次欺诈、虚伪和阴谋,都会成几何级地无限放大,就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他明沏纯净的心的天空,留下浓重的蘑菇云,久久不能消散。
就在这样的阶段,“奇人”李觉深深地进入了少年“我”的世界,他超凡脱俗的智慧、才华、激情与气质,都彻头彻尾地征服了“我”,使求知若渴的“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全部地对他进行接纳。尤其是他的纯真和童心,使俩人在“接近无限透明”的境界中达到了溶台。然而这种不含一丝杂质的童心交往却不为成人(亦即世俗的)世界所理解与接受,他们指认李觉为“神经病”而阻止“我”与他的来往,于是“我”成了人们伤害李觉同时也是自伤的一件“利器”。在“我”眼中(其实也是在朱苏进眼中),李觉当然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只是他的近乎孩童的透明与单纯、本色与自然,和世俗格格不入罢了,于是,在那些“成熟”了的其实是真正有些病态心理的人们眼中,他才显得仿佛有些病态。毫无疑问,李觉式的人物,李觉式的自信、弧傲的个性与气质,深深地浸透了少年朱苏进的身心,而且成了他此后笔下的基本人物原型或人物的基本个性与气质。《接近无限透明》是朱苏进对“李觉”的一次深长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美好孩童时代的一曲挽歌。
我之所以侧重从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接近无限透明》这样一部艺术上也许并不十分优秀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仅仅是因为朱苏进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文本只此一个,确实弥足珍贵。如果企图得出更加贴切、可信有说服力的结论,恐怕还有待于作家贡献更多的可供阐释的同类文本。不过仅此一个,也足以帮助我们根据“少年患病”的一般情状,对朱苏进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少年天性最好幻想而酷爱自由,可一旦染病在身就不免要与床榻为伴,孤寂独处,形影相吊,划地为牢。如此一来,物理空间的收缩势必要刺激心理空间的扩张,也就是说,行动的拘谨反而导致了心灵的加倍自由,孤独使幻想更加辉煌。(这也是一种“绝望中诞生欲飞”吧)此其一。其二,少年患病而又长期住院,就等于提前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在一夜之间变换了“角色”——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的“角色”了,既不是学校里的学生,也不是家庭中的孩子;他只是一个病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周围的病友们是平等的。在这里,小孩的角色意识被削弱和淡化,他必须努力提拔自己,学得“少年老成”,以便“平等”地和病友们打交道。而与此同时呢,病友和医护人员们仍然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在他面前往往不设防,不存减心,不戴面具,最容暴露出真性情,真面目。他由此获得了一个观察人生与进入社会的特殊视角与通道,他从中感受了真善美,也领略了假丑恶,尤其从一个纯真的少儿目光出发,那些人性中的根本弱点部分也许更加让他触目惊心,从而一下予洞穿与抵达人的本质。他就在这一点点发见中成熟与成长,直到褪去童真,冷酷地直面人生。那些“发见”与感悟虽然深埋心底秘而不宣,但对他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朱苏进在《接近无限透明》中所感叹的:“心里老搁着一团隐秘,……我们正是凭借那种东西才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的,它跟酵母一样藏在身心深处,却澎涨出我们的全部生活”……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朱苏进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逐步确立起他介入人生(和此后介入艺术)的基本姿态:一方面是冷静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是遴狂的幻想主义,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孤独的冥想者”。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以一个少年好奇而又早熟的目光,多疑而叉坚定地直面人生,探视与揣测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养成了“凝眸”洞观的习惯,和锐利得不无几分刻毒的“第三只眼”,察人观物远比常人来得更为犀利、透彻和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十分防范别人窥破自己的内心,讲究收蓄与内敛,自我设肪,自我封闭,喜怒有度,“引而不发”。使人很难穿透甚至接近他的内心世界,他拒绝交流与沟通,连朋友也不例外。这实在是一种对人的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和对自我质量的高度自信。现实世界中的孤标傲世,常常导致精神领域里的孑然独行,他不得不去寂寥的心空中高张起冥想的翅膀,在一种自足的封闭状态里实现幻想的辉煌——那也是一种“病态”的辉煌。一种“自恋”形态的辉煌。
16岁(1969年)的朱苏进带着将率的梦想、孤傲的个性和幻想的气质,去到福建海防当了一名炮兵。这对手文革中期的军门子弟来说,实在是别无选择中的最佳选择。它既回避了“上山下乡”的大潮而解决了“出路”问题,又在“子继父业”(或“望子成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作了一个直捷的沟通。然而,它对于心性和憧憬都高薄云天的朱苏进而言,却无疑是踏上了一条充满幻想的幻灭之旅。一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产生将军的年代(取消了军衔制,也没有了名义上的将军),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和平无战事,更由于它本身的全部的畸形决定。它甚至不能容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正规的军人素质养成,更遑论其它?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红色政治”充斥在每一缕空气中的非常岁月,整个军队都在“突出政治”的高调下高速运转。人人激进,人人自危,而人人都呈显出某种心理和精神的真正病态。朱苏进就好像刚刚从—个生理的小病院又来到了一个精神的大病院,他尖利的“第三只眼”常常轻易地就洞穿了谎言下的真实,窥见到了人们心中的“病灶”,体验到了荒谬年月里整整一代军人的心灵被压抑被扭曲的沉甸甸的苦痛。这是军旅生涯对少年朱苏进的一次人生洗礼,也是对作家朱苏进的一份“文学馈赠”。作为这份“馈赠”的另一部分,则是扎扎实实的军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从朱苏进入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整整7年他基本上都是在炮兵连队度过,当过炮手、瞄准手、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和副指导员。也就是说,7年中当过连队三级(班、排、连)领导,摸过炮兵各个行当。这样一分履历在全军专业作家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朱苏进日后建构军旅文学世界最初的一块坚实的奠基。
当时的朱苏进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家的梦想比将军的梦想对朱苏进来说可能更加遥不可及(他毕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一切梦想,你只有遵循现实的法则,打掉傲气,夹紧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好兵。然而,倚门弹铗的感慨却不肯在心中平息,梦幻破灭的结果是催发新的更加迷人的梦幻。在梦幻中可以舔心灵的创伤,可以加倍爱惜自己的羽毛,可以“自恋”般地臆想和放大出一个个超人般的自我去和现实对伉。当这种美妙的、栩栩如生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梦幻”再也不甘于偏居心之一隅而要呼之欲出的时候;当这种“梦幻”通过文字公诸于世成为可能甚或是需要的时候一一尤其是当这二者不期而遇的时候——(这时候是1977年),朱苏进终于握起了笔,毅然地弃武从文,选择了创作。这种军旅人生的最终归宿肯定违背了朱苏进少年从军的初衷,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主要不是文学艺术长期薰陶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而是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人生突围,一次“绝望中诞生欲飞”的背水一战。朱苏进走上了这条路,并且一步一个台阶稳健地登上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高峰,他所依赖的和他所创造的主要是两个军人:一个是冥想中的未来时的将军,一个是现实中的过去时的士兵。这是两个非常独特和孤傲的军人,这也是两个非常优秀和地道的军人。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朱苏进。本章小结:平行比较中的“交叉比较”。
写完本章,分别对“三剑客”文学之树的“根”和“冠”作过一番发掘和描绘之后,似觉意犹未尽,忍不住还要打破本文一般平行比较之体例,再来作一点必要的“交叉比较”——
如果说莫言的奇诡狂怪汪洋恣肆有如天马行空,那么,周涛的豪放不羁旷达潇洒则好似牧马人,而朱苏进的凝重内敛沉郁深刻就极像罗丹雕塑之“思想者”(笔下表现为一种有劲道有张力而又有控驭有节制的紧张感、焦灼感与冲突感,他八十年代早、中、晚期三个阶段六部代表作品标题颠倒组合而成的句式最能反映这种风格:“引而不发”“射天狼”;“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欲飞”)。
如果说莫言是来自传统而又重在反传统、亵渎传统与颠覆传统,敢于在文学的神圣殿堂里撒野放泼,蔑视规范冲决制约,把内容和形式都推向极端,有一股子“造反有理”的“蝎子窝里捅一棍”的邪乎劲和野蛮性,充满了磅礴的原生的活力与魅力,破坏性同时也就是他的创造性。那么,周涛、朱苏进则更“老实”和“正统”,矫枉而不过正,放纵而“不逾矩”,显出了一种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全部人文“教养”的内在规范与制约。
三人之中,周与朱的相近点更多一些,他们的出身大体相同,都可归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有一种认同与崇尚“贵族”(或曰贵族精神或日高贵气质)的意识或潜意识,向往与标榜一种“超人”精神和王者风范。他们都恃才傲物,睥睨群庸,只是“傲”的形式又各有不同——周是傲得狂却率直,朱却做得狷且矜持;周虽傲,但承认别人倒也来得痛快,朱却显得不无几分悭吝;周曾在口头或文字中不止一次称莫言为“天才”、“奇才”,朱对莫言的评价却要审慎得多,最积极的推崇也不忘设定一个前提。
三人之中,真正“互文评论”的文字只有一篇,那就是朱苏进评周涛散文集《稀世之鸟》的《自然之子的痴笑》。这是一篇很漂亮的赏析文字,不仅表现了欣赏者卓越的才华和准确的眼光,更见出了一个作家鲜明的个性。——朱是这样感觉的:“这次一路读下去,舒服得就像自己在写这些东西。它们嵌入我的精神缝隙里,并且不刺痛或者涨破我(在读一些大作品时常有那种感受)。我相信《稀世之鸟》是属于周涛这一代人的小书”……后面又说“与卓越作品匹配的只能是卓越的欣赏。”云云。可以说,朱苏进如此动情地承认另一位作家(尤其是军内同行),实在难得。但请注意两点:一,这个“承认”不过是认同周与自己“等高”或“与已相当”罢了(“就像自己在写这些东西……并且不刺痛或者涨破我”——刚刚好);二,虽然承认它不错但也并非“大作品”而只是一本“小书”而已。——朱氏其个性其傲气何其昭然,和周氏又何其相似乃尔。
此文中还有一个颇有意趣的话题是朱苏进谈“刻薄”,不经意间谈到了他们三人的一个共同点。朱苏进说周涛——“他太刻薄了(说成锋利也行)……我感到他有点玩弄刻薄和赏识刻薄”……这又何尝不是说朱苏进自己,不是一种“夫子自道”?朱苏进还不够刻薄吗?就比如该文中他指出周涛进入了人生之秋——“他身心都已归属秋天,再多的收获也不能消除年华逝去的哀惋……”这可真是洞穿肺腑的知音之论,也确实是击中要害(“心灵最柔软部分”)的“诛心之笔”!周涛读至此,真该“默读数遍,举首望天”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刻薄就是一种才华,朱苏进在这里欣赏周涛的才华也包括欣赏周涛的刻薄,或者干脆说是自我欣赏,他从周涛身上照见了自己,他俩各自以对方为“镜子”互相欣赏(周涛欣赏此文,以后就以此文作了《周涛自选集》的代序)。刻薄就是他们才华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刻薄常常是一种机智,一种锋利,也是一种深刻。善于刻薄敢于刻薄尤其是敢于承受刻薄的人,往往都是心智聪颖健康性格强悍而自信的人。莫言难道就不刻薄吗?——
当然,莫言无疑是一个刻薄大师,他的刻薄往往机巧、幽默并且犀利。但他与周、朱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刻薄常常是对着自己来的,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出现并完成的。他其实是以自嘲来掩饰自悲,以自傲来遮盖自卑。他的自信心远不如周、朱的那么纯粹、坚定和强大,白马非马的邪劲也好,天马行空的狂气也罢,都有些故作傲姿和狂态,有些夸饰和提虚劲的成分。他对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抗拒中又不无觊觎和向往,耿耿傲骨的内里始终难以摆脱一种起于荒野来自土地的感伤与悲凉。因此,他的情感世界更浑沌、更迷茫,更矛盾,也更复杂;也因此而更丰富、更广大、更深邃也更多层次。……
下篇:“三剑客”现在行进中的困境与突围
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
开写本节之前,我得首先声明,前此我对莫言分析研究的依据主要来自他1985年前后的创作,即从《红萝卜》到《红高粱》约20部中短篇。至于对他此后从1987年的《欢乐》、《红蝗》迄今的多量创作,我一直保留看法,而且由于种种文学和非文学的原因,也始终无话可说。时至今日,当我试图对“三剑客”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正处于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了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