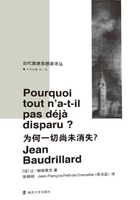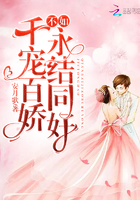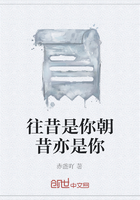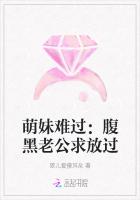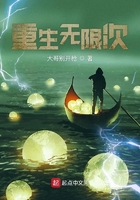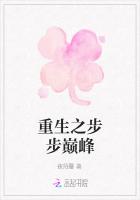即使以张之洞《增设洋务五学片》(1889)为开端,与义理考据辞章的制义贴括旧学相区别的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也已逾百年历史了。但“人文学科”一词确定地进入汉文献,迄今仅十余年。据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统计,大陆最初一批人文学科理论文献为:顾晓鸣《“人文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刘少泉《人文科学要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未定稿》1987年第1期)。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人文认识”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笔者1985年酝酿这一课题时曾与《青年论坛》主编李明华通信,得悉李泽厚在该刊创刊号(1984)卷首语中已使用了“人文学科”一词;而李氏《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981)中也早已使用了“人文科学”一词。海外虽早有唐君毅《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际》(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但从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与余英时《文化建设私议》等文来看,人文学科观念在80年代台湾尚处在启蒙阶段。香港虽早通行“humanities”一词,但从张灿辉《人文与通识》(香港突破出版社1995年版)中可知,直至90年代,汉语“人文学科”仍是香港学术教育界探讨性课题。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对比。
诚然,现代人文学科并非指与史学、文学、经济学、化学等并列的学科实体,尽管它传统上依托于文史哲诸科,本质上却更呈现为一种学术观念论,即“人文”角度的学术价值观与方法论,或者说,是对科学一学科的意义域阐释。详参“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一节,尤西林《有别于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理论也因此以反思性姿态晚出于科学发达数百年之后。
但如果撇开唯科学主义(scientism)长达四个世纪(16—19)统治的国际背景,人文学科观念在中国迟至20世纪末叶才获独立这一史实,仍有特殊的中国社会文化缘因,它包含着20世纪中国学术一个根本性教训。
二
毋须赘述,如学术界一再指出的,民族危亡与由此导致的科学救国,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的契因,而且是支配中国现代学术最有力的方向。随着从器物、制度向文化深层的推移,20世纪初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已不止于形下之物,而明确地尊奉为普遍有效的方法论与使人自由的价值论。从而,唯科学主义作为文化哲学思潮,其本身已具有人文功能意向。用1923年科玄论战中任鸿隽的著名论断来说,“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但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此即一方面否定了人文学科知识形态的可能性,一方面又以唯科学主义承担了人文价值观。
科学固然有其人文意义。对于迄今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不仅科学的效果力量,而且科学所陶冶培育的人文精神气质(理性等),更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但唯科学主义不仅视人文意义为科学派生物,否认有以人文为主题的学科知识形态,而且用狭隘的科学文化取代了丰富多样的人文内涵。
正是这种基于特定时代潮流的唯科学主义,使中国现代学术自始即漠视人文学科视域。尽管张之洞已以新学为参照,对中学做朦胧的人文阐释,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尽管耶教中译数量远远大于科学译著,李提摩太已向国人把西学区分为“治神心”(宗教人文)、“治人”(社会科学)与“治物”(自然科学)(《教务本末》下);尽管章太炎也已以新学眼光对中学作“客观之学”与“主观之学”的分类(《诸子学略说》);尽管王国维强调了哲学在学术科学中的指导性地位(《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甚至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援引西方现代人文思潮,为人文学科争一席之地而开科玄论战;范寿康把科学区分为规范科学与说明科学……但终究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文学科观念。
然而,单凭唯科学主义自身并不能阻遏人文学科的发展,科玄论战作为平等的学术争论,反倒刺激了其后人文学派在北京大学的聚集与发展。唯科学主义的扩张意向受到两个限定:
(1)唯科学主义尽管自诩为“科学的人生观”,但由于它根本上否认人文观念作为独立学科与普遍有效知识形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而,唯科学主义只是在人文类型之一的科学精神上关涉人文意义域,并不能涵摄人文学科功能。
(2)唯科学主义即使像梁启超称之为“霸王”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逞雄中国近30年,但依然局限为学术思想观念,而不享有政教合一的权威。
这最后一点攸关包括人文学科与科学在内的现代学术兴衰。
尽管有唯科学主义这样的偏颇潮流,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学术却享受着本世纪少有的思想自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思潮迭出、百家争鸣的活跃时期。思潮自由鼓荡积淀为学术建设,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中央研究院(1928)、西南联大(1937)成立为标志,20年代后期至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引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却恰是内外战争动乱最剧烈的时代。
这一对比现象与周朝解体、天下大乱的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汉末战乱分裂而自由超逸的魏晋人文精神有重要印证之处。它们都表明,学术之消长,主要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却与某种大一统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内在控制直接相关;上述三个时代又都似乎表明,这种大一统的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废弛,正是学术繁荣的有利条件。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其处于专制型意识形态更替之际的真空阶段有着重大关系:数千年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教纲常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终于失去支配人心的效力,而新的意识形态权威在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分期论战后虽获主流思想地位,却因辛亥革命后数十年军阀割据的政治权力多元格局,而未能获得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所必需的中央集权条件。从而,未曾停歇的内外战争,反倒成为延撂权威型意识形态统治的学术生存条件。
唯科学主义虽也被称作唯科学意识形态,但如前所述,由于它无法涵摄人文学科,便即使纯就思想而言也达不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权威。但唯科学主义与其后建立的唯物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却有叠合之处,这就是郭颖颐在其《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末尾所暗示的,唯科学主义自身无法统一多元竞争,但却“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美〕郭颖颐(D.W。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这才是现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最为严重的负面涵义。
三
科玄论争后期加入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基于科学专业背景的一般唯科学主义,而是将科学与人文价值乃至万事万物均统摄于自身,类似于古希腊知识王的泛哲学,但当陈独秀宣称,“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时,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1923)。这种实质由第二国际学派所塑造流播的唯物史观,参阅〔南〕弗兰尼茨基(P。Vranicki)《马克思主义史》及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等有关分析与批判。在以对象性客体之“物”为本体及因果决定论方面,却与以牛顿力学为原型的19世纪唯科学主义有重要共同点。唯科学主义从而引导出唯物的科学主义。
唯物科学主义把康德划界区分开了的(现象界)科学与(本体界及人文学科领域)形而上学重新混同一体,并且以类似古代自然本体论的框架,对全部学术作出既是科学知识名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规定。但它又并非古代的“超科学”(Metaphysics),而是以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为立场,将人文价值还原为科学因果律,即取得唯科学主义无法达到的统摄人文价值的最高权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他一切知识部门所业已达到的成就的科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哲学”。〔苏〕阿历山大罗夫(AF.Φ.AлkcangpoBa)主编:《辩证唯物主义》,马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3页。在这里,柏拉图式的传统最高人文理念—理想(idea)以科学理性逻辑(logic)形态出现,这就是权威理念型(而非一般观念型)的“意识形态”(ideology)。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关于“意识形态”广狭两义的说明。作为人文哲学,它依归于科学;作为科学,它又是僭越人文价值本体的旧形而上学;但它既非科学也非人文学科。这种经过20年代科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唯物科学主义,终于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学术的权威意识形态。与限于社会哲学的三民主义相比,唯物科学主义因其“物”的普遍抽象性而拥有前者没有的本体论,这是二者虽均为现代中国意识形态而仍有强弱之分的哲学根据。
这种权威型意识形态虽因战争而暂未建立统治,但仍可凭借军事组织权威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干预学术。在延安整风、上海与重庆文化论争中,“人性论”“主观论”反复成为靶的,表明了唯物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首先是亦主要是对人文学科的垄断,即排除意识形态之外任何独立的人文价值观念。1949年建国后,以革命胜利所赢得的中央集权巨大威望为后盾,终于演进为政教合一的极端意识形态,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在此垄断下,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基本成为意识形态的注释,仅在有限的实证与史料领域保持着边缘独立。几乎全部意识形态运动,从“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心”与“物”关系,到道德抽象继承论、文学创作“中间人物论”、形象思维论……全属人文学科批判。由于“权力的无限性依赖于以意识形态为中介的意义理念的无限性。因而,本体论乃至任何基本原理性的研究都攸关权力统治根基而被垄断。这类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域成为只有少数意识形态权威可以进入的禁区,任何独立思想者都客观上成为对教化垄断亦即权力本身的挑战。”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极端意识形态此种高度的垄断(同一)性,反过来铸造了意识形态化的人文学科观念,以至在后意识形态的20世纪90年代,大陆思想界依然将新生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加察辨地疑虑为传统意识形态的保守遗产,而与人文精神相关的理想主义、本体论,也被染上意识形态色彩而归入消解之列。
专制型意识形态同时也垄断了人文学科对科学意义背景的阐释。人文学科基于自由创造与系统整体目的价值对特定科学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引导拓展,被扭曲为专制型意识形态将一己褊狭涵义膨胀为伪意义而对科学的独断论裁定。诸如指控马寅初计划生育论为帝国主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斥摩尔根遗传学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甚至宣判心理学为唯心主义而取缔心理学科……专制型意识形态对科学的这种粗暴干预,也败坏了科学界心目中的人文学科形象,至今学术专业界对超越具体经验实证的人文意义阐释仍抱有深层的轻蔑与厌恶。
20世纪中国专制型意识形态对人文学科与科学的这种双重垄断压制,与古代儒教伦常既收摄超越性形上学又束缚经验科学的传统格局有重要相仿处。参阅“实学与本体论”一节。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明清实学当年以心性人文之学为靶的而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对立,却未能将批判矛头指向双方背后共同的压制者伦理纲常,这一混淆再次出现于90年代科学与人文学科、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格局中。
然而,不仅对于唯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的20世纪中国,而且对于几千年政教合一与世俗主义的封建中国,形上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及其学术形态的人文学科,都是未曾独立的有待建设的新事物。
四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产生独立的人文学科观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②参阅“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一节。除过西方人文学术思潮(同时包括19世纪末的物理学革命所开启的与人文互补统一的现代科学观念、对技术经济非批判发展所引发的世界大战、能源、生态、公平等问题的反省)影响之外,中国本土契因至少有以下三项:
(1)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必然引向作为技术背景的科学精神与文化哲学。80年代,“当改革实践从经济、政治扩展到文化心理领域并意识到人自身现代化的必要性时,也就向理论提出了不仅有别于自然科学,而且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的地位问题。”②
(2)社会转型与中外交流加剧形势下,对不同发展模式与文化模式的人文价值评判与选择。20年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是从此角度首次提出人文问题的,但尚属文化哲学而未进入学科学术规定。80年代文化讨论在更为深广的规模上再现了这一人文选择的历史哲学意向,并从学术建设角度提出了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
(3)以反省“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质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批判消解,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两种表面似乎不相关的思想方向:一是重倡实事求是,否定教条理念的先验地位,代之以经验性与操作性的实践;二是通过研讨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兴起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将第二国际与斯大林视为科学定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为批判与引导近现代科技文明的马克思人文理想主义。这两种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与定位。前者解放了专制型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科学,后者则提供了人文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种超越性的人的本质观念。双方共同进行了类似康德式的划界,从而如同康德终结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也开启了政教合一的专制型意识形态的消解时代。
从而,马克思人文理想主义的意义与地位空前突出了。在科技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一体化日趋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面临现代与后现代反省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在摆脱了专制型意识形态传统之后,若不愿消解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或民族主义,那么,批判与引导现代文明的人文文化理想主义,将是时代亟须并且依然不可逾越的一种定位。
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人文理想主义,便从专制型意识形态中剥离出了人文学科,同时意味着放弃对科学的独断论控制。这表明,人文学科的独立,既是20世纪末叶文化思潮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又是专制型意识形态解魅,从而解放学术科学的前提性环节。
五
但人文学科与科学相区分,并从大一统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并非要重蹈唯科学主义而执著为一种反科学的“唯人文主义”。
诚然,作为当代人文主义,20世纪末叶兴起的中国人文学科观念,并非文艺复兴时期针对神学的世俗人文主义,而主要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庞朴发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1985),试图立足现代学术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缺点是囿于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观念而突出了与僧侣主义的对立。但后者在狄尔泰以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中已转化为建设性资源,并构成反拨唯科学主义的重要一维。但唯科学主义并非科学,相反的,如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所强调的,科学并未从唯科学主义中受益。〔美〕郭颖颐(D.W。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2页。70年代末与人道主义同时兴起的科学观念与方法论热潮,恰是消解专制型意识形态的互补的两翼,二者关系不仅不同于20年代科玄论战时,也不可与西方人本主义同科学主义的对立简单类比。
科学技术作为人作用于物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亦即人文主义的感性载体。现代人文学科正是在对科学的反思关系中,亦即对科学局限性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规范、引导与拓展中才确立自身的职能地位的。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孤立自在的人文学科。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文学科尤其如此。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从不缺少人文意向,但在引入近代科学之前,只有以封建伦理为轴心实体的旧学,并不存在具有独立学科对象、方法与功能的人文学科观念。中国古代学术在20世纪被突出地阐释为人文主义文化,但无论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思想家,或是从梁启超、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的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此种阐释的前提都恰是近现代科学以及对之反思的现代人文学科观念。
“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一基本现象。新康德主义将康德的知识论从科学扩展向人文文化,由此开端的对“人文知识”的追求,其内在矛盾张力在胡塞尔标榜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现象学的人文科学建构中达到顶点。现象学彻底而绝对的本体论究问,却以对科学概念的悬撂消解为前提。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都强调现象学不是知识体系而是运用中才自明的方法,却都留下了不同于作为方法现象学的煌煌现象学学(即关于现象学的学术)。参阅“回到事实本身”一节。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形态,应既区别于天启性蒙昧信仰,又区别于专制型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话语。这需要同时发展作为人文学科内在规范的形上超越性的人的本质观念(一种既超越动物生存又超越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性观),与作为人文学科外在规范的客观知识形态。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特性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规范》,《文史哲》1995年第6期。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在消解西方自身唯认知主义传统时曾一再倾慕东方传统文化,西方汉学家近年来也不断有人建议中国人文学科放弃西方知识形态话语而返回中国古典感性直观形态。参阅〔德〕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中国美学与康德》(《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等,有关反应争论参阅“纪念宗白华、朱光潜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纪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会议纪要(《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此类来自西方当代文化的诱惑,使中国本土学术更易忽视自身缺乏客观知识形态的传统弊病。因此,注意“人文科学”的知识形态建设,在以人文价值引导科学时与之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是基于自身历史现状发展中国现代人文学科时尤需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