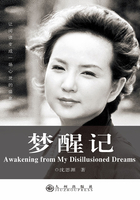§§第三编 文学民族意识与人民意识的张扬(1937~1949)
1937年到1949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战争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土地也就被分割成多种板块、多维空间。其中,主要有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及早已存在的港台地区。活跃其间的文学,自然也就称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及港台地区文学。这些不同地区的中国广大文艺家,“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结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这些不同地区的中国广大文艺家,努力贴近现实社会人生,突进生活密林,强烈地感受着与把握着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时代脉搏,个体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追求融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追求之中,民族意识与人民意识获得程度不一的张扬。由此,这些同一天宇下的不同地区的文学,构成为一个文学整体,共同支撑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大厦。
第一节 现实主义和“主观论”讨论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自救自强、自立自主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投身于这一大时代洪流之中的中国广大文艺家,为着有助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和文学自身的建设,对“文学和人的关系”进行了调整,自觉地开展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理论与文学创作问题的多次讨论,促使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理论的深入发展,并形成体系。以国统区文艺家为主所进行的“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民族文学运动”、“文艺政策”、“民族形式”、“主观论”的讨论,便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这六次文艺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一点即在民族意识与人民意识高扬氛围中,如何对待和构建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理论体系。
“暴露与讽刺”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文学与现实社会人生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1938年到1940年间的“暴露与讽刺”论争,是围绕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展开的。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只做“救亡要人”不做救亡实际工作、包而不办的“抗战官”华威形象,旨在暴露与讽刺抗战阵营中的黑暗面和剥蚀真正抗战力量的负面势力,显示出强烈的历史真实性与政治倾向性。这一具有主题题材的及时性与尖锐性的小说的问世,引起了广大文艺家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他们或认为“暴露与讽刺”有利于抗战;或认为“暴露与讽刺”有损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且易滋误解;或认为“暴露与讽刺”的对象应是侵略者与汉奸,否则“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通过论争,大大强化了广大文艺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认识与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把握,几乎一致认同于《华威先生》代表的文学创作方向,肯定“暴露与讽刺仍旧需要”。那么,文学创作如何去“暴露与讽刺”呢?讨论中涉及到了两个颇有深度的理论问题:一是典型问题,一是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问题。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暴露与讽刺》等文章中,从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及文学作品社会功能效应等角度,阐明了塑造典型人物和作家主观情感倾向对创作“暴露与讽刺”作品的重要意义。周行在《关于枙华威先生枛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等文章中,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角度,强调在创作“暴露与讽刺”作品过程中,作家主观的决定作用:向生活肉搏,不旁观,不浅尝辄止;作主体的把握与批判;从黑暗中看出光明。同时,他还认为,应究明暴露对象产生的根源,加深与光明的对照。这些具有一定深度的现实主义理论见解,不仅回答了《华威先生》问世后引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它是否有损于抗战,是否会使读者悲观丧气,填补了怀疑乃至反对《华威先生》这一创作方向的人“足供藉口”而留下的理论空隙,也有力地引导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沿着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政治方向和开放的现实主义道路纵深发展。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思想理论论争中,多次论及的问题。1938年12月到1939年间,围绕“与抗战无关”论展开的论争,便是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一场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就是文学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战争的关系,即与之结合,为其服务。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别无他途的自觉选择。因为“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但是,就在这一文艺大潮形成之际,梁实秋从自由主义文艺观与纯正文学本体论出发,在其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的《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梁实秋告辞》等文章中,提出并坚持文学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的主张。与此同时成都、昆明、上海“孤岛”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学意见。这一易于产生误导效应的文学主张,在文艺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形成批判浪潮。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家茅盾、老舍、胡风、罗荪、张天翼、宋之的、魏猛克、沈起予、金满成、陈白尘、黄芝冈、潘孑农、张恨水、何酩生、巴人等人,纷纷著文批驳。他们或指出:现实生活既以民族解放战争为轴心而旋转,文艺家的创作对象和创作态度就无法不在某一限度上和战争相关了。战争的命运规定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战争要求于文学的是打退一切反战争的甚至与战争游离的主题。或由此而责问梁实秋:不叫人把抗战文学写好,反叫人写点不抗战的文学,是何缘由?或严厉指出其危害性: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阻抗战文学之发展,关系甚重。这场文艺论争的发生及其得失,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中有过简要而中肯的论述,他说:战争以来,由于政治任务过于急迫和作家自己过于兴奋,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或概念化倾向滋长了。但有人却以为作家一和政治任务结合,只会写出“抗战八股”,倒不如写些“与抗战无关”的“轻松”作品。这一理论马上受到批评,而且败退了,但问题的解决却不能不是对引起这种歪曲反应倾向的反拨乃至克服。
1940年到1943年间,围绕“民族文学运动”展开的论争,是这一时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又一场重要论争。“民族文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铨和林同济,在其编辑的《战国策》杂志与重庆版《大公报》副刊《战国》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民族主义,高张民族文学大旗,以期增强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之目的。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主张,其职能是“个人意志的伸张”与“政治组织的加强”两个矛盾潮流之间的桥梁与调解人,使“人们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牺牲个人,保卫国家”。他们根据这一民族主义政治观,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战国时期”,置身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欲取得胜利,必须“以战为中心”、“一切皆战,一切为战”,必须“与乎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必须奉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一切政论及其文艺哲学作品,皆不离此旨”。陈铨在《民族文学运动试论》一文中,说得已甚明白,他说:要完成这一政治任务,需要文艺来帮忙,民族文学运动即为此应运而生。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一文中,反复哀告“弟兄们”写“恐怖”、“狂欢”、“虔恪”三道“母题”,意在表达一个意思即“把整个生命无条件地交出来在兢兢待命之中,严肃屏息崇拜”“领袖”。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等多幕剧作中的主人公,个个都是“牺牲自己来帮助领袖完成伟大的事业”的“英雄”。这一涂上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唯实政治”与“尚力政治”观和文学观及文学作品,自然为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众多文艺家所不容而受到严厉批判。茅盾在《时代错误》一文中,指出他们“犯了时代错误”,代表了一种危险的倾向。汉夫在《“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等文章中,认为他们的“立场和精神完全是希特勒的法西期侵略主义的应声虫”。欧阳凡海在《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一文中,认为他们的文艺理论“实质上是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说法”。颜翰彤在《读枙野玫瑰枛》一文中,认为这部剧作美化了汉奸,宣传了法西斯的“力”,是抗战以来最坏的一种剧本。这场着眼于政治的“民族文学运动”论战,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意识的论战,两种不同的民族复兴之路的论战,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文学意义。
发生于1942年到1943年间的“文艺政策”论战,是一场政治性、党派性、阶级性更为浓烈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一场论战。李辰冬起草、戴季陶和陈果夫“详细订正”、张道藩署名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运动纲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文艺思想理论的体系化与法典化。这一“文艺政策”规定“三民主义”为“文艺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文艺的服务对象;规定文艺不得去写社会黑暗,不得挑拨阶级仇恨,不得带悲观色彩,不表现浪漫情调,不写无意义作品、不表现不正确意识,而“要写统治阶级、资本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仁爱和平”。为着扩大这一“文艺政策”的影响,潘公展召开文艺政策座谈会,《文化先锋》与《文艺先锋》两家杂志辟“文艺政策讨论特辑”,称赞“文艺政策”的提出“实为当务之急”,必须作为“全国文艺家创作的指南针”、“写作标准”与“写作依据”,以“纠正共产主义左倾,负担‘建设感情’的任务”。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为配合这一文艺政策的推行,还大肆查禁与销毁进步书刊。据统计,仅重庆一地,1942年到1943年间,就有1400余种书刊不准出版发行,1943年就有116种剧目不准上演,1942年就销毁了包括《茅盾自选集》在内的1242册图书。可见,这一文艺政策实为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构成部分,它遏制了进步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文艺界对官方的这一文艺政策的抵制与批判,主要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他们或借文艺政策讨论中梁实秋、沈从文发的微词,指出官方用一种制度来限制作品必然得不到好结果,表示“始终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对文艺的干涉”;或在鲁迅纪念会与茅盾、老舍、张恨水等人祝寿活动中,指责只准歌颂不许暴露的文艺政策是一种怪论,如果让其发展下去,必然会是非不分、曲直不明,阻碍文艺发展,并表示要冲破文化专制主义与文艺政策的禁令,大胆看取社会人生,暴露黑暗,呼喊民主自由。这场论争,是进步文艺争生存、争自由发展的论争。
“民族形式”讨论,是本时期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理论论争中最具理论价值与文学意义的一场论争,它关涉着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路向。1937年到1940年间,解放区、国统区、香港等地的中国文艺家,在民族意识与人民意识空前激发的氛围中,接受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论述给予的启迪和“苏联方面的示唆”,所展开的“民族形式”讨论,将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推进到民族形式讨论的新阶段。这场“民族形式”讨论的焦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虽然是“只偏于一局部的问题”,然而却包含着文艺家们对建立“民族形式”的途径所作的多种设想和全心力投入。其中,有三种意见具有代表性。一是在民族形式的三个源泉——“民间文艺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新兴文艺大众化传统的批判的继承”、“世界文学的批判的移植”中,应以“民间文艺形式的批判的运用为缔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或主导契机”。二是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或“主导契机”,应在于“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艰苦斗争的道路,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三是认为,应以现今新文艺已经达到的成绩为基础,加强吸收历史优秀文学遗产、民间文艺的优良成分以及外国文学精华。尤其是,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对“民族形式”的建立问题,作了更为冷静而深入的思考与阐释。郭沫若在《“民族形式”的商兑》一文中,认为“民间文艺”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并呼吁文艺家们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源泉,用陶冶过的民众语言,写民众的生活、要求与使命。茅盾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中,批评了不正确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指出“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良作风,更要深入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底提出和论争》及《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实践意义》等文章中,从文艺的实际发展过程与文艺的现实斗争情势上分析和批评了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建立民族形式的主张,认为:“以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为基础,一方面在对象上更深刻地通过活的面貌把握民族的现实,一方面在方法上加强地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底经验,这才能够创造为了反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民族形式’。”这场“民族形式”讨论,虽然未能构建起比较系统的民族形式理论框架,然而却反映出中国文艺家们在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洪流中,呼唤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学回归,促使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上向前发展所表现出的真诚,填补了二三十年代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学表层断裂而造成的鸿沟。从这一角度说,“民族形式”讨论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主观论”是胡风在民族意识与人民意识激发和高扬时期构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强调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的能动性与自主性。胡风这一文艺思想理论孕育、萌发于30年代左翼文坛,形成于本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论争过程。《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关于创作的二三感想》、《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论现实主义的道路》等文章,体现出胡风的“主观论”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
第一,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产生文学的土壤,文学是生活现实或生活要求的反映。
第二,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他认为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基础,作家与生活结合,才能使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彼此融合,彼此渗透,作家的精神力量与战斗要求才能得到培养与形成。
第三,文学创作过程问题。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写真实的人、活的人,应写灰色人生战场上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与夺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的思想要求。同时,文学创作过程是从对于血肉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这种搏斗是对对象的摄取过程、批判过程,其中包含了作家不断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作家写的人,是通过作家自己的情感去体验过的人,人物的情感是作家情感的外化。他认为这是创作的源泉。第四,文学批评问题。他认为:①文学批评是创作实践过程或实践内容的反映,同时又对创作实践起指导作用。②批评家应深入作家的创作心理过程,但不一定要和作家共鸣,反而更多地向作家反抗。③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作品,是文学现象。④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对于落后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批评和对于进步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张扬,对于旧生活传统及其美学传统的反抗与摧毁和对于新生活的萌芽及其美学特征的发现与养成,其重心是向着广大人民与进步读者,开拓思想方向、建立思想影响、培养健康的文艺欣赏力量。批评家与作家协力地发掘和改造时代精神。⑤批评家应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一代精神战士。
第五,关于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创作倾向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由来已久,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他执著地批判这两种创作倾向。
以上五项内容的关节点,是生活实践与主观战斗精神、战斗要求与人格力量。胡风这一体系化的文艺思想理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形态,获得了一批文艺家的认同与接纳,产生了重大影响。胡风也用这一思想理论原则为尺子,批评一切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其中也就难免不出现失误,比如把茅盾、沙汀等作家的作品视为客观主义标本而加以批判,致使其思想理论呈现出偏狭性与教条主义色彩。同时,胡风这一文艺思想理论与当时国统区文艺界正在学习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较大分歧乃至抵触。比如,胡风较少正面论及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无产阶级文艺新方向;较少论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而主要讲通过生活实践与主观精神的双向活动达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反对善男信女忏悔式的改造思想;强调写民众的精神奴役创伤,而不讲表现民众的美德。这种表层的分歧,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分野:一个是从政治角度来谈文艺、来规范文艺;一个是从文艺角度来谈文艺干预政治。正是这种分歧与抵触,引发了一场时间较长而又尖锐复杂的论争与批判。
1944年后,对“主观论”的讨论与批判逐渐开展起来。黄药眠首起批评“主观论”。他在《读了枙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枛》一文中,认为胡风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从实际的生活里面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与运动上的公式”。这实际上是认为“主观论”是先验的唯心主义。1945年冬,国统区文艺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思国统区文艺运动时,对“主观论”同调者舒芜与王戎的文艺观点进行公开批评。舒芜《论主观》一文得到胡风的重视,评价甚高,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影响的问题。”黄药眠针对舒芜的文章写了《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认为舒芜的观点是“最典型的唯心论”。邵荃麟针对王戎的观点,在《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一文中,认为“离开主观精神的社会基础,去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紧密结合,可能使我们走到超阶级超社会的唯心论泥沼中去。”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的紧密的结合”,而必须强调与人民结合,到人民大众中去;简单地强调“主观精神的燃烧”、“搏斗和冲刺”,有时可能是与人民大众相违反的。对于这些批评文字,胡风及其同调者在《希望》、《泥土》、《呼吸》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予以反批评,其中夹杂着一些非学术意识与情绪。1948年,邵荃麟等人在香港对胡风“主观论”进行了集中的批判。邵荃麟在《论主观问题》一文中,认为“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的部分——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彩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这“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邵荃麟执笔的香港文艺界同仁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更一致认为,当时文艺运动的主要倾向是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表现,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
胡风的“主观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强调与肯定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主体的能动作用与自主性,这对于促使“文学和人的关系”倾向于“内化”,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围绕“主观论”展开的历时5年之久的这场论争,就“主观论”批评者一方而言,基本上着眼于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层面,倾斜于“文学和人的关系”的“外化”,认为强调与肯定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自主性就会滑向唯心主义泥淖或就是唯心主义倾向。因此,“主观论”者和“主观论”批评者的分歧,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同一大框架内的现实主义的两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歧与碰撞。这两种理论体系,应该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如果说,这两种理论体系实现了互补,无疑有利于“文学和人的关系”由“外”向“内”、由“内”向“外”,“内”、“外”融合健康发展。但是,“主观论”这一理论体系却日益被视为异端邪说,大加排击。当时的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分歧与碰撞,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延绵不断,特别是唯政治的导向,致使“文学和人的关系”趋于政治层面之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