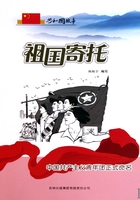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
在穷底结果的病以后,全身便就成枯黄色,脸孔黄的和小铜鼓一样,连眼白也黄了。别人说他是黄胆病,孩子们也就叫他“黄胖”了。有一天,他向他底妻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子也都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身上?……”
他底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底刚满三周的小男孩——孩子还在啜着奶,她讷讷地低声地问。
“你,是呀,”她底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我已经将你出典了……”
“什么呀?”他底妻几乎昏去似的。
屋内是稍稍静寂了一息。他气喘着说:
“三天前,王狼来坐讨了半天的债回去以后,我也跟着他去,走到了九亩潭边,我很不想要做人了。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猫头鹰在耳朵边不住地口转,我底心被它叫寒起来,我只得回转身,但在路上,遇见了沈家婆,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做什么。我就告诉她,请她代我借一笔款,或向什么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饰去暂时当一当,免得王狼底狼一般的绿眼睛天天在家里闪烁。可是沈家婆向我笑道:
‘你还将妻养在家里做什么呢,你自己黄也黄到这个地步了?’
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没有答,她又说:
‘儿子呢,你只有一个了,舍不得。但妻——’
我当时想:‘莫非叫我卖去妻了么?’
而她继续道:
‘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
这样,她就直说出:‘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又因他底大妻不允许,只准他典一个,典三年或五年,叫我物色相当的女人:年纪约30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说的,假如条件合,肯出80元或100元的身价。我代她寻了好几天,总没有相当的女人。’她说:现在碰到我,想起了你来,样样都对的。当时问我底意见怎样,我一边掉了几滴泪,一边却被她催的答应她了。”
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声音很低弱,停止了。他底妻简直痴似的,话一句没有。又静寂了一息,他继续说:
“昨天,沈家婆到过秀才底家里,她说秀才很高兴,秀才娘子也喜欢,钱是一百元,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沈家婆并将日子也拣定了——本月十八,五天后。今天,她写典契去了。”
这时,他底妻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吞吐着问:
“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
“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决定了么?”妇人战着牙齿问。
“只待典契写好。”
“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底爸呀!”
春宝是她怀里的孩子底名字。
“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你也想到过春宝么?春宝还只有5岁,没有娘,他怎么好呢?”
“我领他便了。本来是断了奶的孩子。”
他似乎渐渐发怒了。也就走出门外去了。她,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这时,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底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底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底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飞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溅声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声以外,女孩一声也不喊——她疑问地想,为什么也不重重地哭一声呢?竟这样不响地愿意冤枉死去么?啊!——她转念,那是因为她自己当时昏过去的缘故,她当时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
想到这里,似乎泪竟干涸了。“唉!苦命呀!”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这时春宝拔去了奶头,向他底母亲的脸上看,一边叫:
“妈妈!妈妈!”
在她将离别底前一晚,她拣了房子底最黑暗处坐着。一盏油灯点在灶前,萤火那么的光亮。她,手里抱着春宝,将她底头贴在他底头发上。她底思想似乎浮漂在极远,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远在那里。于是慢慢地跑回来,跑到眼前,跑到她底孩子底身上。她向她底孩子低声叫:
“春宝,宝宝!”
“妈妈,”孩子含着奶头答。
“妈妈明天要去了……”
“唔,”孩子似不十分懂得,本能地将头钻进他母亲底胸膛。
“妈妈不回来了,三年内不能回来了!”
她擦一擦眼睛,孩子放松口子问:
“妈妈那里去呢?庙里么?”
“不是,三十里路外,一家姓李的。”
“我也去。”
“宝宝去不得的。”
“呃!”孩子反抗地,又吸着并不多的奶。
“你跟爸爸在家里,爸爸会照料宝宝的:同宝宝睡,也带宝宝玩,你听爸爸底话好了。过三年……”
她没有说完,孩子要哭似地说:
“爸爸要打我的!”
“爸爸不再打你了,”同时用她底左手抚摸着孩子底右额,在这上,有他父亲在杀死他刚生下的妹妹后第三天,用锄柄敲他,肿起而又平复了的伤痕。
她似要还想对孩子说话,她底丈夫踏进门了。他走到她底面前,一只手放在袋里,掏取着什么,一边说:
“钱已经拿来七十元了。还有三十元要等你到了后十天付。”
停了一息说:“也答应轿子来接。”
又停了一息:“也答应轿夫一早吃好早饭来。”
这样,他离开了她,又向门外走出去了。
这一晚,她和她底丈夫都没有吃晚饭。
第二天,春雨竟滴滴淅淅地落着。
轿是一早就到了。可是这妇人,她却一夜不曾睡。她先将春宝底几件破衣服都修补好。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连孩子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移交给他底父亲——实在,他已经在床上睡去了。以后,她坐在他底旁边,想对他说几句话,可是长夜是迟延着过去,她底话一句也说不出,而且,她大着胆向他叫了几声,发了几个听不清楚的音,声音在他底耳外,她也就睡下不说了。
等她朦朦胧胧地刚离开思索将要睡去,春宝又醒了。他就推叫他底母亲,要起来。以后当她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向他说:
“宝宝好好地在家里,不要哭,免得你爸爸打你。以后妈妈常买糖果来,买给宝宝吃,宝宝不要哭。”
而小孩子竟不知道悲哀是什么一回事,张大口子“唉,唉,”
地唱起来了。她在他底唇边吻了一吻,又说:
“不要唱,你爸爸被你唱醒了。”
轿夫坐在门首的板凳上,抽着旱烟,说着他们自己要听的话。一息,邻村的沈家婆也赶到了。一个老妇人,熟悉世故的媒婆,一进门,就拍拍她身上的雨点,向他们说:
“下雨了,下雨了,这是你们家里此后会有滋长的预兆。”
老妇人忙碌似地在屋内旋了几个圈,对孩子底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讨酬报。因为这件契约之能订的如此顺利而合算,实在是她底力量。
“说实在话,春宝底爸呀,再加五十元,那老头子可以买一房妾了。”她说。
于是又转向催促她——妇人却抱着春宝,这时坐着不动。老妇人声音很高地:
“轿夫要赶到他们家里吃中饭的,你快些预备走呀!”
可是妇人向她瞧了一瞧,似乎说:
“我实在不愿离开呢!让我饿死在这里罢!”
声音是在她底喉下,可是媒婆懂得了,走近到她前面,眯眯地向她笑说:
“你真是一个不懂事的丫头,黄胖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呢?那边真是一份有吃有剩的人家,两百多亩田,经济是宽裕,房子是自己底,也雇着长工养着牛。大娘底性子是极好的,对人非常客气,每次看见人总给人一些吃的东西。那老头子——实在并不老,脸是很白白的,也没有留胡子,因为读了书,背有些偻偻的,斯文的模样。可是也不必多说,你一走下轿就看见的,我是一个从不说谎的媒婆。”
妇人拭一拭泪,极轻地:
“春宝……我怎么能抛开他呢!”
“不用想到春宝了,”老妇人一手放在她底肩上,脸凑近她和春宝。“有五岁了,古人说:‘三周四岁离娘身,’可以离开你了。只要你底肚子争气些,到那边,也养下一二个来,万事都好了。”
轿夫也在门首催起身了,他们噜苏着说:
“又不是新娘子,啼啼哭哭的。”
这样,老妇人将春宝从她底怀里拉去,一边说:
“春宝让我带去罢。”
小小的孩子也哭了,手脚乱舞的,可是老妇人终于给他拉到小门外去。当妇人走进轿门的时候,向他们说:
“带进屋里来罢,外边有雨呢。”
她底丈夫用手支着头坐着,一动没有动,而且也没有话。
两村的相隔有三十里路,可是轿夫的第二次将轿子放下肩,就到了。春天的细雨,从轿子底布篷里飘进,吹湿了她底衣衫。
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来迎她,她想:这当然是大娘了。可是只向她满面羞涩地看一看,并没有叫。她很亲呢似地将她牵上阶沿,一个长长的瘦瘦的而面孔圆细的男子就从房里走出来。他向新来的少妇,仔细地瞧了瞧,堆出满脸的笑容来,向她问:
“这么早就到了么?可是打湿你底衣裳了。”
而那位老妇人,却简直没有顾到他底说话,也向她问:
“还有什么在轿里么?”
“没有什么了,”少妇答。
几位邻舍的妇人站在大门外,探头张望的,可是她们走进屋里面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为什么,她底心老是挂念着她底旧的家,掉不下她的春宝。这是真实而明显的,她应庆祝这将开始的三年的生活——这个家庭,和她所典给他的丈夫,都比曾经过去的要好,秀才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讲话是那么地低声,连大娘,实在也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妇人,她底态度之殷勤和滔滔的一席话:说她和她丈夫底过去的生活之经过,从美满而漂亮的结婚生活起,一直到现在,中间的30年。她曾做过一次的产,十五六年以前了,养了一个男孩子,据她说,是一个极美丽又极聪明的婴儿,可是不到十个月,竟患了天花死去了。这样,以后就没有再养过第二个。在她底意思中,似乎——似乎——早就叫她底丈夫娶一房妾。可是他,不知是爱她呢,还是没有相当的人——这一层她并没有说清楚。于是,就一直到现在。这样,竟说得这个具着朴素的心地的她,一时酸,一会苦,一时甜上心头,一时又咸的压下去了。最后,这个老妇人并将她底希望也向她说出来了。她底脸是娇红的,可是老妇人说:
“你是养过三四个孩子的女人了,当然,你是知道什么的,你一定知道的还比我多。”
这样,她说着走开了。
当晚,秀才也将家里底种种情形告诉她,实际,不过是向她夸耀或求媚罢了。她坐在一张橱子的旁边,这样的红的木橱,是她旧的家所没有的,她眼睛白晃晃地瞧着它。秀才也就坐到橱子底面前来,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呢?”
她没有答,也并不笑,站起来,走到床底前面,秀才也跟到床底旁边,更笑地问她:
“怕羞么?哈,你想你底丈夫么?哈,哈,现在我是你底丈夫了。”声音是轻轻的,又用手去牵着她底袖子。“不要愁罢!你也想你底孩子的,是不是?不过——”
他没有说完,却又哈的笑了一声,他自己脱去他外面的长衫了。
她可以听见房外的大娘底声音在高声地骂着什么人,她一时听不出在骂谁,骂烧饭的女仆,又好像骂她自己,可是因为她底怨恨,仿佛又是为她而发的。秀才在床上叫道:
“睡罢,她常是这么噜噜苏苏的。她以前很爱那个长工,因为长工要和烧饭的黄妈多说话,她却常要骂黄妈的。”
日子是一天天地过去了。旧的家,渐渐地在她底脑子里疏远了,而眼前,却一步步地亲近她使她熟悉。虽则,春宝底哭声有时竟在她底耳朵边响,梦中,她也几次地遇到过他了。可是梦是一个比一个缥缈,眼前的事务是一天比一天繁多。她知道这个老妇人是猜忌多心的,外表虽则对她还算大方,可是她底嫉妒的心是和侦探一样,监视着秀才对她的一举一动。有时,秀才从外面回来,先遇见了她而同她说话,老妇人就疑心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买给她了,非在当晚,将秀才叫到她自己底房内去,狠狠地训斥一番不可。“你给狐狸迷着了么?”“你应该称一称你自己底老骨头是多么重!”像这样的话,她耳闻到不止一次了。这样以后,她望见秀才从外面回来而旁边没有她坐着的时候,就非得急忙避开不可。即使她在旁边,有时也该让开一些,但这种动作,她要做的非常自然,而且不能让旁人看出,否则,她又要向她发怒,说是她有意要在旁人的前面暴露她大娘底丑恶。而且以后,竟将家里的许多杂务都堆积在她底身上,同一个女仆那么样。她还算是聪明的,有时老妇人底换下来的衣服放着,她也给她拿去洗了,虽然她说:
“我底衣服怎么要你洗呢?就是你自己底衣服,也可叫黄妈洗的。”可是接着说:
“妹妹呀,你最好到猪栏里去看一看,那两只猪为什么这样喁喁叫的,或者因为没有吃饱罢,黄妈总是不肯给它们吃饱的。”
八个月了,那年冬天,她底胃却起了变化:老是不想吃饭,想吃新鲜的面,番薯等。但番薯或面吃了两餐,又不想吃,又想吃馄饨,多吃又要呕。而且还想吃南瓜和梅子——这是六月里的东西,真稀奇,向那里去找呢?秀才是知道在这个变化中所带来的预告了。他整日地笑微微,能找到的东西,总忙着给她找来。他亲身给她到街上去买橘子,又托便人买了金柑来。他在廊沿下走来走去,口里念念有词的,不知说什么。他看她和黄妈磨过年的粉,但还没有磨了三升,就向她叫:“歇一歇罢,长工也好磨的,年糕是人人要吃的。”
有时在夜里,人家谈着话,他却独自拿了一盏灯,在灯下,读起《诗经》来了: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时长工向他问:
“先生,你又不去考举人,还读它做什么呢?”
他却摸一摸没有胡子的口边,怡悦地说道:
“是呀,你也知道人生底快乐么?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你也知道这两句话底意思么?这是人生底最快乐的两件事呀!可是我对于这两件事都过去了,我却还有比这两件更快乐的事呢?”
这样,除出他底两个妻以外,其余的人们都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