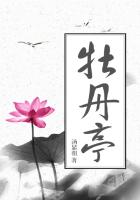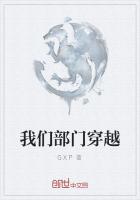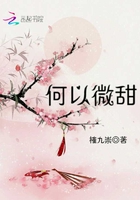三、第一个“全部扔光”
我六岁进书房,也就是私塾,读的是司空图《诗品》、《古诗十九首》等,一个幼童刚识字,对这些古典文学真是莫名其妙,只像山歌一样唱唱而已。接着读《论语》,总算读完了,刚要学《孟子》,东北街张家聘请了一位吴润之先生教书。我父征得张家主人同意,让我去附读。吴先生教三个学生,张家的三子逸侪、四子荷百和我,那年我九岁。一到张家,吴先生首先问我读过些什么,我一一说了,谁料他当即吩咐我把以前读的全部扔掉,先识方块字,重新学起,也就是“从零开始”。吴先生为什么这么决定,当时我完全不懂,只是照办罢了。
吴先生非常懂音韵。他每次给我四个方块字,是平、上、去、入搭配好了的,教我念字念准,不许含糊过去。就是这样念了几百个字,我自然而然地懂得了四声,一听就能辨别,一念就能准确。这对我学昆曲以及后来学京剧的唱念,起了奠定基础的很好作用。我生平有过两次“全部扔光”,这第一次是吴先生要求的,我是被动的;后来我拜程继先先生为师,学京剧小生,又来一次“全部扔光”,那是我瞒着老师主动决定的了(详后文)。这两次“全部扔光”,对我影响很深远,使我尝到了甜头。现在有相当多的中青年演员,舞台经验不少,但对四声一点不懂,经常发生错误,其实质是在戏曲唱念艺术上缺乏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识字。深愿他们把已经有的一知半解,来一个“全部扔光”,而采取“从零开始”的态度,有系统有步骤地学习音韵知识,正确地运用到舞台实践中去,免得自己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吴润之先生教书很特别,不要求我定要读完《四书》、《五经》,先要我读一种“蒙学课本”,可能是当时上海澄衷学堂编印的;再就是教了一部《孟子》。
他教书时像一位说书先生,夏天手执一把油纸扇,边摇边讲,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不是一本正经得令人沉闷或害怕。所以学生听得懂,学得进。如果我能向他多学几年,就更幸运了,可惜他才教完我《孟子》,不幸因病逝世。我为失去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而深感哀痛。在这以后,我家从石塘桥迁到狮林寺巷,读书很不正常,至今回忆起来,还痛惜浪费了这段少年时光。
四、“一龙二虎”
张家主人荫玉和四个儿子,都向我父亲学曲,荫玉唱丑,大儿子紫东唱老生,次子笛渔唱小生,三子逸侪唱旦角,幼子荷百唱丑。他家补园的“三十六鸳鸯馆”和“十八曼陀罗花馆”是张氏父子和我习曲、唱曲的基本阵地。我父亲认为,我除了学官生、巾生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家门”的好曲子,也该学会。
张紫东学《侠武》、《三挡》、《弹词》、《骂曹》,张荷百学《扫秦》、《问探》、《拾金》,我像旁听生一样,学会了。在狮林寺巷家里,苏州曲友来向我父习曲的多起来了,有徐镜清、陆麟仲、殳九组、尤企陶、宋选之、宋衡之、顾公可、俞锡侯以及开眼镜店的刘姓弟兄等人。房屋不宽,座客常满,十分热闹,彼此交流频繁,见闻随之扩充,对每个人欣赏水平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在此期间,我又学会了净角的《刀会》,旦角的《女弹》、《认子》、《寻梦》、《题曲》等戏。我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出发,觉得今天的中青年演员,如果多学习和多了解一些本行当以外的戏,来一个“一专多能”,是有益无害的。当然,一专为主,多能是辅,也颠倒不得。
大约就在此时,苏州曲友中间,有所谓俞门的“一龙二虎”之称。“一龙”指顾公可,他肖龙,长我十岁;“二虎”指俞锡侯和我,我俩同年肖虎。顾公可是苏州怡园主人顾子山(名文彬)之孙,着名吴门画派顾鹤逸(名麟士)之长子。他一心要在俞门中出类拔萃,执掌牛耳,鉴于我父已近八十岁,不敢太多劳神拍曲,于是把我这十三四岁的师弟找去当“小先生”,因为他和我一样是唱官生的(俞锡侯唱旦)。他身体很瘦,嗓音却极宽亮。他家有自备的藤轿,从杭州请来两位抬轿工人,健步如飞,又快又稳。公可经常派藤轿来狮林寺巷,接我到护龙街(今人民路)怡园去,为他拍曲、吹曲,喝点酒,吃顿晚饭,再送我回家。在这样的“唱和”之中,也逼得我对曲子要更下一番苦功,才能胜任其事,恐怕这就是“教学相长”的道理吧!
五、笛子和小锣
笛子是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在我幼年时代,苏州最老的笛师是殷溎深和张云卿。殷溎深又称殷老四,他收集曲谱很多,后来张余荪缮写的《六也曲谱》、《昆曲大全》、《怡怡室曲谱》等,大都根据殷的藏本。
张云卿排行老二,身世凄苦,人家叫他“苦二”(后来又讹为柯二)。我几十年间所见笛师,以张云卿为最好。他是个文盲,拿出来的曲谱只有工尺,而用笔帽打成一个个圆圈来替代曲文,但他能给人背曲、拍曲,整个唱词和念白全都储存在他脑海中,其记忆力之强,真是惊人。张云卿曾去北京工作,很受欢迎。后来我到北京,听曲友们谈起张云卿,无不交口赞誉。据我父亲说,有一次他在北京曲集上唱一段《玉簪记·秋江》,由张云卿吹笛,配合得严丝密缝,唱者舒心惬意,听者如饮醇醪。其时有位曲友见猎心喜,急忙请我父亲教会了这支曲子,也要求张云卿吹笛伴奏,但效果不佳,就责怪张云卿对人有厚薄。张云卿不能接受,说:“俞某人唱得有交代,我合得上,你的唱没有‘肩胛’,是‘连刀切十八块’,一无交代,叫我怎么吹?”因为最好的笛师要在伴奏时扔掉自己的东西,而跟着演唱者的“气口”、“尺寸”和各种润腔技巧,紧紧配合,才能相得益彰,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倘若唱得不合规范,没有交代,怎能埋怨笛子配得不好呢?张云卿在苏州,借住玄妙观财神殿里,去世时孤身一人,并无家属。旧社会艺人的下场,悲惨极矣!他有一徒弟赵阿四,后来在上海吹笛,指法颇似乃师。
此后,苏州又出了一位笛师,名叫永福,不知其姓。他性格内向,不大说话,逢到“同期”,总是他吹笛,任何戏码,没有不会的,而且“后场”(乐队的传统称谓)乐器,每件都拿得起(京剧叫做“六场通透”),吹起笛来,只见他的长指甲抖呀抖的。他的徒弟李荣生笛声饱满,水平也不错,大名鼎鼎的《十五贯》,就是他吹的。
我初次到上海才七八岁。那时上海最老的笛师是范金泉,吹得也好。
1921年,我父七十五岁,应上海百代公司之邀,灌制了十三面唱片,是由殷溎深的徒弟严连生伴奏的。严连生穷得打光棍,没有家,寄住在上海集益里潘和懋绸庄里,生活完全由绸庄主人潘祥生供给。他一向打小锣,后来才吹笛。
有一次,在潘和懋举行“同期”,我父亲唱《断桥》。这是一出“风火戏”,其中“锣段”(京剧称为“锣经”)很复杂,严连生早已改行吹笛,那天自告奋勇,为《断桥》打小锣;名鼓师王松福打鼓,他是打鼓的好手。严的小锣确实好,不但尺寸准确,而且声音也和别人打的不同,按照现代舞台术语说,打出了气氛,打出了感情,为演唱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当时苏州、上海一带的昆班像全福、大章、大雅等,主要演文戏,故名“文班戏”。文班戏以小锣为主,大锣居次。经过历代艺人的经验积累,打小锣大有学问。过去的小锣有一定的调门,苏州河沿街一家响器铺里有位老师傅,极有本领,买客需要小锣定什么调,他手里的头“砰”地一下,就能打出什么调,真是“一锤定音”!这样的绝技完全靠苦练得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约辛亥革命刚过,我在苏州玄妙观看到了“童子军”吹的军笛,笛管很短,不贴笛膜,我要父亲给我买一支,在家里吹着玩。我不懂哪个笛孔管哪个音,父亲用纸写了工尺,给我贴在笛子上,可我嘴唇吹笛,眼睛看不到纸上的字,还是白搭。父亲骂我太笨,只要对着镜子吹,不就看到字了吗?我一试果然。我还想,几十几百出戏,大人们怎么都能记住工尺谱的?一天,我吹着吹着,心里在唱,手指就会吹出来了。我换上一支正式的曲笛,就这样学着吹会了。在狮林寺巷时,父亲已七十多岁,牙齿全掉了,吹不动笛了,所以只给学生们拍曲,拍会了,都由我吹。我会的曲子随之日益增多,对我尔后比较全面了解各个行当的戏大有裨益。
六、看戏和学戏
辛亥革命前后,苏州城内的全福班并非经常演出。我在童年,对看戏不知有多喜欢,逢到看戏的日子,午饭后早就心痒得呆不住了。父亲说时间还早,急什么?我可不行,定要早些去,从“天官赐福”、“跳加官”、“报台”看起(“报台”又称“副末登场”,念一首词,最后加一句:“交过排场”,接演正戏),直看到“老旦做亲”(《百顺记》传奇中王增的夫人由老旦扮演,在《占登》里夫妇重又拜堂做亲。昆班传统每场加演这节,作为结束,取其吉利)。如果不是从头看到尾,我就不满足。苏州制作的戏装绣工考究,至今名闻四方,这类戏衣庄做一件新“行头”(戏衣)便用竹竿挑出店门,在街道旁飘荡。我经常走过,就抬起头来看得入迷,心想:哪天我也要穿起它来唱戏!孩提的幻想后来竟成了现实。
张家的长子紫东,大约长我二十岁,极爱昆剧表演,常请沈月泉、沈锡卿两位老师教戏。我看到他们“踏戏”(昆班传统对排戏的名称),心里当然极为羡慕,但父亲认为昆剧身段繁重,非下苦功不能学好,那就会影响习曲,所以一向不准我学身段。到我十四岁那年,张紫东为其母亲做寿,打算演戏。他家在迎春坊住宅的天井里,造起一座戏台,平日可以放下,演戏时用架子撑高。张紫东先向我父说好了,怂恿我陪演《牧羊记·望乡》,他演苏武,我演李陵。我父亲虽不上台,但看戏多年,谁有什么好手段,都能说得出。有时高兴,比划几下,用大袖口当水袖抖。我早就看得熟,跟着学,所以对一般小动作,心中也有点数了。沈锡卿老师教这戏是在夏天,我打着赤膊学,沈老师说这样很好,可以看到手、臂、肘、腕各个部位的使用方法,有毛病就可指出、改正。及至《望乡》演出,居然不僵不呆,博得了宾客的赞赏,父亲也很高兴。禁不住曲友们的好评和鼓励,我又学演了《紫钗记·折柳阳关》,成绩也不错。
这些剧目重在唱念,身段不繁,传统称为“摆戏”,表演比较容易。在此以后,我请沈月泉老师陆续教了不少官生、巾生、鸡毛生、鞋皮生的折子戏,演出也逐渐增多了。
在多学了几出戏之后,渐渐对传统的小生步子感到幅度不够,容易沾带“脂粉气”。于是试着改为前脚出去、落地,与后脚拉开距离,腰腿一使暗劲,显得出古代男子昂藏七尺的气概。同时注意体形和唱念,把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所谓“书卷气”体现出来,才可避免一些庸俗浮浅等弊病。几十年来,在我的舞台实践中,自然地形成一种表演风格,溯其根源,在青少年时代对昆剧舞台艺术的揣摩之中就开始了。
七、第二个“全部扔光”
我的习曲过程,已经简要地写完了。有关昆曲的见闻以及自己的艺术生涯,只得留在回忆录中详述。但必须说一说我一生中的第二个“全部扔光”,才能和上文呼应。
我十九岁到上海,在穆藕初先生的豫丰纱厂担任文书工作。穆先生酷爱昆曲,为苏州的昆剧传习所(即南昆的“传”字辈老师们当初的学艺之所)出过资金,也在上海大力提倡昆曲,这里暂不细述。我在上海,除了继续唱曲和偶或演出外,还参加了京剧票房“雅歌集”,向蒋砚香老师学京剧小生戏。
1922年,程砚秋先生二次到上海,很想在京剧之外加演一出昆曲《游园惊梦》,苦于没有恰当的昆剧小生。有人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我就配演了柳梦梅;1925-1926年间,他再度来沪,在义务戏中我又为他配演了《奇双会》、《玉堂春》、《红拂传》。这几次合作,他都感到满意,因此竭力劝我到北京去“下海”(京剧界术语,指从业余的票友转为专业演员)。我因父亲阻止,难以从命,只好婉言辞谢。1930年春,我二十九岁,父亲逝世了。秋季,砚秋又来沪演出,知道我父已故,坚决要我一同北上合作。此时已无拒绝理由,我只表示需要正规学习,要求他能取得京剧小生前辈程继先先生的同意,收我为徒,使我能好好学几出京剧小生戏。如果此事不成,我依然不想“下海”。程继先先生大家知道是不收徒弟的,但经砚秋一再地要求,并得袁寒云从中协助,居然应允了。我遂即束装北行,拜程先生为师(此事曾轰动北京戏剧界)。
拜师后,程老师问我:“你学过几出京戏呀?”我心想在上海已向蒋砚香老师学了许多,什么《九龙山》、《借赵云》、《叫关》、《玉门关》、《飞虎山》等一般小生戏都学过了,上台“票”得也不少。但那是“票友”时期,要求还不最严格,现在既要“下海”,就该学得更扎实些。程先生的艺术,讲究表演和念白,是京剧界着名的,我要从头学起,才能纳入正轨。因此我答称:“老师,我只会一些昆曲戏,京戏一出也不会,所以特来拜您为师。”程老师听了大为高兴,说:“好,改改弄弄是不行的,从头学起最好。”于是,从“九龙口”亮相、抖袖,举手投足,老师一招一式地教,我跟着一板一眼地学。他抓出我许多疵病,如身体摇晃,臀部外突等等,要我每天练功,“山膀”、“云手”、“耗腿”,一拉就是半小时,练得臂腿酸痛,却渐渐长了功。这一次的“全部扔光”是出于自觉自愿的,虽向老师撒了个大谎,可是受益匪浅,得到了程老师的真传,绝不掺杂。程老师教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学会了不少剧目,最主要的是《群英会》、《临江会》、《岳家庄》、《监酒令》等,绝大部分经常演出,只有《临江会》演出机会较少,现在记忆中已模糊不清了,实在是愧对师门。
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