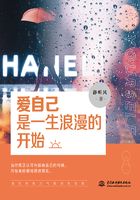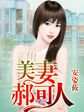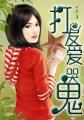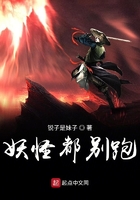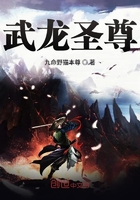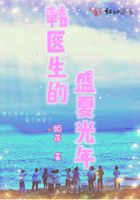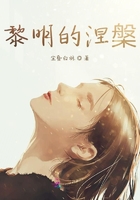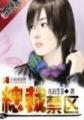赵燕侠(1928- ),河北武清人。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主演过《十三妹》、《霸王别姬》、《白蛇传》、《沙家浜》等。
“不疯魔,不成活”
旧京戏班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有所作为,不勤学苦练不成;而且一般的勤学苦练还不成,一定要达到废寝忘食,甚至“疯疯癫癫”的程度,这样才能练出真功夫来。
我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混功”,每当父亲练功时,我也拿上一截棍子在一旁模仿着练。特别是自从首次演出《三娘教子》里的小东人薛倚哥后,戏班里的人都夸我有登台演出的才能,父亲也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气教我练功。开始练,先练踢腿、下腰、撕腿等一些基本的功夫。父亲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是唱武生的,就拿培养武生的路子来教我。如练正面“撕腿”(就是正面劈叉),把两腿劈开伸直了渐渐往下坐。开始我坐不下去,父亲就压着我的双肩狠劲往下压。压得屁股坐在地上以后,就搬来两块大石头,一条腿上压一块。那时候我们这些穷唱戏的也没有表计时间,父亲就点上一炷长长的香插在我面前的土堆上,什么时候香燃尽了,才准许我站起来活动一下,松快松快。痛啊,真是难以忍受,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滴,等一炷香燃尽了,我面前的土地也被汗水淋湿了。硬功夫就是这么用汗水泡出来的。
父亲小时候“写”给王师傅学戏,受尽了毒打。为了早日能学出戏来,他把这套“打戏”的方法也用在了我身上。父亲教得严,我学得也苦。每日白天练完了,晚上还要接着练,一年四季寒暑不辍。记得,那是父亲在武汉搭班唱戏的时候,每天晚上夜戏散场后,他也顾不上休息,赶紧把我叫到后台就教练起来,他做什么动作,就让我跟着做什么动作。然后,父亲手里拿一条枪杆,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反复练习,每当一个动作做得稍差一些,照着我身上“叭叭”就是一阵枪杆抽打。有一天我发高烧,体温达到三十九度多,可父亲还是不让我休息,散戏后又把我叫到后台练带枪鹞子翻身。我由于发高烧,头晕,转起圈圈来只觉天旋地转,一个动作没做好,不想父亲还是把我打了一顿。过去唱夜戏时间拖得长,哪场戏下来也得在十二点左右。这天晚上,我练鹞子翻身一直练到凌晨三四点钟左右,再也支持不住了,一个翻身没转过去,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事后母亲直埋怨我父亲,说不该在孩子发高烧的时候还打着练功。父亲也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可他还是说,越是在身体不利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练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过硬的本领来。当然,他的那套教学方法,今天不该提倡,但那种严格要求的精神,对我艺术上的进步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说实话,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我的身体条件并不怎么好。就拿我这双扁平足来说吧,要是现在报考戏曲学校,一定不合格。因为这是学戏中的一大缺陷,在做一些纵跳翻腾的动作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这双扁平足确实给我练功带来了不少困难,但这不但丝毫没有使我失去信心,反而促使我下决心用辛勤的汗水来弥补所谓“戏理”上的不足。
幼年时代,我一直跟随父母在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等一些地方流浪。父亲经常搭不上班,一时不唱戏就没钱吃饭。父亲被一家人的生活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流浪的途中不得不给人家拉船背纤,那景象至今我记忆犹新。南方的夏天,父亲赤膊光脚,炎热的太阳照射着他那汗水明晃晃的脊背,弯腰弓背,一步一步往前挪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和母亲坐在船上,看着父亲背上那条粗粗的纤绳,好像不是在拖着小船前进,而是紧紧系在了我的心头上,拖着我在长夜难明的苦难社会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爬着。
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眼泪也不由得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父亲啊,父亲,怎忍心让您这样卖苦力气,难道女儿我就不能挣碗饭给您吃?每当我想到这里,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练功那股子劲一下子就窜了上来,便利用船上的“一席之地”练起功来。船一停,就赶紧跑到岸上去,找块松软地练习抢背、吊毛、鹞子翻身等难度较大的动作。那时候练功,倒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目的,只是为了快练出来,好挣钱养家糊口;也就是说,为了吃饭,就得豁出命去练。
过去,舞台上的旦角都讲究跷功,这也是旦角中的基本功之一,每个学旦角的演员都得练。到了舞台上,不仅要踩着跷表演所饰角色的各种身段动作,而且还要挥刀舞枪“打出手”、翻跟斗,甚至还要在摞起的几张桌子上做各种动作,最后一个“云里翻”下来,没有硬功夫是不行的。但是,练这种跷功,就得要付出大量的汗水,经受得起痛苦的折磨,否则是练不出来的。一些看过我的戏的老观众可能还记得,像《阴阳河》里的踩着跷耍挑子,《游湖阴配》(即后来的《红梅阁》)里踩着跷从两张桌子上面做“云里翻”下地的高难度的程式动作也都能掌握得了。在跷功上,我确实下了一番苦功。
在前辈艺人的旦角中,芙蓉草(即赵桐珊)的跷功是很有些功夫的。他所用的那副跷后来不知怎么落在我小姨马秀荣手里。当时我们家穷买不起跷,每当小姨练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练,小姨不练的时候,我就把跷拿出来偷着练。
说起这副跷来,简直就是一副刑具,硬木木头做的,其形状完全仿照过去缠足女人的小脚制作的,宽窄、大小、曲度等也都一切似真,外面再套上袜子和鞋,就和真的一样了。跷长约在三寸左右,下端是前尖,后圆,中间凹,在靠近脚后跟的地方,有一长约八寸,宽约二寸,厚约二三分,向上斜起的托足板。
踩跷时,演员脚掌的中后部,基本上都要托在这条板上。因此,演员的体重,就要靠前脚掌支撑。为了不使脚后跟露出来,托足板和地平面要成七十五度左右的倾斜角,使足后跟和腿肚子接近垂直,足面和胫骨正面垂直。就和跳芭蕾舞一样,不过就是脚趾前是个三寸木制的小鞋,脚趾在小鞋上,脚趾、脚面和腿成一直线,后边放一木板捆上,比现在穿溜冰鞋难多了。想想看,这样一副跷踩在脚上,怎能好受得了。
练跷功时,先把两只跷牢牢地绑在脚上,然后背靠墙笔挺笔挺地站着,这叫“站跷”,站得时间长了,两脚便由胀变为酸,再由酸到痛,渐渐地腿、腰,甚至背部都感到了酸痛,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由靠墙站立逐渐过渡到扶墙行走,练到一定程度就可离开墙独自站立和行走了。然后再增加难度,在地上放两块砖,或平面的石块,站到上面去。一站就是半天多,这叫“耗跷”。时间站长了,两腿都麻木了,再由人扶着下来走走,那个滋味可难受了。
“耗跷”以后,接着就练“走跷”、“跑跷”以及走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了。
这样练出的功夫,不论是台步还是身段,确实好看,可是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但为了早日能学出戏来,当时我主动找苦吃,在我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硬是练出了跷功。
我们家到了北京后,在裘字街住了不久,就搬进了西砖胡同周义宸(唱老生的)的两间西厢房。这时,父亲搭不进戏班,在家闲着没事,我们父女二人便齐发奋,一门心思用在了我的学戏练功上。常言道:“功夫要练好,一年三百六十个早。”其实,那时我练功,哪分什么早晚。我身穿一副破扎靠,脚蹬一双硬厚底靴,没日没夜地在院子里练来练去,实在累了就打个盹,一觉醒来接着再继续练,有时连打盹的时间也不放过,一个“朝天蹬”(即把一腿伸直,抬到耳边)压着腿睡觉。那副破扎靠穿在身上,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知道往下脱。
头上还得带上破盔头,破盔头上还加了一些沉重的东西。记得有大铁锁、大铁链子等,为的是加重头上的分量,平时练时,头上加重练习惯了,到了舞台上,就会显得轻松自如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贫困的时候。父亲没有戏唱,挣不来钱。费好大劲只能买上五六斤“共和面”,根本不敢吃干的,只能一天吃两顿稀糊糊。有时我练功练得肚子饿了,端起碗来就喝,可当我想起某一个武打套路时,饭也顾不上吃了,放下碗又到院子里练起来。长年穿着厚底靴练功,把四合院的那满地青砖磨得坑坑洼洼,房东女主人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燕侠,以后等你成了名,你要赔我这一地砖!”
练武功是这样,练文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起先,我的嗓音条件并不好,我就下大工夫练。冬天,外面下了雪,雪一化墙上挂了一层冰,我就对着墙喊嗓子,一喊就是几个小时,墙上那层冰都被我呵出的热气融化了。要么我就找来一个大肚小口的坛子,把嘴对紧坛子口喊嗓子。开始不但别人听不到声音,就连我自己也听不到,练得日久天长了,那“嗡嗡”的声音就出来了。因此,后来我的嗓音不但能打远,而且能够持久不衰,不致因嗓子累了而嘶哑,或出现其他的毛病。三十多年来,不论是风天、雨天、雪天,还是干燥的天气,我的嗓子从来没坏过。在同一天晚上,我能唱完了唱功十分繁重的全部《玉堂春》,紧接着再演唱、念、做、表都比较吃重的全部《红娘》。直到现在我仍喜欢翻高腔,而且翻得上去,这不能不说跟我扎实的幼功有很大关系。
俗话说:“若要漂、帅、脆,就得练功不怕累。”我练功,不是要演什么才练什么,而是京剧里的各种行当我都练。年轻时我专工花旦,但青衣、刀马旦、文武小生,甚至彩旦、丑行的功都练。因此,我不但能掌握一般的唱、念、做、打,而且武生中的一些高难程式动作,我也能做得上来。这样全面练功的结果,无疑开阔了自己的戏路子。我演过好几十个年龄、性别、身份、性格不同的人物。从行当来讲,包括青衣、花旦、刀马旦、彩旦、文武小生,甚至小花脸等,我都演过。仅从1943年我十五岁时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到1949年这段时间内,我就演了七十多出戏。这也正像戏班里常说的“功不亏人”。
我的老师在我练功学戏期间,先后拜过好几位老师,使我有机会学习王(瑶卿)派、荀(慧生)派、梅(兰芳)派的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前辈的流派艺术。我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早在我跟随父母在南方流浪期间,有一次到了上海,曾拜着名王(瑶卿)派青衣金碧砚为师。因为当时没有钱,学不起,只跟金老师学了《宝莲灯》等一两出戏。
到了北京后,我先是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为师。那是在1942年8月23日,当时的习俗,拜师是要请吃酒席的,八大盘八大碗地摆几桌,请老师、亲朋、同行等吃喝一顿,酒席间正式举行拜师仪式,然后一登报,社会上就公认谁是谁的正式弟子了。但因当时我家无钱摆请酒席,没有公开登报。
荀慧生在他同一天的《艺事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因赵家贫,没有请客,只向我磕了个头就成了。”当时,荀先生在舞台上已是久负盛誉了,早在1939年就已收了童芷苓、毛世来、吴素秋三个已经能独自挑班的演员为徒了,而我仅是一个穷苦艺人的小姑娘,拜师又不请客,在当时来说有损老师的面子。但他能收我,说明已是很不简单的事了。据荀先生讲,他发现我是块唱戏的材料,有艺术素质,有刻苦精神。荀先生曾对他的“二旦”何佩华说:“这个孩子,看来是很有出息的。”荀先生只给我指点了几出戏,而我所学的荀派戏基本上都是跟何佩华老师学的。何老师虽说武功差一些,但一些荀派戏他都会。在教我学戏期间,每月给他三十元钱。我跟他学了《红娘》、《香罗帕》、《钗头凤》、《红楼二尤》、《勘玉钏》、《荀灌娘》等。后因没钱学不起了。不久,荀先生看了我演出的《十三妹》后,很满意,就把我又介绍给了李凌枫老师。
李老师专教王(瑶卿)派青衣,很有名气,许多名家都是出自李门,一般人他不教,因此教人学戏要价也比较高。我父亲咬了咬牙,把自己仅有的几件行头当了五十元钱,让我跟李老师学了一个月,只学了《祭塔》、《朱痕记》、《王春娥》几出戏,又没钱学下去了。
提起李凌枫老师,我不由得联想到1980年2月25日为纪念着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八十诞辰的一次演出。我和袁世海、李万春、谭元寿、周和桐、刘雪涛以及外地来京参加纪念演出的马(连良)派演员马最良、言少朋、王和霖等同志同台演出了马派名剧《龙凤呈祥》。这次演出,可以说班子搭配相当齐整,也是近年来少见的合作。我饰演戏里的孙尚香。这任务刚接了下来,就引起了同行一些同志的议论。有的说,从来没见我演过《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似这样的“大青衣”不知我怎么演。甚至有人说我演孙尚香是围棋盘里下象棋——不对路数。面对这些议论我沉思了许久。在怀念马先生的同时,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李凌枫老师教我学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