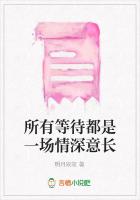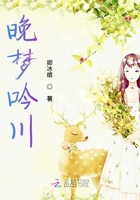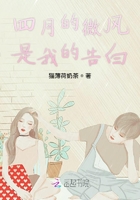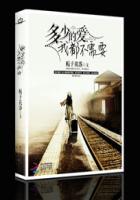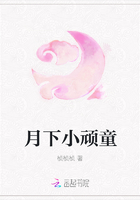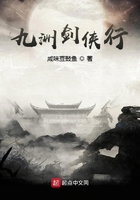夏至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明明是无雨的天色,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同行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即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由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棚屋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蒙蒙。
——《生存与命运》
一七年的夏至是六月二十一日,一八年的夏至也是六月二十一日,都比高中地理教材上的夏至日早了一天。很难说我为什么喜欢夏天,可能是某个夜半我漫步在人已散去的商业街头,忽明忽暗的灯下那个唱着《男孩》的街头吉他歌手让我喜欢上了夏天的安逸,也可能会是珠江边我和老友在漫步的时候,夜风吹来的那一霎那我看到了轻轻拂起的她耳畔旁的几缕头发让我将她回头的笑和夏天联系在了一起。
也可能是因为那无数次半途醒来苦笑着告诉自己这是梦的梦吧。
我喜欢有秩序的音符,不必太悲伤,但或许可以苍凉。那个夏天不论我逃避到哪里,不眠的夜里不知不觉的就迎来了天边泛起了微光,甚至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梦。梦里的你,就像北野武电影里至纯的蓝,湛着溢出的欢愉和清澈,宛如初恋的青春,从山和海的尽头走来。
一个人的酒吧——痛苦与自由
卡夫卡说:“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
他还说:“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痛苦,这是你的自由,与你的天性相符。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就是逃避本身。”
没有了生活,怎么抛弃生活。那我们去重新获得生活吧,这样我们就得从抛弃生活开始。人生的趣味有时候就在这里,不论我每一天早上在哪里睁开眼,我都清楚的知道,我需要什么、又拥有什么,但我却没办法同时把握它们。我们身处世上,我们努力追求的事业,其实只是源于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失去的一些东西,我们付出努力有时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酸楚的自我证明。
一七年夏天,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夏天,离别的到来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想想少年时候的承诺至今也没能兑现,毕竟人生如此,慷慨应允下的承诺只不过到头来唯一的作用是教会我们下次不要再轻易许诺了而已。有的离别很令人伤感,有的人会默默承受,也有的人会宣泄情感。而对于我来说,那个夏天有充足的时间去感受“离别”,讲着前行,其实也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告别,但生活嘛,沉溺于某些东西的时候总归能让人忘掉许多。没人喜欢改变,虽然改变有的时候会带来更好的东西,但人性就是如此,改变总是会带来痛苦。
不知曾几何时,我看到过《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说:“纵欲并非源于快乐,而是源于苦闷。”我们告别了生活,毕竟还有未知的前方给予我们莫大的欣慰。于是我开始想到,出门走走或许会好很多,旅行总是能让人忘掉一部分旧的,开始一部分新的。
其实我本就很喜欢旅行,旅行的时候总是能沉浸在另一段回忆之中,如果碰巧遇到一场雨,就更好了,因为一场雨足以让我爱上一座城市。她曾问我为什么喜欢下雨天,因为只有在下雨时,那些平时熙攘的街道才只剩下三三两两几个人。一个人,一座城,一场雨。一切的一切都像是一出戏剧,舞台就在身边,演员就是你自己。雨中漫步和熬夜相似,在雨中和夜里相遇孤独、习惯并喜欢上孤独,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苦闷啊、孤独啊,过于追求这些负面的东西听着像一个未谙世事冷暖的独生子在成长环境中造成的心理偏差。但这又何尝不可,既然我们其实都不是尼采所说的“宗教式的盲目的乐观主义”,那我们未免先承认世界悲观的本质,再回过头来以审判式的定夺,承认痛苦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看不到的或不愿承认的“救赎”。与百年前如出一辙的是,“救赎”这一词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我此处仍旧必须用它不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借歌队之口慨叹了无奈而又阴郁但却合理的终章:“没有人是快乐的,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人才算是解脱痛苦。”不必为此而焦虑,杞人忧天。这世界本就是悲观主义的天堂,何必强行解释为乐观主义的地狱。
人生必有终点,世界也必有末日,权且承认悲观的世界,并不意味着人生这场悲剧没有它存在的合理意义。就像特里·伊格尔顿撰写《人生的意义》时说的:“悲剧乃是诸多乐观方案的人生意义问题中最有力的之一。”哪怕意义被解构,一切价值崩塌等待重估,但至少真切地痛苦是我们都感知得到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痛苦可以给我们带来残酷而绝望的自由,但毕竟是自由,或者像卢梭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而已。如果我已经抛弃的生活告诉我,我逃避的就是逃避本身,那么我宁可回过头,坚定的走向我的痛苦。
人有权利选择痛苦。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但痛苦之于我们所创造的一切莫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面对死亡、疾病、战争、灾难,我们经受分离、踌躇、忧伤、思念,这一切的痛苦给了人类艺术与道德进步以强大的助推力。当我们意识强大到足够地步的时候,我们终究会有选择或避免痛苦的能力,也只有那时候,能力才能转化为权利。
我们的痛苦可以在于一瞬,也可以在于永恒,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差异之于意识本就是一种伪造的欺骗。我们可以因选择痛苦而强大,也可以因强大而选择拒绝痛苦。但这二者本身并无实际差别。这并不是一场无聊的辩论,如果人生可以像辩论一样,毫无理由的选择正反方而后巧言令色地贯之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并为此而沾沾自喜,那么人生将会像辩论一样,无聊而毫无意义。
一七年的整个夏天,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从上海到珠海,从广州到沈阳,南北千余里,东西日落异。我喜欢去酒吧,因为那是一个少有的可以将身心轻易地融入一个氛围中的环境。不论那里,酒吧里总是充满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脸上没有悲伤,没有苦闷,只有在斟满宿醉的月夜里和习习凉风的空街上,间或才可以见到几个许是欢尽而散的漂泊者抑或感情世界分别的异乡人。
有时候凌晨回到酒店,还不是很累,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没有别人的消息,也没有能发消息的人,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刷着朋友圈,在无数个失眠的夜傻笑着,拥抱自己的孤独。有时莫名开心,也有时莫名难过。那些从前吵架的时候总是说着“我与你无关”的人,到头来真的成为了“无关”的你。苦闷过后也许就是痛苦吗?多年以前总是喜爱在作文题记中引用尼采的那句“谁终将点燃闪电,必先长久如云漂泊;谁终声震人间,必先长久深自缄默”的少年如今只能依偎着孤独和衣而眠了。
人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很脆弱,但仔细想想,多愁善感未必不好,赐予我们情感的上天,应该附加着明确告诉人们,情感是一样宝物,不论开心还是悲伤,绝妙的情感体验才是世间一切的色彩与味道。可惜他没有这么跟人们说,所以许多人自己去悟,想明白了,还有许多人永远也想不明白痛苦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只是一味的逃避逃避本身。
和前文尼采的话出处相同,多年后我仍就能想起周国平先生在《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里开篇描述尼采在地中海滨旅程的那一个“山峦海巅”的用词,激发了我对于那位古希腊文老师的哲学和旅行的全部兴趣。如果从那个夏天的最后一次别离算起,许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没什么值得快乐的,当你从一个桎梏中解脱出来时,就是进入下一个枷锁的预备,但,这就是你的自由、你的选择。
让·波德里亚在乌托邦小组(le groupe Utopie)刊物《乌托邦》上发表过一篇《游戏与警察》,一个夏日悠闲地午后,我顺手从书架上拿下来时看到了这么一句虽然不出名但足以立刻让我目不转睛的话:天堂和地狱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只能依照地狱的摸样来梦想天堂。这句话犹如我当年迷茫的状态里所日夜不知期盼的些什么东西似的,让我隐隐产生共鸣,偶尔却又强迫症似的纠正我自己的刻板行为,就像一只动物学家们所说的一圈又一圈在笼子中踱步而不知道这是由于自己巡视领地天性的狼或猎豹一样,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醒悟:原来我们所厌恶的事物对立面却并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
我的那个夏天和她最后一次相见是毕业典礼前,在校的学生们为毕业生送行,我们相见却没有说些什么,心照不宣地走完了最后的流程。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告别,但可能伤感就是这样,总是迟来,没有沉浸在仪式般的分别里,但却总会跌落进回忆的杀手名单上。
那个夏天从一个曾经熟悉的操场,到了另一个以后熟悉的操场。我进入了大学,身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虽然去留和别离总是让人伤感,但更加说不出口的,是每当温热的风吹过面前,温暖的阳光打在肩上,透过桑叶和杨树的阴翳照在地上的光斑默默晃动时,我却想起了那个没有告别、再也不见了的她。我本不想写些什么,因为过多的语言,看起来如此累赘,我也明白早晚有一天我会对这段感情淡忘如纸,但至少眼前,我只怕再不动笔,记忆中那些所剩无几的美好也会被时间默默风干蚕食。有时候,越是感受到痛苦,就越分明地感受到情感的存在,我们的情感,不论是欢愉还是痛苦,惆怅抑或忧伤,都是最好的记忆,最好的礼物。
一年四季其实是有它们独特的味道的。尤其在东北,四季分明,不同季节漫步在路上,会感受到不同的气味。一个晚上,我在大学宿舍的床上躺着,恍然间,发觉到熟悉的气味,那是去年夏天的味道。倏忽,我突然发现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一直觉得每个季节都是有独特的气味的,夏季的最鲜明。
生命中的有些过客,梦醒时才记起你我早已成为陌路人,只是又忽然想起,我们居然未曾道别。我羡慕高中时候的恋情,或许多半我自己就总是陶醉其中吧。人啊,总是会忘掉过去里不好的,只记得过去里那些好的。所以可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
毫无疑问的是,很久之后我会忘记上高中时写过的诗和爱过的人,会忘记毕业那个夏天我做了什么。但你如果问起我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会这样告诉你:可能只有在夏日的午后,才能看到寂静的街。夏天是那么热,反复一切都变慢了,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个常常抱怨炎热的我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夏天的感觉。夏天的恬静全在炎热的空气中偶尔袭来的一阵清凉微风。夏天的安逸都在起床听到窗外点点雨声的清晨。我喜欢在雨中享受一个人的孤独。但是我又不喜欢鞋子被雨水浸湿的潮湿泥泞感。我不知道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你期许的人生是否达到,但我事后才知道的是,这个夏天过后,我活着的方式确确实实的从此改变了。
加缪说: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活着,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的迎像幸福。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呆在喧闹的酒吧里我也觉得周遭如此寂静,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我试着去抚平生活的创痕,后来发现,我还是应该抛弃它,不然对谁都不公正。
一八年五月,夏日前夕,我还是去了她在的那个城市。诺大的大连,我和另外一位朋友四处游逛,也曾在氤氲的海风里彼此畅谈着理想和过往,沉醉在快乐的假象中,勉强让自己感受到一些她生活的参与感。有时我会想啊,究竟什么是后来啊,无非是那个曾经说着娶她的人再也没了联系,就是那对最令人羡慕的情侣分道扬镳、形同陌路。
不过,好在“娶你”那句话,他后来再也没有对旁人讲过。后来遇见了其他人,我永远不敢和她说的是,我那么努力的追你,只是因为你很像一位我生命中阔别已久的人而已。原来彻夜纵欲沉浸在疯狂的欢乐中真的可以麻痹痛苦,不过既然我选择了面对痛苦,我扪心自问:何必一定要找一个人来代替她呢,这样对谁都不公平。
我知道这句话并非原著原意,但我还是会想到《基督山伯爵》中那句颤抖心扉的诘责:“你是不是因为太懦弱了,才这样以炫耀自己的痛苦来作为自己的骄傲?”后来,我想着,既然接受了,就要彻底一些,享受着自己纯粹的感性来源,仅仅为了爱而爱,为了恨而恨,为了忧伤而忧伤。我只好相信《德米安》中说的:“上帝借由各种途径使人变得孤独,好让我们可以走向自己。”一方面,我不认为孤独带我们走向的是自我的灵魂,但事实上,在我凝望孤独只之时,我凝望的其实无非是自己。就像痛苦。我所沉湎的,所抗拒的,所依恋的,所鄙夷的,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东西。
夜深了,纵欲狂欢的人们走出酒吧,面对冷涔涔的漆黑的月时,会不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回想纵然身边朋友万千,终究自己还是一个人。有时候幻灭带来的美丽,远远大于任何得到的魅力。我想起瓦格纳那最富有天赋的代表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貌似沉默却稳健有序的旋律,给人一种明明知道最终悲剧式毁灭的结局却压抑不住内心想继续看下去的力量指引,这就是幻灭的魅力,将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二幕中其实就预示了结局的归宿:神圣暮色的灿烂预感淹没了迷幻的恐惧,带给我们超凡的自由。是啊,自由啊,谁又能对其说不呢?我们有权利选择痛苦,或者回避,甚至是幻灭,而不是得到。
不论是什么时代,我们都逃不过关于生存与命运的思考。其实痛苦和毁灭本质就是生存与命运的形式与质料,情感只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感知工具之一的另一种不直观体现,从生物角度它有益于人类族群的进化与繁衍,而文化上它又是与经典艺术及社会道德密不可分的催化剂。所以,爱的惨烈或者绝望,都是我们情感器官反应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尊重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是我们所以存在到如今的理由。
就像我不期盼太阳,因为我从未真正知道它升起的方向;就像我不艳羡春光,因为它会随时会因阴翳而消亡。这个世界上你自以为熟悉而又美好的事物和人,都真的可能是一场高尔吉亚似的不存在。必然?自由?或许我们还是在宇宙的一隅之中牢牢抱着我们培育出的芦苇草暗自庆幸为好,毕竟那些为阴翳撰写礼赞和坚信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终会带我们走向深渊。只要我们保有思考的能力,我们就还可以继续斡旋而活在这残酷而绝望的自由之中。
最后,我愿借叔本华一段关于人生追求所谓价值或有价值意义的东西的论调——《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暂时的志得意满、由渴望限定的瞬间快感、大量而长期的痛苦、持续不断的挣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互相逃避和追捕、压力、欲望、需求、焦虑、尖叫和怒号;这是永恒的景象,或者等到地球土崩瓦解再重新展开,没有人对这整场悲喜剧存在的原因有丝毫的了解,因为它没有观众,演员也经历着无尽的烦忧,极少有享受,并且只有消极的享受。”来致敬我心中经典名著《生存与命运》中信出版版本的腰封上的话:“逝去的人,活着的人,苦难并没有结束……”
星辰与大海的情愫——秩序与道德
每年六月,牧夫座流星雨都会在高考考生背着星空回家的路上从苍穹的边际掠过。
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坐在小院里看天。微凉的空气从耳边滑过,路基旁花坛怡人的芳香搅拌着醇浓的咖啡,唤醒每个人对宇宙的想象,湮没在黑色幕布中的星月好似随时都会浸入夜空里,偶尔飞过的闪着光芒的飞机渐渐从眼前地上的灯火中逝去在天际尽头。
我喜欢宇宙的一切,天上有好多我们能看到的、看不到的,就像加来道雄笔下的平行宇宙中的物质在我们的空间中聚集到一起,成了丽莎·兰道尔笔下造成希克苏鲁伯大撞击的“元凶”,一切按秩序和轨迹运行着,总让人联想到纵使是人类,也只不过是这浩渺规律中稍稍那么自由一点点的原子和物质而已。我不认同机械的决定论,但有时候我不得不认同拉普拉斯信条是那么的美。
我们或多或少都对星空和大海这种未知的领域感兴趣,多半是因为感到我们自身的渺小和对庞大事物的好奇。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内心有心弦,但最好不要颤动。”每每当我聆听到空灵深邃的钢琴声时,我就会联想起那些雪山之上的漫漫星空,再想想其实我们都来自于那里,我忍不住在心底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妙啊,卡洛·罗韦利说:“我们与世间万物一起,是由同样的星辰塑造的,无论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还是焕发出喜悦的光芒,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论造物主存在与否,我们都是自然万物、宇宙时空一系演化的样子,最遥远的星云和我们身边的世界,都源于斯、长于斯。今天我们看到宇宙星海对灵魂冲击的作用,可能和曾几何时孔夫子川上之感有几分相似吧。
但想想此前我怎么会领教宇宙的美,还是和她有关罢。很难过也很难说出口的是,那个人再也不是她了,经历了这么多,即使她再回到身边,也绝对不是原来的她了。明知如此,我却还是愿意活在过去的快乐中而不是面对痛苦,毕竟前者轻松得多。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常满怀回到过去的期望,不过是因为莫名坚信重新来过会更好。
偶尔也会睹物思人,甚至睹城思人。我时常看着一样东西会走神儿,注视着它,就会想起曾经有它在场时发生的故事,紧接着想到的就会是那些不在身边了的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书店买了一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当时第一次看到那句话还是她拿给我看的,书中引用了歌德《玛丽恩巴德悲歌》的经典独白:“如今花儿已无意绽开,再相逢,又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现在偶尔从书架选书时扫过这本书,最先想起来的已经不是巴尔沃亚从不朽功绩中寻求庇护或者替凯尔卡门感到惋惜,亦或者阿蒙森·斯科特的由来,莫名想起的只是这么一小段在人类开拓宇宙历史中小的不能再小的失败的单相思故事。不过现在我才算明白,我们从黑暗丛林中走来,到了今天,仰仗的正是科学发达的时代我们内心中越来越不被重视的东西——情感。所以也算是今天我才读懂这本书的书名吧。
直到很看过《平凡之路》很多年以后了,我才读懂平凡之路的歌词,原来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拥有和失去,直至失去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才算完美的拥有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有太多我失去的记忆了,也可以说痛苦之处正在于我曾拥有却也曾失去了的东西交织在身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接她的拥抱,记得很多平凡的小事,记得星空下无所事事的散步,记得一切如今看起来那么美好的东西,我尝试过在其他人身上寻找这些东西,可是最终失败了。到头来,我的全部生活就剩下了这半座城。也只有这半座城,没有她的故事,没有她的痕迹。
有人说不快乐就是因为想得太多、想得太明白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接纳痛苦,才能直视意义的消亡,我们相信悲剧,才能珍视拥有的和失去的。年少别离时一吻,眼中噙着的泪花,和现在值班时满地的烟头与镜子里自己不整的长头发,对比过后却说不上哪个更有什么意义,有人嘲笑活在幻觉中的人,但其实世间所有道德、法律、家国,那个又不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呢,我们所信仰的,别人所鄙视的,其实无非都是建立在幻灭之上的宇宙秩序美学的体现罢了。这世间已经有太多的明月清风了,只不过美妙的都在回忆里,逼仄的都在眼前而已。
这世代,谁都有资格抱怨几句怀才不遇啊。我们必须活在秩序之中,哪怕是幻觉,但必须如此,我们可以窥测秩序之外的“真实世界”,但梦蝶之劳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庄子·齐物论》说:是非莫辩。诺姆·乔姆斯基说过:“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活在舒适的幻觉中。”放弃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吧,沉下心来追寻真正的美,其实就在我们内心之中,种德者必养其心,情感就是我们触觉、听觉、味觉、嗅觉、视觉之上的认识工具,我们的情感才是人性最根本的导向,是我们那神性的一部分、理性的一部分、兽性的一部分所未经粉饰的本初之心,何必羞耻于它呢。
薛忆沩在《伟大的抑郁》中曾这样描述爱因斯坦:“他不接受残疾的科学。他敬畏确立宇宙法则并且维持宇宙秩序的上帝。”很多人把尼采说上帝死了的例子搬出来鄙夷宗教,其实尼采和爱因斯坦都深知,他们口中的上帝并不是真正的上帝,敬畏秩序才是真正原因,能从欧洲意义的沦陷中一步步真正走出来的人,除了那些坐在塞纳河畔咖啡馆里的,就剩下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实我们的宇宙,不单单是一个星系和一个星系的时空概念,至少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不是如此,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宙就是秩序的代表,人类花费千年的时间费尽心机地构建起了现代价值意义的体系,从一穷二白创造了道德、国家、宗教、民族、科学,文明的一切来自于文化,文化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所体验过的的最昂贵的体验消费,同时也是对经济最具有刺激作用的基础设施。我们从无数的战争中回看人类的历史,发现人类无非就是想方设法在凭空创造秩序。用情感体会秩序,而不单单用理性,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在做的就像站在庭院里仰望星空一样。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指出自古道德对抗痛苦的两种基本方式,一个同情,二是禁欲主义。迈克尔·坦纳在《尼采》中将其描述为“企图通过剥夺个人再痛苦面前的尊严来消除痛苦”和“企图通过扼杀生命的本能来消除痛苦”的两个“企图”。如果我们将道德纳入秩序的范畴中看它的本质,其实无非就是我们面对所不能逃避的痛苦时,想出的一种“逃避”,说到底,道德还是卡夫卡明智的“逃避本身”而已。可见,道德被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蒙蔽我们的感情,为了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为了让我们不去窥见真正的秩序而忽略了被人类凭空创立的秩序。我们必须从感情中窥见秩序的一隅,不论真实与否。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真实虚假将会使这一切过程变得因具有目的性而可笑之极。寻求目的就是说明我们想要探知意义,而意义在这一局早就被淘汰了,用因果追寻事物、认识世界是人的生物属性限制,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接近终极秩序。王东岳在《物演通论》中提出分化与媾和的观点,强调了宇宙一百三十八亿年演化中递弱代偿的趋势,其实宇宙某些角度上也和人或者生物类似,宇宙从大爆炸之后,也在努力避免着消亡,但存在度降低是万物悲剧的必然归宿,我们建立的一切秩序只是在和终极秩序抗争,包括宇宙演化时建立的秩序,也只是在和终极秩序抗衡,通过丧失一样又一样的“权利”而换取我们的存在度,就像千年前爱琴海边的古希腊人们在想法设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做出的努力如出一辙:我们放弃一些,交给“利维坦”,以便建立一个契约似的秩序。最终到来的不论是热寂还是大撕裂,至少我们寻求秩序的“增熵”环节是不可逆的。
寻找五常先生——生活与生存
宇宙会毁灭只是代表世界的悲剧属性,却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空虚。
如果我们明确失去意味着最终的悲剧,那拥有就是与悲剧抗衡的自由之光。
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开卷有益,但后来才发现,读书就像生活,随意拿起来慢慢品味一本书,看到一半才发现选择的不那么称心如意,再想换一本重新开始的代价却让人望而生畏。到头来,合上这本书,苦和乐只有自己知道。生活可以是悲剧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能是美好的,我们抛弃了生活而为了重新获得生活,正是拥有和失去的关系。许多岁月流走了以后,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曾经日子担忧过的事情现在看来不值一提,曾经岁月拥有过的东西现在看来鞭长莫及。
事实上,生活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能让你忘记它本质的面貌,不过这也未尝不可,毕竟我们用情感理解这个世界,越深刻、越回归人性,情感不意味着反理性,而正相反,情感包含理性,反理性的来自于人本身生物属性的许多限制,那是千百万年来丛林演化的遗留产物。我们的情感不仅包含痛苦,虽然痛苦占绝大部分,但不可忽视的是,还有一部分快乐也来自于我们的情感。
面对美好我们会感到愉悦,比如,我喜欢夏天。因为在诗人的词典里,夏天是如此的惬意而美好。夏天的风是暖的,人是友善的,就连秋风都为你熬过夜,夏晚也为你醉过酒。你可能听过黎明枝头春意和鸟儿歌腔的同时绽放,但你绝对没见过蛐蛐的长鸣声飘荡在湖边翩翩起舞。轻轻的风声划着枝头云儿的船问摇曳的风铃要不要一起去旅行,露天的田野里茂盛的草丛向过往的鸟儿点头致敬,昆虫总是提着黎明的第一盏灯去问叶子借几滴露珠,夏天的生活也总是如此盎然、忙碌和宁静。
生活其实并不应该在于追寻意义是什么,形而上的路有一万种走法,但都不适合意义的命题。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方式,在黑暗中、在灰色世界、在光明彼岸,我们可以像汉芙小姐,像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像眼中只有洛丽塔的亨伯特,甚至可以去像包法利夫人、像安娜·卡列尼娜、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最后,往往我们都活成了斯通纳。正如文景出版的《斯通纳》腰封上写着的:第一眼看故事,第二眼看经典,第三眼看生活,第四眼看自己。好多我们不经意的决定,其实已经在不断的改变着我们的一生。
一八年的夏天,六月的时候,我去了南京。南京和广州都是我因为一场雨而深深爱上的城市。中国的大城市可能找寻不到“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以及“棚屋之间形成的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但内心中常有这样的情愫未免会使得我故意去臆想那样灰色年代的场景。而雨呢,就是一剂良药了。不论是地图上还是从当地人的话语中,很少能听到紫金山的称呼,取而代之的是钟山,但不知为什么,我更偏爱紫金山的名字,可能是因为那个秦皇下令毁其龙脉的段子让我记忆犹新。不论如何,在中山陵台阶的顶端望着雨中的南京,阴沉的天空下可以看到葱郁茂密的森林掩藏着错落有致的现代城市,和一七年夏天时我在白云山上俯瞰广州城时的感觉颇有几分相似。长江从城市西北缓缓流过,下游的长江少了几分激荡和狂妄,多了几分沉稳和城府,从江畔向城中一一数去,甚至可以找到新街口的摩天大厦,情景真与“江上数峰青”神似几分。雨滴打在通往孝陵深处的升天桥石阑上,打在中山先生陵寝的石柱边,打在小红山别墅屋顶上,不禁使人感受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韵味,千百年来,南京就默默屹立在长江之东,历经了建业的赤壁之战,目睹了应天府建文帝的忧伤,陪伴了江宁制造总局之子的童年成长,见证了南京中华民国的世袭罔替。
古往今来,中国自有礼教之说,所谓“五常”者,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礼记·乐记》云: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金、木、水、火、土是也。五常即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论语·学而》有云:温、良、恭、俭、让是也。《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也。其实何为五常?只不过是中国人按传统的表达习惯给许多外在事物赋予的总结性、规律性、启发性、导向性归纳而已。中国哲学不过分强求本体论、逻辑与伦理,更遑论形而上,但中国哲学体系更注重于处世之道、为人之道、齐家治国之道,所以身为中国人,做一个“五常先生”,对生活甚至是生存有独到的间接未尝不可。
意义的解构并不预示着生活的空虚与乏味,我们应该用情感去揣度、追寻生存的方式。情感多数包含着痛苦与苦闷,其次是快乐或者欢愉。抛开造词本意来讲,如果把欢愉和快乐分开来用作表达人类的两种情感模式的话,我想用欢愉来表达接近兽性的乐,而快乐则更多是源自于人的恶的部分,如果单纯表达此种含义,爱恨未免用词过于歧义。
人的快乐不来源于感官和情绪,那是动物之乐,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欢愉”。人的快乐是源于恶。当我们有了私有财产那一刻,恶即产生了,基于欲望带来满足的快乐也随之而产生了。也就是说,人的快乐是来源于再造的秩序之中的,是精神自由的副产品。欲望不一定是恶,但恶一定以欲望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想法的形成,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其生物个体的脑部发育状况或者成长环境,这两者固然重要,但不足以解释人类群体的恶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群体的恶应该来自于财产的拥有和分配,以及后来的交换行为等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这种对于财产,也即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生存资料、发展资料,还应该包括性资源等隐性的欲望载体。所以恶的诞生不是在卢梭《论文二》所描述的私有制诞生的社会状态之时,而应该是更久远之前人类因基因作用争夺雌性资源时的行为。而当恶包含的一部分欲望被以某种形式达成之时,人类就感受到了快乐。平庸之恶也是如此,不作为或者间接故意都是希望达成某种心理满足状态欲求的体现,可以把这种特定的心理状态看作一种特定环境下做出特定行为权利的资源。
而欲望,则是来自于人类心底的。在恶之前就有了欲望。况且恶也不应该被带有道德含义,毕竟根据上文的定义,恶产生的时刻人类还没有能力构建起道德的秩序。这一词汇在这里只是用做描述某种客观状态而非道德概念。说回欲望。恐惧催生欲望,但这绝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也就是说恐惧不能够作为所有欲望的诱因,但可以看作催生一些欲望的结果。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对欲望的定义其实要显著晚于它存在的时刻,但这并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先后概念,而应该是道德秩序层面的、具有说教意义的“欲望”被定义之时,欲望的真正且更广泛含义的本体早已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二者应该处于同一时间层面的相互影响、制约关系。纵观生物进化历程,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欲望的产生与达成,不论是否是道德构建的秩序层面的产生,或者达成。我们讨论的反道德以及犯罪行为都只局限在再造秩序的层面而非终极秩序之内。
欲望的满足影响了我们情感的变化,我们之所以时常感到痛苦,很大原因是我们的欲望过多而达成过少。我们太想着去达成欲望了,以至于有时候会做一些梦,就像佛洛依德《梦的解析》说的那样:梦是愿望的达成。我们面对欲望感到痛苦,但痛苦却是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如果按比例算的话,绝对远远大于快乐。但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去用道德的再造秩序去干扰痛苦的实现,比如禁欲和同情。我们大可以面对生存的现状,例如农业社会长期困扰人们的食物问题,我认为和长久的忍饥挨饿比起来一顿饱餐一瞬得不值一哂,就像一世卑微之于前者铸就的一刻钟的伟大。饱餐之后便是无聊,伟大之后即是空虚。痛苦是永恒的,因为世界是悲剧的,所以挽回的效果并不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往相反方向去压抑欢愉或者快乐应得的空间,。只是坦然的去面对生存就可以了。
痛苦总能促使一部分人去追寻秩序,因为人类社会中必然有一批热衷于再造秩序的人,否则人类远远取得不了今天的成就,秩序之于我们是有益的,但在不同秩序面前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人自从匮乏之时就开始追寻平等,然而人越是富足,就越背离平等。但我们必须从富足这条路追寻平等,而不是回归匮乏,尚未到来的平等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即是尚未真正富足。所以秩序将要继续再造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生存的前提是不要忘记人类再造的道德秩序、社会法律秩序、政治秩序、宗教秩序、民族秩序背后的宇宙秩序和终极秩序。
我们如此详尽的讨论情感的诸多因素对于我们生存与生活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近年来“理性”的呼声被吹捧的太高。当人们认为理性与科学精神挂钩的时候就难免会想到增长的经济、创新的科学发明、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甚至反过来鄙视情感只不过是“儿女共占巾”的儿女情长,认为感性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存续下来的基因作用。但其实理性远远不能代表这么多,感性也不止如此。理性不应该与情感混为一谈,理性对应知觉,感性对应直觉,真正的创造多数源自于感性而构建价值体系则交付于理性。而情感,则属于更广泛的话语体系,应该包含直觉与知觉。尼采的处子作《悲剧的诞生》中评价苏格拉底之时这样描述直觉与知觉:“直觉智慧在这个完全反常的性情中出现,只是为了在某些地方阻止清醒的认识。在一切创造者那里,直觉都是创造和肯定的力量,而知觉则起着批判和劝诫的作用。”无独有偶的是,早于尼采和苏格拉底二人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斯认为宇宙代表知性,而宇宙即是秩序。用尼采的话说:“批判、劝诫”构建了宇宙的秩序。
人类情感是自由意志的重要表达途径之一,但很难说人类情感和行为背后生物决定的比重。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层面自古以来就不断争论的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在本体论方面探讨从未停歇,但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哪一方,人类意识的自主能动性几乎成为哲学意义上普遍承认的基础(拉普拉斯信条除外),但另一方面,近年来生物学、脑科学、神经医学的发展将事情的发展方向越推越远,在科学层面上,自由意志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有部分专家认为自我意识可能是一种幻觉,甚至是资源浪费。因为人的行为决策源自于基因和大脑的化学变化,未来人的行为决策可能会听从于人工智能的最优安排,人的行为决策还受到社会环境和心理暗示的广泛影响。但抛开哲学或者科学的高度,俯瞰我们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活中充斥着的痛苦事实严重激发了我们的痛苦情绪,如果说我们的情绪来源于生物化学反应,但事实毕竟客观存在,即使是外界刺激,每个人的反应也不同,故而我仍是自由意志的坚定信仰者。但就像我们第一段所说的,自由意志,其实并不那么自由,我们称之为痛苦而绝望的自由下所做出的抉择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人类是亘古以来最为追求精神自由的族类,沉湎于优越感的陶醉是我们创造精神的本质心扉,但是创造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从鸿蒙初始那一刻即开始受限于我们的创造。精神既是我们的成绩单,也是我们的病原体。基于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将永远囚禁在此怪圈的桎梏之中。我们已精神自由为傲不假,但我们也因精神自由而丧失自由的本真。我们用自由意志创建了秩序,但我们的自由意志却最终困在了再造的秩序之中。就像卡夫卡这位明知而伟大的作家所说:“精神只有在不成为支撑物时,它才会自由。”
《索洛维约夫文集》中说:“人的意识和生命的二重性是一切思维和哲学的真正基础,人在自身中既有内在自由的感觉,也有外部必然性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存与生活过程中,必然体验到自由的感觉,即使这种概念还未被赋予定义,同时自由发生的维度是人的生命和意识中最本质的状态下,但还要受到秩序的制约。所以真正追寻无限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不存在的,我们建立了秩序,就必须从秩序中窥测外部世界的状态,而不是超越再造的秩序而直接达到所谓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带着枷锁,但毕竟确实还是存在的,就像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说的:“自由是确实有的,但是不可被界说的。”我们用知觉与直觉探寻和认识世界,但这本质上还是属于情感工具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生存的工具应该分为三层,最先是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味觉,其次是自由意志主导下的直觉与知觉,而后是人性意义下的情感工具。纵使我们的自由对于我们本身既绝望又有限制,而且各种科学的进步还质疑了它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有一部分科学的发展佐证了其消失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与生存,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恰恰是“自由”。但即使是这样,这个工具也被我们运用的得心应手甚至不可放弃,就像艾米莉·狄金森所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我想用“得到”上怀沙解读的特德·姜的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来结束这段论述:去开启一段注定会分离的感情,去孕育一个注定会早逝的生命去拥抱她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
2018.8.25戊戌年七月十五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