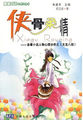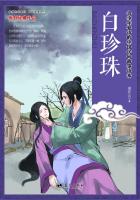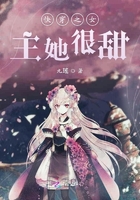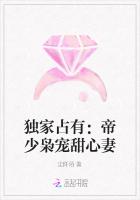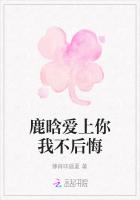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而且“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30]。不过,陶渊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认所达到的并非一种理论的深度,而主要表现为一种感受和体验的深度,他对有限与永恒、存在与意义的把捉,也不是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其心灵的深微体悟,说到底,陶渊明并不是一位诗人哲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他的全部作品所展现的不是一种深刻严谨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超旷的人生态度,一种洒落的生命境界。形成他这种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丰富而又复杂,他到底应属于儒还是应归于道,思想史家和文学史家们一直在打笔墨官司。有人认为“渊明所说者庄、老”[31],“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32],“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33];有人则认为“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34],“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35],“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36];有人说他“实外儒而内道”[37];又有人说他“实内儒而外道”[38]。然而,陶渊明既无擘肌析理的理论兴趣,更无意于谨守学派门户,非儒即道的划线固然失之武断和偏颇,调和折衷的“内”“外”之分也稍嫌笼统和空泛,甚至割裂了这位伟大诗人生命存在的浑融完整——好像他的为人和为诗尚未臻于和融澄明的境地,却骨子里一套而外表另一套似的。相比之下,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倒较为通达:“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39]鉴于陶渊明应对人生世事的方式是体验,诗文呈现的是体验的意绪和生命的境界,本文不拟罗列他诗文中的用典来源及其多寡,也不仅仅对他施以抽象的理论剖析,而是经由对其生命境界特征的揭示,进而探寻形成这一境界的文化底蕴,看看儒道文化各自在什么层面参与了他的精神建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命存在。
一
清人锺秀论陶首标“洒落”[40],“洒落”二字的确道出了陶渊明生命境界的主要特征。南宋陈模早已称道过陶渊明的“胸次洒落”[41],稍晚于锺秀的毛庆蕃也对陶渊明的“素怀洒落,逸气流行”赞叹不已[42]。大概是晋人开始用“洒落”一词来描绘树叶的摇落飘零之状,如潘岳《秋兴赋》:“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43]稍后又被用来形容超然物外的情怀,如郭象《庄子注序》称道庄子说:“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44]郭象此处的“洒落”是做动词用,意思是“使之……洒落”。人们又用它来形容人自然脱俗和潇洒飘逸的仪表风度,如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竺法雅》称雅“风采洒落”[45],《南史·萧子显传》说“子显风神洒落,雍容闲雅”[46]。就现存的文献看,以“洒落”来形容人内在的心灵或精神状态最有名的例子当是黄庭坚《濂溪诗序》中的一段话:“舂陵周茂叔(即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引者注)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47]以“光风霁月”状“胸中洒落”,可见,“洒落”在这儿主要是指一种澄明、淡泊和旷远的心境。后来,“胸中洒落”成了宋明理学经常讨论的话题。在宋明理学中,“洒落”与“敬畏”是彼此相对的两种人生境界,“敬畏”则戒慎提撕,“洒落”则旷达自得。王阳明对二者曾作过清晰的界定:“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放荡旷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48]“洒落”一词因而也染上了道学色彩。从宋至清的治陶者和诗论家如陈模、锺秀等人赞美陶渊明胸次洒落,显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黄庭坚评濂溪一语的影响,但他们各自“心目中所摹拟”之“洒落”又显然不尽同于黄庭坚所“摹拟”的“光风霁月”,如毛庆蕃的“素怀洒落,逸气流行”除了指陶渊明心境的澄明、淡泊、旷远以外,它更侧重于生命的超然这一层面,所谓“逸气”就是指陶渊明摆落了世俗羁绁后那种超脱的人生韵味。陶渊明的洒落无疑有别于道学先生周敦颐。《饮酒》之五就是他洒落胸次的生动展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由于精神已超然于现实的纷纭扰攘之上,心体原本不累于欲不滞于物,何劳避地于深山,何必幽栖于岩穴?结庐人境无妨其静,车马沸天不觉其喧,环境虽然随地而有喧寂之别,诗人的心境绝不因之而有静躁之分。宋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将陶渊明与王安石作过有趣的比较:“王荆公介甫辞相位,退居金陵,日游钟山,脱去世故,平生不以势利为务,当时少有及之者。然其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既以丘壑存心,则外物去来,任之可也,何惊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如陶渊明则不然,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然则寄心于远,则虽在人境,而车马亦不能喧之;心有蒂芥,则虽擅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也。”[49]陶渊明心体自足无须外求,结庐人境,采菊篱边,哪用得着去“擅关中”或“擅丘壑”呢?寄迹于人境之中,何妨神游万象之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评论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为什么改“见”为“望”就使“一篇神气都索然”呢?诗人心如明镜朗鉴万物而不存有万物,见南山之前胸中并不曾有一南山。“望”属有意——好像诗人自性亏欠而求助于外,特地在寻求美景的刺激,“见”则无心——诗人的自得之趣存乎一心,丝毫不关乎见不见南山,其胸次的“悠然”不在于见南山之后而早已现于见南山之前,是“悠然见南山”而不是“见南山”才“悠然”。既随意而采东篱的秋菊,亦无心而见远处的南山,这是生命自身的嬉戏与自娱,是精神无拘无束的自由与洒脱,是心灵纯洁无染的怡乐与恬适。山间缭绕的山岚是多么自在,日暮“相与还”的飞鸟何其从容,此老眼前的南山、秋菊、山气、飞鸟无一不是佳景,此老胸中的结庐、采菊、见山无一而非乐事。此诗决非如古代论者所说的那样前四句写“迹寂寞”,后四句写“心寂寞”[50],或者如许多现代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全诗先写心,后写境,将心与境先分成两截然后再连成一片。诗中的境由心起而不是心由境生,是“胸有元气,自然流出”[51],是因有自得之乐而采菊见山,不必有待于采菊见山才获自得之乐。诗中的“真意”注家常引《庄子·渔父》篇以为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并据此将“真意”释为“自然意趣”[52]。“真”属于道家的景观当然不错,但就此诗而论什么是“自然意趣”呢?能否把结庐、采菊、见山说成是“自然意趣”?至于把“真意”说成是“人生的真谛”或“人生的意义”的种种解释,则又将诗中的“真”混同于认识论上的“真”。其实这里的“真”不是逻辑上的“真”而是“存在者状态”上的“真”,“此中”的“此”是“此在”“在”“此”的“此”,“此中”就是存在者“在”当下的此时此地之中。由于诗人既不滞于物欲又不累于功名,摆脱了一切俗缘的遮蔽,自己存在的本真状态,就在“此中”显露敞开。已复其“真”的诗人与各得其所的万象猝然相遇,只见南山耸秀,秋菊迎风,山岚飘拂,夕鸟飞还,顿时一片化机,天真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这是诗人生命存在的自由洒落,也是他本真存在的澄明朗现。可见,陶的“洒落”是指他脱落了一切功利、声名、计较、俗虑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无目的无利念的洒脱,无所关心无所欠缺的圆满,也就是其生命超然无累的自得与自适。
这首诗展露的是儒者的胸次还是道家的襟怀?一般而论,儒家强调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要求个体通过人格的自我完善,担当起巨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让自己走完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一被规定好了的人生历程。道家则主张放弃一切社会责任而“任其性命之情”[53],鄙薄那些“弊弊焉以天下为事”[54]和“伤性”“以身殉天下”的“圣人”[55],其终极取向是解脱社会的束缚与礼法的拘忌,以超脱社会、超越自我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洒落”的胸襟看来有别于儒家悲天悯人的入世情怀而近于道家旷放自适的逍遥态度。但是,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儒学也包含了不同的精神向度,孔子在提倡“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敬畏戒慎之外[56],同时又非常激赏“吾与点也”的自在超然,为宋明理学家所乐道的“胸中洒落”已经蕴含在先儒的精神资源中,所以后世不少论者认为陶渊明的“洒落”深契“曾点之意”,他深心体贴的仍是儒者的襟怀。陶渊明的《时运》一诗也许是这一论点的极好佐证: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诗前小序说:“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这首诗抒写暮春独游之乐。在一个“景物斯和”的良朝,诗人穿上刚缝制成的崭新春服去东郊游览,只见微风吹散了山间的薄雾,天空点缀着淡淡的白云,和风轻轻拂动田野嫩苗,郊外的风物那样清新静美,诗人心情那样恬适和悦。“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二句“写出性情”[57],在鳞鳞湖水中“乃漱乃濯”,远方美景惹他“载欣载瞩”。序言说这次春游“欣慨交心”,“前二章为欣,后二章为慨,此大始末也。‘迈迈时运’,逝景难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恨殊世’,本之‘我爱其静’,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回环也。载欣则一觞自得,人不知乐而我独乐,抱慨则半壶长存,人不知慨而我独慨,此又一回环也”[58]。这儿没有政坛的血腥倾轧,没有人际的尔虞我诈,他再也不必为功名利禄而劳碌奔波,再也不为侍奉上司而折腰作揖,此情此景使他打心眼里“称心易足”,悠闲地“挥兹一觞”更是其乐融融。这使他想起当年孔子“吾与点也”的情景,自己眼下所享受的这种人生怡乐不正是曾点当年所企望且为孔子所赞许的人生境界吗?清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一中称许此诗“能会曾点襟怀而发为尧、舜气象”。诗中“春服既成”“童冠齐业,闲咏以归”隐括《论语·先进》中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一则对话: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59]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所言,或者勇于事功,或者娴于礼乐,分别秉承了夫子济世与修身之志。想不到孔子虽然没有贬斥和否定前面三位弟子的人生理想,却把由衷的赞叹和嘉许给予了那位只想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的曾点。从拯世济民的层面来讲,孔子当然注重事功与道德,从个人的人生境界来说,他又更看重“曾点之志”,并把这种精神的超然怡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这一则对话中孔子四个弟子所谈的人生理想,在精神层次上一个比一个为高,道德的境界高于事功的境界,存在的境界又高于道德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外智者所见略同,费希特把人的精神分为“五个高低不同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即使具有较高的境界,站到了道德立场上,不论他有多么高的德性,也总盼望自己的行动能取得实际成果。可是外在成果永远是没有把握的,对于成败,人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只有摒弃对外在成果的指望,内向于自己本身,以求心安理得,自己才与本源同一,这才是站到了宗教的立场,这时,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才能享受陶然自得的‘至乐生活’(Seligesleben)”[60]。费希特这段话能加深我们对曾点之意和陶渊明诗中“陶然自乐”的理解。不同的是,费希特对事功和道德的超越最终导向了向上帝的皈依,而曾点与陶渊明虽超越伦理但并不走进宗教,而是将个体生命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之中——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一体。朱熹将曾点之意阐释得最为深透贴切:“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61]曾点既不像子路那样汲汲于功名,又不像公西华那般拘拘于礼节,脱略了一切俗缘、功利、计较、顾虑、欲求,无所利念其人生自然便超旷,无所欠缺其生命自然就洒落,这是费希特所谓摒弃功名欲望以后的“至乐”,也是朱熹“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的自得之境,同时,这也正是陶诗中的“称心自足”和“陶然自乐”。个体“人欲尽处”就会显得充盈自足,就能与天地上下同流,并因其与天地合其德而生机盎然,自逸自乐。
陶渊明神往并已达到的就是这种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跨过历史的通道与曾点深心相契,甚至达到了与其“寤寐交挥”的程度,并为“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而惋惜抱恨。清张潮等人在《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中说:“浴沂之志,尼父已与曾点。千载而后,复有知己,靖节若在圣门,与曾点真一流人物。”从《时运》序文“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与《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来看,不只说明陶渊明与曾点所使用的语言相同,主要表明陶渊明已将曾点所描述的人生理想变为自己现实的人生体验,他真可谓曾点“千载而后”的“知己”。他像曾点一样“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完全放弃了事功的奔竞,如果天天想着立德立功立名,“将此事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不可能成为曾点的“殊世”同调,他一如曾点“只管对春风吟咏,肚里浑没些能解,岂不快活”[62]。“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林,浊酒半壶”,写的是诗人将“事事放下”后的轻松,是他胸中不著一事的自在。
由于他将曾点的人生理想变为自己现实的人生体验,所以陶渊明对“曾点之志”有一种独到深至的体认,“从来说曾点为狂,不曾道破静字,今始拈出,深心体贴,俗人不知”[63]。儒门一直将曾点的人生态度称为“狂者胸次”,《孟子·尽心下》将曾点作为狂者的代表:“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来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如何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名点)、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64]相反,陶渊明认为曾点之志的本质不是“狂”而在于其“静”:“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明锺惺评这几句说:“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65]为什么高人旷士少不得一“静”字呢?“静”的反面为“躁”,“躁”表明个体还有所欠缺、有所欲求、有所渴慕,心灵还处于一种栖栖遑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洒落得起来呢?陶对“静”与洒落的内在关联可谓别有会心,他在诗文中经常谈到自己对“静”的偏爱,如“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静”是不妄想不妄求时个体和谐自足的心理状态,它是个体洒落的必要条件,就其无所欠缺而言也是洒落本身。在这一点上儒道走到一起来了。
朱熹几次说过“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曾点有老庄意思”[66]。庄子的逍遥游虽然被他描绘得气度恢宏缥缈玄远,但其实质仍是一种精神的闲适自在、清虚恬淡之乐,逍遥不只是“乘物以游心”[67],而且是“游心于淡”[68]。实现逍遥游的前提是“无名”“无功”“无己”[69],或“外天下”“外物”“外生”[70],摆落一切欲望、功名、算计、利害,做到超社会、超功利、超生死,物我两忘,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而“游乎四海”[71]。断绝俗缘忘怀物我的方法是通过“心斋”以达到“虚静”:“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虚而待物者也。唯物集虚。虚者,心斋也。”[72]也只有“静”才能感应天地朗鉴万物而与道同体:“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73]
陶渊明不以曾点为“狂”而目之为“静”,说明他对洒落有独到的体验与洞见,也说明儒道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的感知意向。曾点与庄周本来就有些“相似”,这种“相似”不仅表现在洒落与逍遥都呈现为“闲静”或“虚静”的心理状态,更在于它们都以不依赖外物为其条件:洒落必须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下文对此将有详细讨论。逍遥游同样要求“无待”,《逍遥游》中从“水击三千里”的鲲鹏到起止于枋榆之间的鷃雀,从耿耿于世俗毁誉的俗人到“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都不能实现逍遥游,只因为它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待的。洒落与逍遥都是充盈自足的生命本体的自得自适、陶然忘机,因而,陶渊明的生命境界既近于儒也近于道。一直想把陶渊明儒化的明清学者对此也似乎拿不定主意,如方东树在分析《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一诗时说:“此但书即目即事,而高致高怀可见。起四句言地非偏僻,而吾心既远,则地随之。境既闲寂,景物复佳。然非心远,则不能领其真意味,既领于心,而岂待言,所谓‘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言’,有曾点之意。”[74]引文中的“造适”二句见于《庄子·大宗师》:“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75]庄子这段话是描述一种适意自得而忘怀物我,一切听从自然的安排而委运任化,并与寥廓的天地同一的境界。方氏认为陶渊明既近于庄子所写的“真人”也有似儒门的曾点。郭沫若曾断言“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76],甚至“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77]。从其超社会、超事功、超伦理以使心体一尘不染,使生命存在得以自足、自适、自得这一层面看,曾点与庄子的确有其相通之处。陶渊明的洒落之境是庄子之逍遥与“曾点之意”的完美结合,既近于儒也近于道,同时又不同于儒也不同于道,他是在融汇传统的儒道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生命存在。
一方面,陶的洒落与庄的逍遥在境界上相通而又不同:相通在于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伦理和自我的超越;不同在于庄反社会而超社会,反伦理而超伦理,陶则在世而又超世,属伦理而又超伦理。由于反社会反伦理,庄子逍遥游的承担者只是那些吸风饮露的“神人”或“至人”,这种逍遥游也只能到“无何有之乡”[78]“四海之外”[79]或“无穷”的寥廓中去寻觅[80];由于不离人伦日用之常,陶渊明的洒落在当下即是的“人境”或“东篱”就可实现。“结庐在人境”——好像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回响[81];“而无车马喧”——似乎又是庄子“彷徨乎尘垢之外”的同调[82];他在对人境的超越中又充满了人际关怀。清方宗诚在《陶诗真诠》中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83]另一清代学者张谦宜也称陶诗既“字字高妙”又“句句近人”[84]。由于有儒家对人世与人生的执着、热爱作为根基,陶渊明比庄子更淳厚更朴实,他的洒落虽不似逍遥游那般汪洋恣肆,但也不似逍遥游那般诡谲荒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起“乘云气,御飞龙”的逍遥游要平实而亲切[85]。
另一方面,由于同样深刻地受到庄子逍遥游精神的影响,陶渊明比曾点更少拘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他的洒落比起曾点的清沂舞雩之乐更加脱略形迹,更加超脱旷远。当然,就其既超脱又平实的人生韵味来看,陶渊明更近于儒门的曾点。尽管他在《止酒》一诗中声称自己“逍遥自闲止”,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倒更能与曾点“寤寐交挥”。因此,我们将他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标以“洒落”而不目为“逍遥”。
二
陶渊明自然不可能一辈子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天地同流”或“与道冥一”,对于人这种社会存在物来说永远只是一种短暂而超然的心灵体验,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面对社会和个人的许多现实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扰、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纠缠,还得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而痛心疾首,为“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同上)而愤愤不平,为“六籍无一亲”(《饮酒二十首》之二十)而忧心忡忡,因“草盛豆苗稀”而负耒躬耕。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的重量,临终前还慨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明末锺惺责怪人们只知“陶公高逸”洒脱的一面,却不了解他“竟是一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人”[86]。到清代沈德潜、锺秀等人都说“晋人多尚放达”,独陶渊明秉持儒家“忧勤自任”的精神,“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87]。“忧勤”既是他“洒落”的对立面也是其“洒落”的补充。那么,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的呢?在走向洒落的过程中,哪家的文化精神左右着他的心灵感知和存在决断?
陶渊明一生可能同时面对许多难题,但我们的考察得从一个一个的难题开始。
首先他得消除穷与达给他精神上带来的烦扰,在他心灵上造成的紧张,否则他的人生就难得洒落自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的经历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壮志,有过“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之五)的豪情,也有过“慷慨绸缪”(《杂诗十二首》之十)的雄心。《命子》一诗据王瑶考证约作于其三十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追述其先辈的勋业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唐氏在中国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和荣幸,从“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的昌隆,数到“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的伟业,再说到陶侃“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显赫,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励,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拟古九首》之八
此诗思致奇幻缥缈,诗旨归趣难求。古代的治陶者见诗中提到夷、齐和荆轲,便以为是流露“忠君报国之念”[88],今天的学者见诗中提到北方的张掖、幽州,便断言“本诗的主题思想”是“抒写统一的爱国理想抱负无望实现的悲愤,发泄对东晋苟安江南的深刻不满”[89],对东晋王朝尽忠或“对东晋苟安不满”这两种主题虽然彼此相对,但它们同样都将这首诗过度政治化了。诗人在此诗中不过是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节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的实录,在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并不是借以明其“恢复国家统一的理想”[90];“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也只是明其节义侠骨,并不一定是要“为晋一明大义”[91]。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九、十两诗中,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夸父“与日竞走”渴死途中,刑天“舞干戚”未能取胜,精卫“衔微木”也不足以填海,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其《拟古九首》之二说:“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论者多以为此诗表达“公盖深欲效田畴之忠于晋室,而鄙当时附宋者之为狂驰也”[92]。这首诗的落脚点不在于事不事二姓的忠逆问题,而是强调要像田畴那样以节义求万世名,清方宗诚对此别有会心:“《拟古》第二首:‘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此本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之意。”[93]儒家通过功德圆满来实现不朽的思想对陶渊明有深远的影响:“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屈贾》)他把“进德修业”“如彼稷契”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生命取向,并把它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存在课题。这使人想起诗圣杜甫的咏怀:“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94]一个希望“如彼稷契”,一个“窃比稷与契”,陶渊明与杜甫的自期何其相似!毫无疑问,是相同的儒家文化精神塑造了这种相似的襟怀。陶渊明在《荣木》诗前的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此诗将进道修业、建功立言的志向放在“人生若寄”的生命背景上来抒写,诗中的感情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慷慨激昂,表达了诗人对于“四十无闻”的怅然愧疚,以及不甘于寂寞“无闻”的振作进取。黄文焕对这首诗的情感与结构有十分精当的分析:“四章互相翻洗。初首憔悴怅念,若寄之人生,与夕丧之晨华同脆,无可自仗,说得气索。次首拈出贞脆由人,有善有道,可仗俱在,不须念怅,说得气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敦,怛焉内疚,倍于怅矣,又说得气索。卒章痛自猛厉,脂车策骥,赎罪无闻,何疚之有?又说得气起。”[95]诗人在“徂年既流,业不增旧”时痛责浮生,警策自己“脂我名车,策我名骥”,这显然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