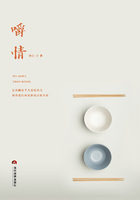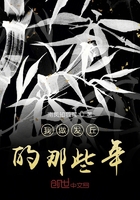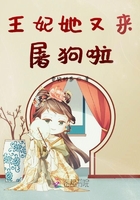陶渊明一生何曾有财富“过足”的时候,可他在此诗中竟然“贫人夸富”[124]:“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身处贫贱却精神充盈,全诗都是抒写自己自得与自足的人生体验,如“回飙开我襟”的惬意,“息交游闲业”的闲适,“酒熟吾自斟”的悠然,还有“弱子戏我侧”的天伦之乐,难怪吴瞻泰在《陶诗汇注》卷二中说,此诗所写的精神境界“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一洒落”[125]了。唯其不以贫贱而慕于外,不因富贵而动于中,陶渊明才会真正感受到人生“真复乐”。
如果说儒家“君子固穷”“素而不愿”的节操使他解脱了贫与富的困扰,那么,在“代耕”还是“躬耕”的问题上,陶渊明则纠正或突破了儒学的偏颇和局限。儒家的传统鄙视躬耕稼穑,《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26]孔子恶声恶气地骂“请学稼”的樊迟是“小人”,孟子也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之“禄足以代其耕”[127],因而士之不仕亦犹农夫之废耕,二者对于各自的身份而言都是一种失职的行为。陶渊明却“不以躬耕为耻”[128],“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的人生经历使他对耕植有一种朴实的体认,对那些勤劳的“陇亩民”由衷地亲近,对那些“曳裾拱手”者则十分鄙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劝农》),这是在劝农耕也是在表心迹,清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九中说:“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129]魏晋那些出言玄远却不辨菽麦的士子,声称自己非汤武薄周孔,恰恰将孔孟鄙薄稼穑的偏见作为自己的成见。陶渊明反问这些一方面“宴安自逸”一方面耻涉农务的士子说:你们面对那些“宵兴”“野宿”的桑妇农夫“能不怀愧”(《劝农》)?解缨归田后的诗人明白,如果自己不“勤陇亩”便要“饥寒交至”(《劝农》),在《移居二首》之二中他还提醒自己说:“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清陶必铨认为这是陶渊明远承乃祖陶侃的遗风:“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绍长沙之勤慎,异晋士之玄虚欤?”[130]由于对治生和农耕怀有这种忧勤的心态,因而他不但像老农一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共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之二),而且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除了种豆、获稻、灌园等田园耕作以外,还兼织席子、打草鞋、卖蔬菜,他的朋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灌园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田园耕作并非那些“曳裾拱手”的诗人所想象的那般闲逸,它不仅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苦,还得为“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五首》之二)而忧心,更要忍受耕不救穷的饥寒之苦,即使他勤于陇亩仍不免“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是陶渊明对自己躬耕的人生选择毫无怨悔:“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十二首》之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诗人表露了何以选择躬耕的衷曲: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
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衣食”,而“衣食”之谋首在躬耕,“孰是都不营”会使身心不得安宁。谭元春说“每诵老陶真实本分语,觉不事生产人,反是俗根未脱,故作清态”[131]。对力田耕作这种“真实本分”的体悟使诗人不惧四体疲劳,不辞田家辛苦,不避霜露严寒。勤劳和汗水换来了他那种踏实的生命感,看他“盥濯息檐下”时神情如此安祥,“斗酒散襟颜”时心境那样舒坦,因此锺惺在《古诗》卷九中说:“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一段忧勤中讨出。”[132]此诗虽句句不离耕作衣食之忧,却字字逸出自在坦然之乐。《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同样也表现了这种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贫居”不得不“依稼穑”为生,但“依稼穑”又不能救“贫”。尽管他及时力田不误“春作”,可仍难免“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有会而作》)的饥乏。不过,陶渊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看他“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的劲儿,简直抑制不住对新谷登场的喜悦和期盼;“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他此时的心情也和“清壑”中的小舟一样轻快;“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从这些喜气流溢的诗句中不难想象诗人的兴奋。他归田躬耕至此已有十二个年头了,虽然这十几年里没少受饥寒之苦,虽然他如今“姿年逝已老”,可他一直没有间断过田园耕作,并乐意以躬耕终老。明谭元春称这首收稻的农耕诗“无一字不怡然自得”[133]。躬耕真正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充实与快乐。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也是写躬耕之乐,不仅两诗“通首”都“气和理匀”[134],诗中还有“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些古今传诵的佳句。早春的微风轻轻拂过田野,随风摆动的嫩苗好像也满怀喜悦,鸟儿叽叽喳喳欢快地迎接“新节”,秉耒春耕的诗人更有说不尽的欢欣。“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躬耕对他不仅不是一种羞耻和苦役,反而是一桩难得的乐事,是生命的一种快慰与欢娱。“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管年尾的收成丰歉如何,就是躬耕的过程本身也“多所欣”。上首诗写秋收的喜悦,第二首写春耕的欢欣。诗人何只是从躬耕谋生的忧勤中讨洒落,这种忧勤本身就已变成洒落了。
诗人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的结尾说:“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聊为陇亩民”正好表明陶渊明并没有把自己混同于“陇亩民”,他对自己的士人身份十分敏感和自觉。他乐于躬耕除了衣食之谋外,还有对人格完成的执着与关怀。孔子认为君子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135],将人性的完善和人格的完成拘限于诗书修习和礼乐训练,躬耕既“馁在其中”又有碍人格的发展,他所忧之“道”因而悬浮在远离现实人生的半空。陶渊明敬而远之地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既志于“忧道”又不能不“忧贫”,所以他选择“志长勤”的存在方式,与孔子恰恰相反,他把躬耕作为一种忧道守节的重要途径,他多次说自己躬耕“所保讵乃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之一),“量力守故辙”(《咏贫士七首》之一),“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不以躬耕陇亩为耻,自不以媚世趋俗为荣。明沃仪仲认为陶渊明的躬耕“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136]。此话稍失偏颇,只强调了他躬耕忧道的一面而忽略了谋食的一面,陶既通过躬耕经营“衣食”,也通过躬耕“忧道”“保真”。形体虽然拘系于田园农舍,换来的却是形神超越;“戮力东林隈”的辛勤耕作,换来的是生涯性情的洒落怡然。
四
“俗网易脱,死关难避”[137],可以把功名、富贵、利禄、得失看作是外在于生命的“非我”而超脱它们,但生命本身却是自我存在与同一的根基,所以王阳明说:“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因为“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138]。不戚戚于贫贱未必就能不戚戚于死亡,然而,仅仅挣脱俗网而不能超脱死生其人生还是难于洒落。
和魏晋的许多士人一样,陶渊明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对个体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和自觉,对光阴的倏忽易逝心怀忧惧:“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这种意识是如此强烈,面对美景佳人反而惹起他满怀愁绪:“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九首》之七);岁月的推移也增加了他的惶恐:“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对自己趋死而在的这种必然归宿的体认更让他焦虑不安:“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甚至眼见乡邻故旧的死亡也使他感悟到生命的短暂和偶然:“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
怎样摆脱这种生死的束缚呢?陶渊明否定了肉体的长生不老:“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形影神》)。采药炼丹以求长生不仅无补于事,即使肉体能够如愿长生不老,在诗人看来这种个体在时间上的单调重复必然使生命显得苍白无聊:“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八),何况并没有什么“寿世之术可以长恃,然纵至于不死不老以至万岁,不异平常,则神仙亦属寻常耳,何足贵哉”[139]!同时他也否定了死后的荣名,荣辱毁誉对于已经消亡了的个体来说都毫无意义:“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首》之四),“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在临终前回顾平生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他认为不能指望通过养生或求名来超越生死:“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二十首》之十一)颜、荣以名为宝,客以千金躯为宝,可是身、名都不可久恃,因而总不如以“称心”为宝。
诗人这种对生命的体悟在《形影神》三首诗中抒写得最为精彩动人。诗前的小序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诗中的“形”“影”“神”分别代表个体超越生死的三种不同态度,代表在面临死亡深渊时三种不同存在方式的价值取向。“形”在意识到“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这一“必尔不复疑”的人生结局后,主张人生应该放纵感性以及时行乐,既然无望长生就得穷尽今生:“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影神·形赠影》)“影”则认为在“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的情况下应选择求名,不能使躯体长存就得让精神不朽;求名的最好途径莫过于立善,血肉之躯虽不得不与草木同腐,通过立善则可让荣名在历史中长存,形固不能久生而名尚可久传。“影”认为“形”纵酒行乐的人生取向毫不足取:“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答形》)最后“神”以自然之说力辨“形”“影”“惜生”之非:“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破立善求名,“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破求仙长生,“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破纵欲长饮(《神释》)。诗人认为个人的生命无永恒可言,因而他没有渴望个人不朽的冲动——不管是躯体的长生还是美名的长存。他将超脱生死与超越自我联系起来:个体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与天地同流的高度,一己的生命便能与天地同在;将个体冥契于自然同一于万物,便不会因生命“从古皆有没”而“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便会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洒落超然。
魏晋儒学价值大厦的崩溃带来了士族个体的觉醒,士人由某种伦理的存在变成了独立的精神个体,因而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喟叹和依恋便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这种自我依恋又容易滑向自我中心,看穿了名教的虚伪和丑恶,过去人们所崇奉的那些价值、规范、信念既不可靠又不可信,只有自我的生与死才真实而且重要。这样,自我便完全龟缩到了自身,不仅切断了个体与类的内在联系,也不能让自我融进更广阔的生命洪流,看不到超越自我并超越生死的可能性,对生的自觉就变成了对死的恐惧。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到刘伶诸人“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140],再到《列子》中“聚酒千钟,积曲成封”[141],无不是对生命绝望的表现:既然不能永久地占有自我的生命,便要拼命地挥霍自我的生命。《形影神》一诗中的“影”似乎比“形”的纵酒要积极得多,主张在短促的人生中“立善”以流芳百世,但由于驱使“立善”的动机是为了求名,为了个人在身后还以某种方式永存下去,这就使“立善”这一为人的行为最终变成了为己。因名立善是在“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情况下的选择,假如“卫生”有道“长生”可求就不会要求“立善”了。清吴瞻泰在《陶诗汇注》卷二中尖锐地指出:“饮酒”和“立善”“皆从无可奈何中各想一消遣之法”,不管是因肉体不得长生而纵饮还是因希望令名永存而立善,二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惜生”——害怕失去自我。“《形影神》首章‘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遗(当为‘不复疑’——引者注)。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四句,虽不贪生,尚未能忘生死。二章‘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四句,虽进一解,尚未能忘名。”[142]
纵酒忘忧和立善求名的病根都在于占有欲,而这种占有欲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占有自我。对死亡心存恐惧表明恐惧者还心中有“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自己的一种私有财产,因此想死死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自然就有害怕失去的忧虑。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并不存在;而当死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143],怕死是害怕失去自己已经占有的东西,躯体、名誉、地位、财产、个性等等,所以苏格拉底认为,“对死亡感到悲哀”的人“是一个爱欲者”,“或者爱财,或者爱名,或者两者都爱”[144]。
要使自己超脱生死的束缚,个体就必须从自我占有、自我中心和自我依恋中解脱出来,让自己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只有“纵浪大化中”才能“不喜亦不惧”,达到一种无挂无碍不沾不滞的悠然洒落之境。陶渊明通过与天地同流来超越生死,论者往往认为其生命取向近于老庄,并因此遭到后人委婉的责难:“立善谁誉,今及之而后知非口头语,乃伤心语。孔子亦叹‘知我其天’,即此意也。然只有如此,并无别路。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其失在纵浪大化,有放肆意,非圣人独立不惧,君子不忧不惑不惧之道。圣人是尽性至命,此是放肆也。不忧不惧,是今日居身循道大主脑。庄周、陶公,处以委运任化,殊无下梢。圣人则践之以内省不疚,是何等脚踏实地。”[145]儒家超越生死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事奋斗,赋予短暂的人生以崇高的价值和密集的意义,在现实人际和短促人生中赢得永恒;道家则是通过与大化同流而与大化同在。陶渊明否定了立善求名的功利人生,而取“纵浪大化”的审美式超越,其生命取向的确近于庄子。庄子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46]。人之生来于自然而其死又归于自然,无论其生其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生与死都是气聚散变化的结果,由此他推出了“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结论[147],完全抹杀了生与死的对立和区别,“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人生态度因而确立[148]。陶渊明的“不喜不惧”与庄子的“不悦不恶”,二者对生死的态度好像如出一辙。
但是,陶对生死的洒落与庄对生死的放旷有着深刻的差异。庄子肯定了个体生命的自然属性,而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形态,这导致了他的放旷既违人伦又反历史。他把死作为人难得的“至乐”,认为死后“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149],因此他在妻子死后“箕踞鼓盆而歌”。然而,妻子的死亡并不只是她躯体“气散”,而且是她与社会联系的终结,是她与庄子甘苦共尝的情感应答的中止。妻子命归黄泉还鼓盆而歌,表明庄子只把社会的人归结为“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的动物生命[150],完全剥离了亲人的社会属性和生命价值,所以,他放达得近于荒诞,冷漠得不近人情。陶渊明对自己的生死如此平静坦然,对亲旧的死亡却那样哀伤悲切:“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胤才数龄。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流尘集虚座,宿草旅前庭,阶除旷游迹,园林独余情;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悲从弟仲德》)这种哀伤并非如叔本华所说的是从死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骨子里是为自己难逃同样的宿命而落泪,它是诗人对人伦的关怀,对温情的珍视。超脱了死反而使他更执着于生,热爱生与超脱死浑然一体。
陶与庄虽然都通过“返回自然”解脱生死,庄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51],陶则讲“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之三),“纵浪大化中”,但在如何“返自然”这一点上二者大异其趣。庄子的“返回自然”是让人又回到与自然浑浑噩噩直接同一的史前阶段,让人“物化”为非历史非价值形态的自然本身[152],人与自然的合一是以放弃其“人性”为代价的。陶渊明的“返自然”并非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让人与自然在某种价值和意义的景观上重新合一,经由自我生命的升华使自己同流于天地。这样,陶渊明不仅不能中止价值关怀,相反必须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信念、节操,前人早已指出他为人“雅操坚持,苦心独复”的一面[153]。
要返回自然首先就得“用力克己去私”[154],从一般层面上说要摆脱功名、富贵、声利之念,从终极意义上说要放弃对自我依恋与占有的欲望,从各种形态的恋我束缚中解脱出来。“恋我”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而放弃对自我生命的占有和依恋离不开精神上忧勤惕厉的修养功夫。清人锺秀在《陶靖节纪事诗品》卷四中说:“陶公所以异于晋人者,全在有人我一体之量;其不流于楚狂处,全在有及时自勉之心。”“及时自勉之心”就是指“克己去私”的忧勤功夫,“人我一体之量”是指通过忧勤功夫而达到的无我之境。没有忧勤惕厉的克己功夫,就不可能达到无我的精神境界,就会仍然以自我占有为其精神生活的重心,就不会具有“人我一体之量”,更不会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并生,当然也就不可能消释死亡恐惧。“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这种紧张焦虑的病源是害怕失去属于自我的生命,它暴露了“中心焦”者觊觎永久占有自我的心态。陶渊明了然于“昼夜之道”以后,便体认到“营营惜生”之“惑”(《形影神序》),便能“出妙语于纩息之余”[155]了:“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之三)“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祭文》)在“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之际对自己的生命“奚所复恋”,面临死亡时的这种洒落坦然的态度是诗人摆落了恋我心态和自我中心的结果。
放弃恋我心态和自我中心绝不是要以扭曲或者泯灭自己的个性、人格为代价,它恰恰要求真实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完善自己的人格。陶渊明认为“天”的本质在于其“真”,人的目的和价值不在“前誉”也不在“后歌”而在于个体生命的本身,即真实而不虚矫地展露自己存在的本真状态——诗人所谓的“真意”。一旦回复到自己存在的根基——性命之真,在“真”的基础上人便与天合其德并融为一体。他在《连雨独饮》一诗中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一切生物都将穷尽它的生命,传说中的神仙赤松子和王子乔也不能幸免,要超越死亡唯有天人合一,要天人合一就得弃绝俗情远离世故(“百情远”),坦露自己存在的本真状态——“任真”。“任真”并不是一任其本能的放纵冲动,只是不让世故俗念扭曲自我的本性,做到《自祭文》中所说的“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因而离不开“抱兹独”而“僶俛”的律己修身。一为俗情所染便会机巧百端,便会媚俗阿世,便会去“天”日远。“返自然”的过程本质上是忧勤守拙的过程,也即萧统所谓“贞志不休,安道苦节”[156]的过程。《饮酒二十首》之九以斩绝的语气抒写他自己“安道苦节”的决心:“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纡辔”“尚同”便苟容世俗,“驾不可回”则同流大化。
方东树认为陶渊明不过是“用《庄子》之理”来解脱生死的束缚,因而认为“纵浪大化中”“有放肆意”[157],可惜他完全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纵浪大化”这种超脱生死的自在洒脱来自诗人“僶俛抱兹独”的忧勤修身。陶渊明的确说过“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之一),“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一类“有放肆意”的话,甚至还说过要及时行乐:“千载非所知,聊以咏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事实上执着于儒家仁义操守的陶渊明,既不沉迷于利禄又不肆情于声色,他之所“乐”只不过是在景物斯和的暮春一个人“偶影独游”(《时运》),或者在秋高气爽的“佳日”与邻曲一块“登高赋诗”(《移居二首》之二),农忙时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之三),闲暇的日子与“素心人”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甚至在冻馁缠己的时候也“常有好容颜”(《拟古九首》之五),可见,他所行之乐没有任何放肆或放纵感性的意味。陶渊明不通过功德勋业而选择返回自然来超脱生死,其人生取向近道而别于儒,但在价值与意义的景观上与自然同一的这一点上则属儒而非道。如果陶渊明完全“堕庄老”,他“返自然”的同时就难于固守仁义,也无法坚持道德修养。老庄认为正是儒家仁义扭曲了人的内在自然(天性),因此导致人与外在自然的分裂对抗。既要返回自然,又要执着仁义,就好像南辕北辙一样荒谬。孟子却认为只要个人自己知其性就能知其天[158],《中庸》也认为能尽一己之性则能尽他人之性,能尽他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与天地相参。陶渊明自道“性本爱丘山”是为能知其性,“复得返自然”是为能尽其性,而“僶俛抱兹独”是为能至其命。他的“委心”是听任内在的自然(《归去来兮辞》),“委运”是听任外在的自然(《形影神·神释》),能“委心”并且“委运”就做到了“任真”,“任真”是一个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同时完成,并因之成为一个本真地存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博大无私而与天地相参,才能在“将辞逆旅之馆”时豁达洒脱。在论及《形影神·神释》中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几句时,清方宗诚的所见与方东树正好相反,认为陶渊明此语合于儒者“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夭寿不感,无入不自得,乐天安命之旨”。[159]另一位清代的诗论家也认为陶渊明的“不喜不惧,应尽须尽,是为圣为贤本领,成仁成义根源,若徒以旷达语赏之,非深于陶者也”[160]。
片面地指责诗人“纵浪大化”是“堕庄老”或一味将此说成“是为圣为贤本领”,可以说都“非深于陶者”。陶渊明面临死亡深渊时的自在洒落同时积淀了儒、道的文化精神,一方面它有庄子式的超旷,另一方面它的背后又有儒家忧勤惕厉的支撑。这使陶渊明又不同于许多魏晋名士,由对死的恐惧绝望滑入对生的颓丧放纵。虽然意识到人生的必然归宿是“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但他并不因此而追求感官的满足和享乐,反而更执着于“生”的意义与价值,反而更追求存在过程的真实与完满:“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明两萃时物,北林荣且丰。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光阴迅速如虚舟逸棹,世事变化也往复无穷,时间在俯仰之间便从“发岁”到了年中,北边的树林也随之枯而又荣。一切有生之物“既来孰不去”,诗人对这一切没有半点生物本能的恐惧,他平静地接受“人理固有终”的命运。人生的意义在于“生”的过程,如果“生”的过程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又哪在乎“人理固有终”的归宿?又“何必升华嵩”以求仙不死?如果说“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之十五)是由对死的自觉走向对生的抉择,那么,“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便是以对生的把捉来实现对死的超脱。他不求助于过去(家庭或个人的勋业、权势、门第)和未来(死后代代相传的美名)、不求于长生不老(“升华嵩”)以获得永恒,而是经由当下即得的此时此地来完成对有限人生的超越。既然“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161],那么“居常待其尽”不是十分快乐的事吗?“曲肱岂伤冲”句来自《论语·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居常”“曲肱”二句抒写的完全是儒者的情怀:谨守节操而不屈其志,身处贫贱仍乐在其中,不管世运的变化是凶险还是平安,都要按自己的志向正道直行(“肆志”)。“居常”和“肆志”不仅是道德行为,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不能将“即事”释为“对当前事物的认识”[162],它泛指诗人所应对的人生世事以及应对这些人生世事的方式,也即他自己当下的存在过程和存在方式。假如这些存在过程和存在方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个体就超越了自我而同流于天地,此时此地便是永恒。
总之,陶渊明以“返回自然”的审美式超越来解脱生死,其生命取向近于庄子,但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景观上“返回自然”则又回到了孔孟。“‘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四句,得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意。‘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四句,得依乎《中庸》无入而不自得之意。”[163]陶渊明以忧勤修身来升华人生,打通了功夫与境界的界限,“居常待其尽”是忧勤修身的功夫,可谁又能否认它同时也是面对死亡的洒落境界呢?
魏晋许多名士因其精神价值的虚无而无拘无束,因不必操守什么而得意自如,因没有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而放纵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挥霍人生,这不是洒落而是一种放诞、一种任性、一种迷惘——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陶渊明则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功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他脱弃了穷达、贫富、耕禄、生死等人生的束缚,实现了精神的自由与自我的超越。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孕育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点:儒道兼综,孔老并重。他高出于魏晋名士者正在此: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一种人生化境——既“放浪形骸之外”(洒落悠然),又“谨守规矩之中”[164](忧勤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