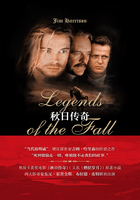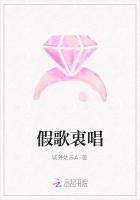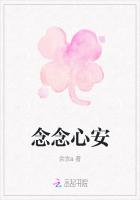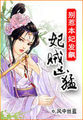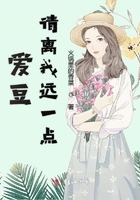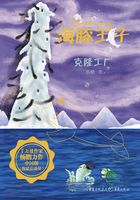让我们再来看余华、阎连科们的小说。《兄弟》、《风雅颂》莫不以“现实”为基本叙事框架,或者说表面上都采用了摹仿现实的常规写法,但是在叙事的中途,又都悄悄地背离了“现实”的束约,甚至是公然掺入了某些“非现实”的成分,从而使小说文本呈显出一种虚实相间的生瓜蛋子效果。然而此类小说的得意处恰也是其症结处:一方面,弱化了现实的丰腴和纵深;另一方面,却没有赋予非现实以生命和灵魂。由此诞下的“文学”便也不伦不类,虽变诈万端,亦止增笑耳。所谓形式感、荒诞化,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把它作为所向披靡、见血封喉的绝杀技,未免太过骄猛。仍以《风雅颂》为例,它所假托的人物,假托的场景(京城、故乡、诗经古城),乃至假托的故事情节,无不浮泛矜夸,就像关公战秦琼一般,充斥着想当然的即兴发挥,也难怪“北大”会指责作者对大学、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了解、研究——“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当然,反过来,阎连科也可以讥讽“北大”不懂文学——事实上他已经“反击”过了——“我作品中的想象我不会去想它的真假,以及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原来,人家写的是“野生小说”,“野生”是可以不讲规矩的,要的就是狂野、荒诞、模糊、象征等等,“无数不可琢磨的因素在其中”,“它非常的复杂”,“确实说不清楚”,就像有人为其辩解的:“把它的象征性情境与现实生活做对照,指责其不合生活逻辑,显然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狄蕊红:《阎连科:世界唯荒诞,才真实》,《华商报》2008年6月28日。)如果你非要较真,不正说明你的无知?又是想象的,又是个人的,难道——我的文学与现实无关,也与你的看法无关?难道——要是你不会换位思考,不能以审美的眼光审出小说的无穷意义,你就没资格对它说三道四?可我还是要不好意思地告诉阎连科,不才真的品不出他这老瓶里的新酒有什么新味道,只是感觉它是假酒是毒酒,总之它足以让人翻江倒海直至吐出五脏六腑。莫非,这就是荒诞的力量吗?
“我们只有个人的现实主义”,阎连科如是说。多么豪迈的声音!“现实主义……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可是,一个宣称“没什么承当”的人,一个只强调“精神真实”、“灵魂真实”的人,一个只会用“荒诞”定义世界的人,他所写出的内心和灵魂会是什么货色呢?内心和灵魂这两个词实在是太有魅力太好使了,仿佛一和它俩联姻就意味着他占据了绝对的精神高地,他所写出的文字一定是形而上的高不可攀的高处不胜寒。然而,当我们架好云梯准备登上传说中的巴别塔时,却总发现那只是一张褪色的教学挂图,它能带给你的,无非是一片斑驳且溃乱的“能指”。再看阎连科怎么说的吧:“有人说我是写北大,这很荒诞。昨天晚上,我和北京某大学的朋友吃饭,他对我说,你书里写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学校的人,杨科就是我们学校的某某,到今天至少有十个人来对号入座了,这让我感到轻松。无论我写的是哪所学校,至少人们产生了共识,即杨科的物质逻辑、故事逻辑可能是不真实的,但他的精神逻辑是真实的。杨科不可救药是因为他背后的现实不可救药。”在此,阎连科轻松道破了他的逻辑:你对号对准了,说明我想得准,你若胡乱对,说明你不懂“精神逻辑”。什么精神逻辑呢?阎连科一再神秘兮兮地拿这个词说事儿,也不过还是在为他的“内心、灵魂”拉赞助。那么,他的“精神逻辑”是什么呢?是灵魂的漂浮无定,是现实的不可救药,是让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家?从《受活》到《风雅颂》,阎连科的精神逻辑原是直指“现实”的吗?现实让“受活庄”大难临头,灾祸频仍,现实又让它退出现代社会,回到自己的“家园”;现实把杨科(这名字正是“阎连科”的谐音)逼得“有愁无乡,有家无归”,现实又让他逃离现代社会,找到了“诗经故城”。不同的故事,相同的逻辑,阎连科反复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不仅是乌托邦,而且是一个连火星人都找不到的假乌托邦。
最近还有一部叫《无土时代》的长篇小说,也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痛恨城市的钢筋水泥,便提出动议要推倒楼群,扒掉马路,好让人和大地亲密接触,并且身体力行,一有空就用锤子破坏马路,尤其壮观的是,为迎接绿化检查,农民工们把所有的草皮都种成了麦子……显然,这部小说和阎连科的“精神逻辑”颇为相通——面对现实世界,他们都有一个乌托邦梦想,他们都要返璞归真,与世无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我不敢说找到了他们的“所指”,但是就其由“荒诞”的现实走向理想的幻境这一“普遍共识”而论,我不得不发问:中国作家的内心、灵魂就剩这么点儿道道了吗?你们的“荒诞哲学”能不能比小学生的“环保倡议书”耐看一些?你们的“荒诞叙事”能不能比“大闹天宫”、“白雪公主”、“伊索寓言”再委婉一些,不要老是用“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样的口吻糊弄我们好不好?王小波曾写过一篇《摆脱童稚状态》,他借用别人的话说,“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王小波:《摆脱童稚状态》,《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在此,我也要借用王小波的说法:某些喜欢玩深沉的文学也还处于肛门期,因为玩弄便便玩出了快感,就以为那便便了不得,就说它很复杂,很象征,很灵魂,很什么什么,只是可惜,我们欣赏不了你的荒诞,更欣赏不了你的现实,更享受不了你那牛皮烘烘的乌托邦。
五
没有什么主义可以无视现实。“野性”绝不是信马由缰,“荒诞”也不意味着信口雌黄。然而,检点当下的文学创作,除了那些貌似贴近现实的贴金文学、热衷于自说自话的呓语文学,似乎再难找到踏踏实实地从现实出发,从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出发,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活力与困厄的作品。太多滞后的、讨巧的、媚俗的、想当然的、简单化的粗加工,偶尔重视了“形式感”,也往往只是一种加个垫子抹点油式的“技术革新”,并不能使形与神同步飞跃;至于某些大胆、另类的想象和创造,也总是流于刻意、做作;即如被人奉为圭臬的“荒诞化”,也只能沦为一类“创作技法”,并不能深入到生活的腹地,就更勿论探摸内心的隐秘了。要知道,真正的技术革新从来不是所谓的“大师们”一拍脑门的产物,也从来与作者本人内心的深浅相映衬,否则就只如东施扭着西施的腰身,麻雀插上了孔雀的翎毛。虽然我们不必强求作家一定要装备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思想武器,但是一个写作者最起码不该浮在感觉的表层,仅因一知半解、异想天开就自命不凡俨然上帝,至少,作家本人应该植根于生活,有自己的感受、省察和洞见,在你的幻想恣意驰骋时,不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敬畏和尊重。一颗粗糙、枯干的心怎么可能顾念生命的细节、现实的丰盈,一个草率、空疏的人又怎么可能仅凭想象就轻易撷取存在的真实?
在我们的印象中,卡夫卡似乎从来不曾写过“真实的生活”,他在文字中创造了一个遥远的异乡,一个完全令人陌生的世界。可是,这个虚无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他生活过的世界和他创造的世界也是统一的。阅读他的作品,没有那种人为的隔膜,他只是带你去见证、去发现,去换一个姿态参与生活。正如罗杰·加洛蒂所说:“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第109页。)“卡夫卡的伟大在于已经懂得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统一的神话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第174页。)那么,卡夫卡的“创造”源于何处?难道全是“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的白日梦?难道全都是从“丰饶的内心”流出来的白开水?只是卡夫卡全无这般自信,他的说法是:“虚构比发现容易。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出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种种样样的日常面孔像神秘的蝗群在人们身边掠过。”(卡夫卡:《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集》(叶廷芳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生活大不可测,深不可测,就像我们头上的星空。人只能从他自己的生活这个小窥孔向里窥望。而他感觉到的要比看见的多。因此,他首先必须保持窥视孔的清洁纯净。”(《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集》,第251页。)面对现实生活,卡夫卡何等谦卑,他不但强调对生活的观察、发现、感觉,而且注重个人的“清洁纯净”,唯其如此,他才得以穿越“现实”的障壁,构建了一座自己的城堡:他抓住了那种荒诞感,他写出了整个世界的荒诞性。
面对纷扰变乱的现实,文学何为?中国作家何为?在一篇人物访谈的结尾处,我看到阎连科有个这样的表态:“从今天开始,我要像鲁迅那样,做个直面现实绝不妥协的人。对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还怕什么呢?”(乌力斯:《阎连科:有愁无乡,有家无归》,《新民晚报》2008年8月18日。)这当然表明了一种勇敢。然而,当你发着毒誓“直面现实”的时候,让人不免为你捏一把汗:一个人自命为孤魂野鬼时,他的内心是否更为荒芜?
究竟是谁中了毒?
前阵子,有位诗人,猛然宣称:“文学死了”,并在文章每个段落的开头都如是大叫一声,以此昭布天下:“文学,这只旧时代的恐龙,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
据粗略统计,算上该文的标题,在不足三千字的篇幅里,该声大叫共计重复十三次。
但是,诗人仍嫌不够过瘾,紧接着,又开出一份死亡报告,罗列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几种死状,昭昭佐证出热气腾腾的中国当代文学,仅是一具“躯体正在腐烂”的华丽的僵尸——“文学,不再有现在,也不再有将来。”
正当我等惊魂甫定,不知所措之际,诗人突然又将话锋一转:他所说的“文学死了”,是指“源于西方的那个文学观念与文学系统,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的彻底死亡”。
闹了半天他只是在为假洋鬼子发布讣告。
尽管他宣称“文学死了”是“一种思想”,是一个“真问题”,尽管他已亲自把“文学这具尸体”运进了停尸房,并且号召大家一起默哀,但是诗人似乎察觉到他先前的诊断结果失之轻率,有草菅“文”命之嫌,所以才郑重发布这么个补丁,告诉大家:中国当代文学最多只是心跳骤停而已,还没发展到脑死亡的地步。
原来,诗人只是说话也喜欢另起一行而已!
原来,诗人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其实深怀感情,哪能让它随随便便就去“死了”呢?
而且,这一次,为了“向死而生”,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文学,他慨然开出一剂大处方:让“西方文学观念”去死吧,让“中国传统文学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复活,将“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发扬光大,以此拯救“死去的中国文学”。
本以为这位“诗性学者”真能掏出几粒起死还魂丹呢,却原来只是在兜售他的排毒胶囊,似乎只要肃清了西方观念的“流毒”,中国文学的煌煌大统马上就可重建。
认为中国文学过于西化,缺少中国特色,这一论调其实并不新鲜。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评论界几近“共识”,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文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便笼罩在从西方舶来的思想观念中,缺乏“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中国的精英文化习惯于使用关于“灵魂”的想象,中国作家亦喜欢拿“希伯来灵魂”说事,少有以传统的审美方式表达出来的中国式体验。所以,才有论者指出:相对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明摆着先天不足,只是一味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既丢弃了大好特好的传统,又无法跟上西方的步伐,结果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半吊子,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嫌,好像中国作家饱受西方文学的毒害,好像他们大都在用汉字写作一种不伦不类的“外国文学”。
果真如此吗?所谓西方文学观念真的是把中国文学残害得半死不活的罪魁祸首?是不是像那位“诗性学者”和一些评论家所认定的,中国文学已经背离了传统,其主流一直是“灵魂”意义上的文学?而只有重新用所谓的“中国之心”、“中国情怀”去绘量、发明现代生活,才是令当代文学绝处逢生的必然出路?
让我疑惑的是,在一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像施蛰存写作《石秀》那样讲究弗洛伊德式的深度剖析、追求所谓希伯来式灵魂的作家、作品占多大比例?是否只是凤毛麟角?上世纪30年代初倒是出现过“新感觉派”,但是他们的衣钵似乎乏人继承。至于80年代被视为于传统最为离经叛道、于西方最为慨然拿来的先锋小说,又庶几近乎语言、文体实验。即便在形式上“西化”了、“现代”了,我们的文学还是一只老狐狸,无论它把皮毛染成什么色,身上流的还是中国血,对所谓“灵魂”的诉求好像并无多大可观,更遑论成为“中国文学主流”了。
当然也不能否认,也有若干中国作家铁了心要与国际接轨,铁了心要“现代化”、“后现代”,但是这样的作家才真正少而又少,如果寻找证人,似乎只有残雪差可胜任。她曾坦言其思想感情像从西方文化传统里长出的植物,并声称要在手法上和写作的深层结构上、理念上都要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文学前进。再结合她的作品,更可见其“中毒”之深。她认定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精神内核,中国文学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她所说的精神内核就是“灵魂”——当然又与所谓希伯来灵魂有所区别,她毫不讳言写作就是对灵魂世界的探寻,因此,她讥讽那些“回归传统”的作家“自卑”,她坚信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通过在创作中批判我们的文化,将消极面奇迹般地转化成了积极面,创造性地挽救了垂死的传统”。但是这种自觉的“灵魂写作”,并未进入评论家的视野,他们所称的“主流”,好像也难将残雪统计在内。残雪不是说国内只有三个和她类似的作家吗,三四个这样的数量,作品又难以出版,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再来看我们的主流文学,自“五四”以降,究竟有多少人摆脱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