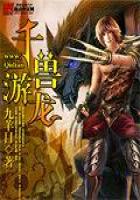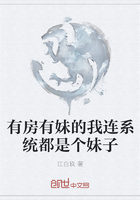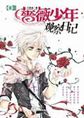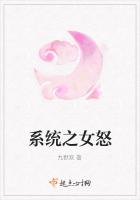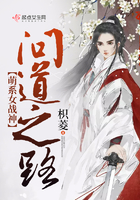一
感受,这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用以沟通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通常我们都在谈论着“思想”的深刻、磅礴和力量,但其实所有的丰富的思想都不过是不同的个体之于世界与人生的不同的感受而已,如果没有这些感受上的分歧与差别,我们所有的思想也就无法产生,思想史所以能够由思想的复杂运动而成为“历史”,是因为人类自己面对世界在不断地不可遏制地生发新的感受,所谓的“思想”其实就是对于这些新的感受的一种梳理与延伸。
感受对于人类思想的运动是如此的重要,对于文学艺术的生成和发展就更是如此,如果说思想家经常不得不进入到由感受提炼而出的思想的王国,他的确还时时依赖于理性自身的逻辑演绎的话,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则不然,他们更需要时时面对的无疑是鲜活生动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与人生,一个越是能够完整、充分、及时地传达自己的感受的作家就越能保持和呈现自己的艺术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特别重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基本感受能力及感受方式的考察,对于作家而言,所谓的思想的进步和理性意识的建立与他实际创作情境下的精神与心理方式其实是大有区别的,理性王国里的逻辑运演常常并不能够代替他之于人生的直觉和体味,越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就越是如此。过去我们是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政治理性”的逻辑框架中突出这些“思想追求”之于具体创作的决定性影响,今天又往往是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理性”的逻辑框架中发掘着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最能够体现作家实际精神与心理状态的基本感受方式,而忽略了这一基本的“感受”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以我们自己所掌握的理性概念与逻辑方式来“说明”作家的原本存在的千差万别,于是,我们各自所掌握的理性的分歧都被加诸作家身上,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含混与缠夹,甚至,我们原本丰富和富有独立意义的创作现象也沦落为某一理论的“合理”与否的证明与证伪,仿佛我们鲜活的艺术首先是“为了”这些理论而存在的,没有了这些理论的存在的合法性,连我们的创作都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近年来我们着力甚多的现代作家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就不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思路。
无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或者其他的什么中国作家都不是在理性上建构了中外文化的理性逻辑才开始自己的创作的,当然更不是在什么外来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目标下操纵自己的文学的,他们之所以选择文学,以文学作为自己的表达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产生了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独特的感受,这个道理或许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事实上却已经开始为我们所淡忘。我以为,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回到作家自己的感受状态中去,由此清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与习惯,读解作家自己的“语义编码”,然后再品味其中的客观“文化意义”。
二
这在郭沫若的研究之中亦有特别的意义。
众所周知,郭沫若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个突出的难题就在于,我们的这一研究对象具有如此复杂的中外文化与文学背景,他几乎与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坛上争议不休的众多文化与文学思潮发生着关系,而且还继续地“与时俱进”,不断在历史的复杂运动中添加着自己的复杂,他不仅在作品中一再表现了这样的复杂,而且还反复地以各种各样的理性的述说来确定着自己与所有这些复杂思潮的联系。于是,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在郭沫若研究当中最方便的选题就是“论郭沫若与××文化”,因为郭沫若文本里漂浮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完全可以为我们所自由地调用,而郭沫若本人从理性意义上所作的诸多的说明也似乎正好成了我们有力的论据。然而,越是在郭沫若被频繁而广泛地“嫁接”到中外文化当中以后,我们的研究也越发显出了一种自我的尴尬:是的,我们已经如此全面地揭示了郭沫若的“文化内涵”,但是郭沫若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显然,无论是“像”儒家道家墨家还是“像”泛神论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孔子庄子屈原王阳明还是惠特曼泰戈尔歌德都不能代替郭沫若自己的创造活动,郭沫若的最根本的意义不可能是由影响他的哪一种中外文化与文学来确立的,说他是由以上这些文化文学因素“综合”决定的也未免过于地“大而无当”了,郭沫若只能是自己确定着他自己,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郭沫若与××文化”这样的命题之下,发掘出一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出来,郭沫若感受这个世界与人生的独特方式如何?他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思维习惯,面对他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他本人有过什么样的“语义编码”?
当然,要作这样的回答的确要比从理性的框架出发寻找“文化的符号”困难,因为,所谓的“感受”,所谓的思维方式常常是一些难于言明的部分,我们只有用心去细细加以体会才能有所收获,作家飘忽的感受只能用我们自己的飘忽的感受去努力地捕捉,这就有可能进一步突出了研究的某些不确定性。然而,归根结底,能够引导着郭沫若研究走到今天并且继续走向未来的不都是因为有了各个研究者的独特的感受吗?因此,让我们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努力与郭沫若本人的感受沟通起来,这在今天和未来的郭沫若研究中无疑就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
三
我自己初步的阅读还是从《女神》开始的,因为正是它使得郭沫若找到了自我,呈现了郭沫若面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方式。
我努力在这些为无数的研究者梳理、阐释了太多次数的熟悉的文字中揣摩郭沫若的心灵的脉搏,努力拭去一些语言的覆盖物,发觉蕴涵于其中的作家的最原初的精神状态。
我的初步感受是,除却所有的那些“文化的解释”,《女神》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种超越于所有的时空之上的绝对自由。这是青年郭沫若对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的理解,是他居于狂飙突进时期对于人生的一种基本的认识。
在《女神》中,到处充满了时间运动、生命运动的动人景象。《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这样的代表作里,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典型的运动方式是:时间的流程带来了生命存在形态的某种变化,而生命本身又并不认同于这样的变化,于是生命内在的活力被激发被释放了,从总体上看,一部《女神》所写的就是生命游走于时间控制与空间控制之上的最自由的创造,是自由创造中的“振动”、“燃烧”、“再生”、“飞跑”、“飞扬”,这些词语已经构成了其大量的诗篇诸如《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无烟煤》、《日出》、《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匪徒颂》、《胜利的死》等的中心语汇。生命的游走与激发,这带来了郭沫若诗歌特有的运动感,这种运动的美使得郭沫若诗歌呈现出了与静态的古典诗歌境界所不一样的特征。可以这样说,是郭沫若对于世界与人生所采取的“运动的创造”实现了对于古典诗歌种种陈旧的境界的突围,突围让郭沫若赢得了新的读者群落,突围令郭沫若体会到了创造的快感,它最终巩固了郭沫若对于自身创作方向的确认。
《女神》的自由还是一种绝对自我的自由样式。在时间之流的波涛汹涌中,它甚至也没有过中国古人“物是人非”的那种感伤,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生所可能出现的变化,诗人似乎是充满了无穷的信心,满怀着挑战的勇气和进取的热望。《凤凰涅槃》所传达的就正是这样一种对于生命、自我与宇宙演化的确信与希望。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对自我生命历程的掌控这才是真正的命运主宰者,一种对于时间、宇宙和自我生命的绝对的主宰者。
时间的流逝最终抛弃了个体的生命,人类最终无法掌握这个世界,无法控制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空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无法掌握时间,因此,对于时间和死亡的恐惧以及面对空间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构成了人类文学与文化创造的根本,反过来,一旦在我们的作家自以为在精神的领域里掌控了时间,掌控了自我生命的流程,这也意味着他将真正确信自己掌握了世界与宇宙,当凤凰“更生”之后,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欢畅: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这里所出现的物我合一与其说是体现了什么泛神论的思想还毋宁说一种掌控了生存空间之后的欢娱的自由,一种游走于宇宙之间无所阻碍的自得与豪情,这样的自我生命在宇宙间自如往返,任意臧否的非逻辑行为正是贯穿于郭沫若诗歌的典型方式,可谓是真正体现郭沫若感受特征与精神特征的“郭沫若话语”。在《天狗》里,是自由奔突于宇宙八荒的狂迈,是誓吞宇宙到自我吞噬的语言快感,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出现了偶像崇拜与偶像破坏的突兀转换,在《梅花树下的醉歌》里,这是无有你我、无有偶像的激情: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宇宙不过是自我的表现,世界环绕着我而存在,这样的生存是充满自由充满快意的,当然也就的确不需要再崇拜什么偶像了!
主宰了生命的郭沫若面对死亡也没有了人生的沉痛,他感受到的不是生的艰难而是对这种新的生命状态的好奇与向往,他已经将死亡作为了一种自我愉悦自我享受的轻松: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死的诱惑》
主宰了自我生命的郭沫若也主宰了大自然,在诗人的眼中,大自然要么是供自己自由驰骋的场所:“哈哈,我便是那只飞鸟!/我便是那只飞鸟!/我要同白云比飞,/我要同明船赛跑。/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光海》)要么自我心灵的激情的应和:“楼头的檐……/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雪朝》)要么就是成为自我创造、征服的对象:“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与神祇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金字塔》)后来诗人表述了这样的自然观:“剪裁自然而加以综合创造”,“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四
1920年2月,郭沫若在《学灯》杂志上总结了自己刚刚从艺术创作中获得的生命感受:“生命底文学是个性的文学,因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创造生命文学的人只有乐观: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储集energy的好机会。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艺术世界中的郭沫若既然获得了掌控时间流程与生命节奏的感觉,那么他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面对现实世界的充足的信心。阅读郭沫若的文论与时论,我们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他总是在强调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如何来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如何来实现这个时代的先进性,例如,郭沫若对于“20世纪”一再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兴奋,他不时借助这一概念来阐发一些时代性很强的要求,诸如“20世纪的今日已经不许私产制度保存的时候了。20世纪的今日的艺术已经是不许特权阶级独占的时候了。”“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痛苦太深巨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接受,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毁灭它,再造它,以增人类的幸福。”“20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代;是艺术家赋予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代;是森林中的牧羊神再生的时代;是神话的世界再生的时代;是童话的世界再生的时代。”这样一种屹立于时代巅峰、傲视寰宇的感觉在他向着马克思主义的转换过程之中,在他倡导革命文学、参与的革命文学的论争过程之中,更有过十分突出的表现。中国何以需要革命文学?郭沫若在他著名的文章《革命与文学》中开宗明义:“我们现在是革命的时代”,“在欧洲的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一时的自然主义虽是反对浪漫主义而起的文学,但在精神上仍未脱尽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色彩。自然主义之末流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浪漫主义之后裔均只是过渡时代的文艺,它们对于阶级斗争的意义尚未十分觉醒,只是在游移于两端而未确定方向。而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革命文学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最新”最符合时代的潮流,这就是郭沫若“新=好”、“最新=最好”的思维,既然要永远处于时代的巅峰,获得先进的豪迈与自在,那么就必须永远追逐时代进步的步伐,“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们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抓着。”
这样的提问与认知模式可以说是贯穿了郭沫若的一生,代表了他最基本的语汇与思维方式。在这样的语汇与思维的背后,依然活跃着一个激情的、乐观的、自信的自我:他充满了能够把定时代的自信,他自诩足以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他确定自己掌握着当下的“先进”。
一个充满自信的郭沫若常常洋溢着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上的激动人心的活力。
一个“与时俱进”的郭沫若又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现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诸多伟绩。
五
然而,一个微妙却又同样实在的难题却也出现在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所有人的面前: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的意义上真正领悟和掌控了我们的生命?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掌握的感觉在我们艺术世界中还可以由我们精神的力量所建立,那么在我们的现实人生活动中却无疑会遇到重重的困难,人真的能够完全把握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外部世界么?真的能够操纵这个世界的异己力量么?人真的能够永远居于时代发展的巅峰,永远充当历史的弄潮儿么?
鲁迅似乎就缺少这样的把握。《呐喊》、《彷徨》里天空沉重而压抑,那里没有自由欢唱的凤凰,没有纵横悠肆的天狗,铅灰色的云霭低低地垂落在大地上,这里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生灵,阿Q、华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七斤……他们包裹在灰暗的生活的雾气里,在生存的尴尬里辗转挣扎。压抑以近于窒息的感觉是鲁迅之于人生与世界的基本感受,他是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了来自于生存空间的巨大挤压。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鲁迅时时体味着来自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多重碾压、纠缠和浸染。“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样的历史重负的感叹常常出现在鲁迅的文字中,在另外的时候,鲁迅谈起了现实世界的“无物之阵”,谈论“碰壁”,言及中国的“推”、“踢”、“爬”、“撞”,言及“横站”的体验。“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样,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这就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压力。就像狂人毕竟还要在病愈后“赴某地候补”一样,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就是说,他自己并不可能获得超越于时空束缚的自由,成为历史与世界的主宰者。
现在看来,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如此细微地体察和传达了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所给予他的那种无法克服的挤压,是他顿悟了这种挤压之后的难得的清醒,是他在洞察了这一现实困境之后的新的自我意识。因为自觉于人无法克服特定时空限制的宿命,鲁迅一再表达了对于所谓的永恒、绝对、黄金世界乃至于自我的怀疑,他常常以自己的特有的怀疑精神阐发着一些脱俗的见解。当郭沫若热情地描述着他心目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文学的历史:“前一个时代有革命文学出现,而在后一个时代又有革革命文学出现,更后一个时代又有革革革命文学出现了。”而在鲁迅眼里,这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进步模式恰恰是十分可疑的,它不过就是历史循环的一种方式。他甚至将他人看来的进步/落后、改革/保守的历史“绝对”解构为现实空间关系的“相对”:“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他人把定时代风潮、对未来满怀必胜的信念之时,鲁迅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对于“最新最进步”,他也并不怎么的热衷,他的清醒在于:“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中间物思想,既表达了一种对于自我生命的局限性的清醒,同时也意味着鲁迅从这一现实的清醒出发,所努力开掘着的“反抗绝望”的自我生命潜力:“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或者,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以“反抗绝望”的方式走向“坟”的鲁迅是沉重的、多疑的甚至滞迟的,因为他“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而充满了青春朝气又“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的郭沫若似乎更相信个人精神的那种所向披靡的力量,他说过:“人类生命中至高级的成分就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脑作用底总和。大脑作用底本质只是energy底交流。”“energy底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
就这样,乐观、自信而自得的青年郭沫若与悲怆、多疑而沉郁的中年鲁迅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受我们这个世界,感受当下人生的两种方式,应当看到他们各自的不同,因为显然正是这样的不同才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那一场意味深长的论战。21世纪的我们回顾这论战的个中滋味当然已经不必再陷入那种“党同伐异”的思维模式中去了,但这场论争中所充分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两种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却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因为就是这样的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也带来了他们在后来的不同的命运。
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对这样的问题产生更大的兴趣:悲怆、多疑而沉郁,相对滞迟地面对20世纪层出不穷的“新潮”,鲁迅式的姿态究竟为我们的现代文化带来了什么?而曾经如“天狗”般狂放自得、乐观向上、一往无前的郭沫若式的姿态又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或者在郭沫若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地方也暗含着一些自我生命的悲剧,这种乐观景象中的悲剧内涵更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当天狗在全无时间压力与空间压力的状态下上奔下跳、左冲右突,这一生命运动的本身是不是就带有某种空虚性和飘忽感?体会到了这一层,我们也似乎理解了《天狗》一诗从誓吞宇宙到自我吞噬的所表现出的自我精神迷乱,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在于,没有对于时空压力的深刻体会,自我生命的深度与广度究竟如何展开?生命的能量如果真的没有了任何外在的压力,是否可以持续不绝地喷吐不已?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有效地把握“时代进步”的脉搏,获得超越于时空之上的自由的快意?在解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郭沫若继续着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典型姿态,但他最后却分明陷入了为时代所作弄的悲剧性命运当中,这一段历史,的确值得我们细心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