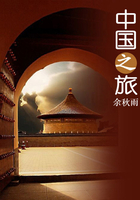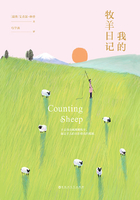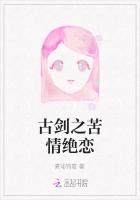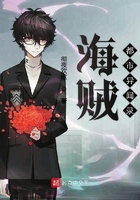如在文学领域中一样,晚明书画艺术领域也面临着如何继承与突破前人成就的难题,这之前书法领域经过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唐代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张旭,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蘒、赵佶、康里﨟﨟等人的不懈努力,各种书体已近乎完美,对于书法艺术创作与审美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理论总结;绘画领域,在晋代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唐代王维、李思训,宋代巨然、范宽、马远、夏皀、梁楷、崔白、董源、郭熙,元代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大师的笔下,山水、人物、花鸟、道释等各种画类的成果也令人叹为观止。而明初画院的恢复创立,把大批有才华的画家网罗其中,忙于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创作,大大抑制其发展。晚明书画艺术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格局。随着艺术的发展,各种艺术评论的文章涌现出来,并且大部分以小品文的形式出现。晚明一些小品文的高手恰恰也正是当时书、画、戏曲等领域中著名的艺术家,时人李陈王说:“从来画苑名家,半属能文之士,何也?其人之精神,必有以取万物之微,而后倒倾横斜能转折赋形而出。”故他们写起这方面的评论小品文得心应手,其中不乏重要的艺术主张和美学思想,这些主张和思想丰富了晚明及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的理论宝库。晚明重要艺术评论小品和文集有:徐渭关于书画评论的小品《书评》,项穆的《书法雅言》,杨慎独的《画品》,茅一相的《绘妙》,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论画琐言》,陈继儒《书画史》及《陈眉公全集》中的书画题跋,李流芳的书画题跋,莫是龙的《画说》,唐志契的《志契论画》,屠隆的《论画》,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六砚斋笔记》、《竹阇画媵》、《味水轩日记》,顾凝远的《画引》,王稚登的《丹青志》,赵左的《论画》,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沈颢的《画麈》和孔衍縂《画诀》等。此外,文徵明、袁宏道、钟惺、吴从先等人的书画艺术题跋中关于艺术的体会也是晚明小品中别具特色的。
晚明小品文中关于书画艺术的美学思考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深度,如对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艺术中的技与意、真与幻、虚与实、神与法、雅与俗的关系,当然还有艺术的意象与意境问题都有一些论述,不过像对其他审美领域中一样,这些论述也不够系统完整。
一 胸中浩浩相遇则深——艺术与自然
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中最为发达的,历代文人、艺术家对书画艺术的创作与审美均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晚明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其本身的特色,一股文人画的新潮逐渐兴起,其中反映出艺术家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与表现,中国古典美学历来重视书画艺术取法自然的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为艺术创作中一项准则,晚初王履《华山图序》中“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精辟观点,宏扬了这一传统。晚明人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关于书画艺术品评与题跋的小品中,对这种主张进行了继承与发挥。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强调外师造化的同时,对于主观审美情感给予了更多的强调。
徐渭是中、晚明最具天才的书画艺术家,他以狂放的泼墨大写意画法,开创了一代新的画风,而其笔意奔放,满纸烟云的书法也在当时独树一帜,袁宏道赞赏他:“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徐渭不仅在书画艺术创作上水平极高,而且对其创作理论也卓有所悟,在他的一些小品中表现出关于书画艺术审美的观点,尤其是表达了他艺术取法自然的精辟心解,如:
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未矣。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大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乃是点画形象,然非妙于手运,亦无从臻此。以此知书心手尽之矣。
说明只有用心去体会自然现象才能真正感受到古人所创笔意中的意味,因而学书当以心为上,手次之。在另一则小品中他对其所认为的绘画妙品给予说明:“奇峰绝壁,大水悬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能入妙品的作品首先是对自然现象的描写,他将其分为两种,前一种是具有雄壮之美的奇峰大水,怪石苍松,描绘这类自然对象须笔墨淋漓,素色烟岚;后一种是具有秀逸之美的百丛媚萼,一干枯枝,描绘这类对象则须笔墨圆润,色彩露鲜。可见描绘不同类型的自然风景须采用不同的笔墨技法,艺术技巧应该以其所描绘的对象为依据。由此可见,不仅艺术美来源于自然美,而且描绘动静不一、形态不同的美的对象时艺术技法也不尽相同,只有如此才能使产生悦性弄情之美感,作品也才能成为妙品。
莫是龙是明万历年间一位画论家,他的《画说》是一部论画的心得小品集,故被陈继儒收入其所编《宝颜堂秘盡》中。《画说》中也讲到了讲艺术创作与师法自然的关系,强调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应以天地为师,勤于接触观察自然:“画家以古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风云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而右看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
把书画艺术的欣赏与创作当作日常生活一种清赏或清娱的高濂曾对绘画、书法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作了分析,在他看来绘画、书法须取象于自然与现实的具体物象,艺术家先要目睹佳山胜水,仔细观察自然现象的种种姿态,再经过想象、发挥与凝炼,最终化为笔端纸上的艺术形象:“人能以画自工,明窗净几,描写景物,或睹佳山水处,胸中便生景象,布置笔端,自有天趣。如名花折枝,观其生趣,花态绰约,叶梗转折,向日舒笑,迎风欹斜,含烟弄雨,初开残落,种种态度,写入采素,不觉学成,便出人头地。”又说:“吾人学书,当自上古诸体,名家所存碑文,兼收并蓄,以备展阅,求其字体形势,转侧结构。若鸟兽飞走,风云转移;若四时代谢,二留仪起伏;利若刀戈,强若弓矢;点滴如山颓雨骤,而纤轻如烟雾游丝。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庶学不窘于小成,而书可名于当代矣。”
董其昌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了师法前人最终仍旧要落得师法自然之上,因为前人的杰出作品也是来自于对自然的描绘:“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吾见黄子久《天池图》,皆赝本。昨年游吴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黄石公’,同游者不测,余曰:‘今日遇吾师尔。’”在另一则小品中他直接说明了自己的创作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朝起看云气变幻,可收入笔端。吾尝行洞庭湖,推篷旷望,俨然米家墨戏。又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诸山,与海门连亘,取其境为《潇湘白云卷》,故唐世画马入神者曰:天闲十万匹,皆画谱也。”
李日华也是在游览欣赏自然的过程中体验到前人画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自然摹本为依据的,实在是艺术之美源于自然之美。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九月十日)大晴,自颊口起行,五里至高路,五里至横溪桥,十里至岭脚。过车盘岭,五里至顺溪,五里至杨家塘,五里至昱岭关,王里至新桥铺,上老竹岭。岭当两山回合处,岭以东水皆流入太湖,岭以西水皆流浙江,山势两背相抵,曲涧蛇行其间,万杉森森,四望疑无出窦,而竹岭稍通一线,亦半假人力凿治,真一夫当关之胜也。气候新晴,愈觉澄朗,诸峰晓色,澄翠托蓝,日光射之,远者如半空朱旗,近者涂金错锈,丹枫苍桧,点缀其间,万壑屯云,午千流漱玉。到此,又思李昭道父子画法不为虚设,大、小米如中书堂,淡审判押挈,其总领而已。……
晚明人对艺术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认识并未停留在以自然为蓝本这一点上,他们同时看到了人的主观创造性的重要,同时也说明了艺术源于自然,却是对自然的提炼与精致,因而是对自然美更集中完全的表现。
袁宏道的《题陈山人山水卷》中有言:“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若山人是也。”说明何以面对自然之美并非任何嗜好山水之人都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只有具审美心胸、胸中浩浩之情与山水相遇相知的人,才真正是自然山水的知音,也才真正能够创作出杰出的作品。
董其昌也强调艺术创造主观条件的重要性,他说:“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他认为艺术家既要有天分,同时也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营造气韵的本事,但除了天分外,艺术家要具备超然的审美心胸,必须多读书,多接触生活,如此才能参透生活,获得超旷的心胸,从而做到山水自然了然于胸,意在笔先,下笔自可传神。李日华则从创作时艺术家应具有的心境来说明只有神情爽,才能下笔生神:“写字必须萧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气,在于笔端,令挥则景风,洒则甘雨,引则飞泉直下,郁则怒松盘纠,乍急乍徐,忽舒忽卷,按之无一笔不出古人,统之自行胸臆。斯为翰墨林中有少分相应处也。”
尽管晚明文人注重艺术创作中人的主观想象与创造力,但他们也并未将其夸大到无所不能,一些人也看到了人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固然具有无限的空间与能力,但是人用来具体表达自己对美的现象的丰富想象的技巧与媒介却是有限的,而且大自然千变万化,无始无终,就是再好的艺术家也难以尽善尽美地将其表现出来。如吴从先《小窗自纪·黄山小记》:“奇山怪树,突盢危峰,幽洞险壑,老藤枯藓,此独寻常境界。若其变幻恍惚,忽青于染,忽净于洗。月遇之而生白,日遇之而成紫,风遇之而生吼,雨遇之而涧寒。插天拄汉,龙虎有形。至于白云缥缈,若抱树而流,携石而走;势与醉石共悬,泽同瀑布争泻;散则如蝶,结则张缦。千态万象,不可模拟,巧绘之士,未能描其万一也。”王思任的《游唤·小洋》中从自然界无可名状的色彩与人间色彩的关系方面,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俄而惊视,各大叫,始知颜色不在人间也。又不知画龙点睛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间所有者仿佛图之。……夫人间之色,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数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议如此错综幻变者?曩吾称名取类,亦自人间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睹,不得不以所睹所通者,达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谓仿佛图之,又安能仿佛以图其万一也?嗟呼!不观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
然而,对于艺术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晚明艺术家还是有清楚的认识的,董其昌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这句话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也重复过,可见自然山水本身胜在其具体、特殊性,绘画不能尽现其千奇百怪的风貌,但是没有经过艺术家加工的自然山水美丑不一,不具备美的典型性,经过艺术家充满情感地精心选景、布置、描绘,自然美才转化为艺术美。因而,艺术美不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照搬摹仿,它是融入了艺术家的情感与主观创造的东西,因而是自然美更高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董其昌才说:“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者,何颠倒见也。”
二 形不碍神雅不离俗——艺术创作中的各种关系
在晚明关于书画艺术的小品中,有许多关于艺术创作中具体问题的论述,包括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中艺与意、真与幻、虚与实、法与神、工与拙、熟与生、雅与俗等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于艺术创作他们要求以立意为先。意在笔先是中国书画艺术创作的传统,早在晋、唐时期就已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晚明人对此给予了继承。
李日华说:“古人作一段书,必别立一种意态。若《黄庭》之玄淡简远,《乐毅》之英采沉鸷,《兰亭》之俯仰尽态,《洛神》之飘摇凝伫,各自标新拨异,前手后手,亦不相师,此是何等境界,断断乎不在笔墨间得者。可不于自己灵明上大加淬治来。”他以王羲之的几幅著名作品说明,每一幅作品皆因其立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当然这种立意多是由作品的内容决定的。可见作品的审美风格是与艺术家创作时所立之意相关的。屠隆也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庄重严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后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也就是说,作画重要的是首先要有意趣,如此画才有神,意趣先立,创作中不必刻意追求工巧。如果作品没有意趣,只以工巧胜,则只有物趣,没有天趣。或者可以说只有表面的形式美感,却缺乏能引发人心灵震动的深刻的意象之美。
进一步讲,艺术创作必须立己之意,或者说要创己之新意,如此则不必一味追随效法古人,而如果没有个人之新意,即使法古,也难成佳作,因为古人亦是以立意为主。钟惺说:“诗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诗文流传于抄写刻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于书欲法古,则非墨迹、旧拓,古人精神不在焉。……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书,不复法古,以无古可法耳。无古无法,故不若直写高趣人之意,犹愈于法古之伪者。”
由此他们进一步说明,作画之所以应以立意为先,根本在于艺术创作的动因便在于胸中实有需吐之意,如此才有艺术创作的冲动,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言:“古人绘事如佛说法,纵口极谈,所拈往劫因果奇诡超然意表,而总不越实际理地,所以人天悚听无非议者。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矣。”顾凝远的《画引》中说:“当兴致未来、腕不能运时,径情独往,无所触则已,或枯槎顽石、勺水疏林,如造物所弃置,与人装点绝殊,则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画之,生意出矣。”意思是说如果胸中无意,兴致全无,则腕不能运,此时不能强下笔,须得到自然中寻求能令人生意之景物,如能与己之情相合,则意趣自出。
其次,对创作中真与幻的关系认识,也就是逼真与想象的关系晚明小品也有所论述。艺术创作中真实与虚幻的问题,是艺术家创作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过于逼真缺乏艺术灵气,过于虚幻又显得缺乏说服力。当然艺术必然来自真实世界,而它又必然具有虚幻的想象。因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于艺术创作非常重要。晚明时期文人画思潮盛行,这种画风更重写意,因而在艺术评论中对虚的强调也更多一些。
钟惺的《画龙说赠王生南游》中说:“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鱼一虫,以至竹篱茅舍,断桥危垣,草衣芒盳,人见其真者,如未之或见也。一入名手点染,好事者即成佳观。以此知真者细,入画则重;真者恒,入画则奇;真者近,入画则远。子第工其画者,何必真?即如今人作诗文,自托名家,其远神远体,时似恒似,宁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趋?”说明真实的物象需经艺术家的妙手点染,才能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在描绘现实对象时是有取舍的,经过其取舍、提炼,虽然可能会与真实有差距,但却更具有审美魅力。所以说,真实世界事无巨细,入画则只能选取重点;真实的东西普通平常,入了画则化为神奇;真实的东西人们感觉平易亲近,入了画的便感觉有距离。正因为真实与艺术的这些不同之处,因而艺术应该不同于真实,否则也就不是艺术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艺术中虚的神似要高于真的形似,关于这一点晚明人最推崇的观点是苏东坡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及与之应和的晁以道诗句“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的著名观点。杨慎、李贽、董其昌等人在论述诗协时均引用的这段对诗,在他们看来,“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代表了宋画的写实风格,而“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则代表了元画轻视写实的写意风格,自然他们更推崇的是后者。杨慎还有这样的言论:“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可见作画如只求形似的真,是不为人所重的。当然晚明在处理艺术中的各种关系时已经能够比较辩证地看待对立的两面,在说明艺术中真与幻的关系时,也注意到了逼真与想象二者均为艺术中缺一不可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它们的关系,在处理其他问题时也如此。如祝世禄说:“形不碍神,雅不离俗。金从矿出,圣以凡修复。……求真,真亦为幻,真不可求,去幻,无以见真,幻不可去。”他的这段话说明了在艺术创作中,无论形与神、雅与俗或真与幻等矛盾关系,均是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是关于书画艺术中虚实关系的处理,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对何为绘画作品中虚与实作了解释。所谓画中虚实,也就是绘画作品中用笔之略、详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作画须虚、实并重,相互弥补,如此才能画出奇韵:“古人画不从一边生去,今则失此言,故无八面玲珑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发之,是了手时事也。其次,须用虚实。虚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详处,必要有略处,虚实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心意取之,画则奇矣。”
李日华从多个方面说明了虚实在绘画作品中的不同作用,并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但实易虚难,故能虚者更高。他一方面从选景取境的角度说明,对于自然景物的选取太虚则散漫,太实又逼塞,应该以虚实相间,有意无意为佳:“盖迹分而意合,当时直写所到与所见耳,天真之趣,虚搏之,则散漫不属,实据之,则逼塞可厌,妙处正在空实相眐,有意无意间。”另一方面,对于创作时的经营布局,笔墨浓淡方面他也主张必须注意多寡、浓淡彼此照应:“古人于一树一石,必分背面正昃,无一笔苟下。至于数重之林,几曲之径,峦麓之单复,借云气为开遮,沙水之迂回,表滩碛为远近。语其墨晕之酣,深厚如不可测,而定意观之,支分缕析,实一丝之棼,是以境地愈稳,生趣愈远,多不致逼塞,寡不致凋疏,浓不致浊秽,淡不致荒幻,是曰灵空,曰空妙,以其显现出没,全得造化真机耳。迥令叶叶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与髹工彩匠争能,何贵画乎?”孔衍縂在其《画诀》中具体说明了作画时的虚实之用:“树石人皆能之,笔致缥缈,全在云烟,乃联贯树石合为一处者,画之精神在焉。山水树石,实笔也,云烟,虚笔也。以虚运实,实者亦虚,通幅皆有灵气。”沈颢的《画麈》中也有类似的看法:“行家位置稠密不虚,情韵物减。倘以惊云落霭束峦笼树,便有活机。”又云:“古人有活泼错落处,残剩处,嫩率处。”可以看出,虚实相间、偏重虚是晚明画论中的流行观点。之所以更重视虚,不仅因为实易虚难,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前人的传统,认为实从虚来,无虚则整个作品便显得死板、逼塞,以虚衬实,则有了生机。尽管实景可能甚佳,但虚处才更具想象空间,因而也更具情韵。
与强调虚实相间相通的观点是讲究画面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包括虚实变化,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变化,总之在他们看来,能变则活,活则生动,生动不定则更具审美想象力,这是符合事物规律的,因而也成为艺术中应该遵守的规则,李日华说:“风无形,庄生写之,自噫气怒号,至调调刁刁,而风之形毕矣。竹有形,玉局、石室诸公写之,簸荡披拂,极烟霞晴雨之变,而竹忽入无形。非无形也,无定形也。径寸之珠,有不定之光;异鸟之羽,有不定之色;美人有不定之态;至人之文,有不定之趣。写竹至于不定,则技神矣。”董其昌也说:“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此画诀也。”进一步他们对于作品中的动静平衡也提出了看法,变化固然重要,但一味求变不能取得画面中动静平衡,则会显得乱,整个作品的势就失之不稳,因而在作品取势时保持其动态中的平衡是相当重要的,如何保持这种平衡呢,顾凝远给出了诀窍:“凡势欲左行者,必先用意于右,势欲右行者,必先用意于左。或上者势欲下垂,或下者势欲上耸,俱不可从本位径情一往。”
第四,是对法与神(包括工与拙,熟与生)关系的认识。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经常讨论的重要问题,所谓法与神指的是创作时遵守画法与追求神韵的关系,能够二者兼得当然最好,但时常是拘束于法便难以出神,出神则需舍法。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当然是以能够出神为高,尤其是对看重个人创造,反对复古的晚明人来说,拘泥于古法显然是不高明的。
关于如何处理好法与神的关系祝世禄有段名言:“凡技艺至妙处,入乎法,又出乎法。师其成心,不入乎法者凿,拘拘焉入乎法,不出乎法者,迹而不神。”在他看来,对于法的掌握应该灵活,真正对法了然于胸便能出科法,而只有不拘泥法,能入能出,才能做到法不压神。董其昌则认为:“佛头坐断,文家三昧,宁越此哉。然不能尽法而遽事舍法,则为不及法。夫士抑能盖其法者也,尽法者,游戏跳跃无不是法,故其意象有神,其规模绝迹,盖其业在与谦应德之间。”也就是说,对法没有真正掌握而盲目舍法是不对的,但一味拘泥于法也不可取。只有真正掌握了法,对法的使用灵活自如,则即使游戏般地随意也包括着法,到了这个境界,作品的意象则会自然生成。陈仁锡对此也提出了高见:“予观先辈,大都法凝则神拙,神旷则法轶,斯道中极心折贞父黄先生。法之不得已而神生,神之不得已而法生。……其指蓄,其词洁,其脉邃,笔墨之径,别无可寻,酷似秋月贮寒潭,盖由先生之法,以入先生之神,精微又豁然。”他从先辈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如果太凝于法则有碍于神,当然得以超然旷达时,便见不到法的痕迹了,能够真正做到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他认为黄汝亨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从而法与神不仅不相互妨碍,反而相得益彰,从而作品既显示出法的精细入微,也表现了神的豁然开朗。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作品的工与拙、熟与生的问题。老子的“大巧若拙”是历代艺术家崇尚的艺术境界,晚明书画艺术评论中对此也进行了发挥,顾凝远《画引》中对此的论述最多:
画求熟外生,然熟之后,不能复生矣。要之烂、熟圆熟本自有别,若圆熟,则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复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则虽拙亦工,虽工亦拙出,生与拙惟元人得之。
元人用笔生,用意拙,有深意焉。
然则何取于生且拙,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
以上几段话的核心之意很明确,认为画之笔墨有工拙、熟生之分,从一般道理上讲工与熟似乎要比拙与生好,一般技艺也讲究熟能生巧、工巧精细等。但在艺术中熟与工只是艺术水平的一个境界,并不是最高境界,在熟与工之后能够不以求熟求工为目的,忘熟忘工,则进入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即生与拙的境界,当然这里的生与拙不是不通艺理的生与拙,而是对熟知艺理又抛弃艺理的更高层次的生与拙。晚明人之所以特别推重元人之画,顾凝远这里所说的其用笔生,用意拙也是原因之一。顾凝远还解释了重视生与拙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文人画之雅的所在。李日华认为叶石林真正悟到了这个境界,他记载说:“叶石林,住吴兴山水幽绝处,终日听泉弄石,读书谈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无知求有知易,自有知入无知难。其见解卓矣。”
第五,正如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尚淡一样,在书画艺术创作中他们也强调淡泊无意,天趣自成的审美趣味。
李日华认为作画学书无论如何表现,最重要的是要不失天成之致,也就是说创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表现不同的对象艺术家应该以对象本身的特点去创作,不能事先有主观的框框:“作画如蒸云,度空触石,一任渺弥,遮露晦明,不可预定,要不失天成之致,用为合作。学书如洗石,荡尽浮沙浊土,则灵窍自呈,秀色自现。二者于当境时卓坚真宰,于释用时深加观力,方有人路耳。”他进一步认为,这种虚淡之境只有具备高流胸次之人才能够达到:“绘事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非性灵廓彻者,未易证入。所谓气韵必在生知,正此虚澹中,气含意多耳。其他精刻逼塞,纵极功力,于高流胸次间何关也。”
莫是龙《画说》中言:“赵大年平远写湖天淼茫之景极不俗。然不柰多皴。虽云学维,而维画正有细皴者,乃于重山叠嶂有之,赵未能尽其法也。张伯雨题倪迂画云,无画史纵横习气,予家有此帧。又其自题《师子林图》云,予此画真得荆、关遗意,非王蒙辈所能梦见也。其高自标置如此。又顾汉中题迂画云,初似董原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盖迂书绝工致,晚年乃失之,而聚精于画。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要亦所谓渐老渐熟乾。若不从董北苑筑基,不容易到耳。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断,幽淡两言,则题赵吴兴犹逊迂翁,其胸次自别也。”在他看来,作画能否达到“幽淡”之境界,是由其胸次之高低所决定的。
三 万类由心千里在掌——艺术意象与意境的生成
宗白华先生说:“意境是造化与心源的合一。就粗浅方面说,就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的交融渗化。”又说:“艺术意境之诞生,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性灵中。沈颢《画麈》里说:‘称性之作,直操玄化。盖缘山川大地,器类群生,皆自性现。其间卷舒取舍,如太虚片云,寒塘雁迹而已。’这话探入中国人创造心灵的微妙境地。”宗先生的前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说出艺术意境的本质,后一段论述是对意境的进一步解释,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说明艺术意境的诞生时,使用了晚明最常用的词汇——性灵,二是在解释心灵创造的奥妙时,引用了晚明沈颢的一则艺术评论小品。由此可以说明,晚明人对于艺术创作中的意象与意境问题的认识是达到了一定深度的,而且在一些艺术小品中表达出来。
中国古典美学中对于诗的意象与意境理论研究比较深入系统,而对书画艺术是意象与意境的分析相对薄弱,晚明时期这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一些画论中也涉及了意象与意境的问题,但比起诗论中仍然不是很充实的系统。晚明一些艺术评论、题跋小品中以具体的故事说明了艺术家在创作时主观心灵与自然造想达到交融渗化的过程,及其作品所具有的意象之美。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艺术作品以创造意象与意境为最高境界,但是从理论上对意象与意境生成进行抽象概括的还比较少。此外,在他们的描述中直接使用“意象”或“意境”概念的也很少,他们大多用“气韵”来代表书画艺术中最高境界的意象之美,并且认为这种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李日华的小品《与张甥伯始图扇题》说明了意象在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意象之得与否不是事先可知的,而是艺术家在挥毫运笔之时,以自己的心灵之情描绘自然景物,如宗先生所言“使客观景象作我主观情思的注脚”,如此则笔到意生,渐入妙境,创造出意象之美。李日华把认识到这一点当成是画家之“三昧”,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作品才可能进入奇品:
昔黄鹤山樵极敬黄子久,奉为匠师。一日素黄至舍,焚香进茗,从容出其得意作请教,子久熟视久之,为添数笔,于?处作樵径,遂觉有嵩、恒、岱、华气象,因大叹服。此画名为黄王合作,真奇品也。……大都画法以布置意象为第一,然亦只是大概耳。及其运笔后,云泉树石,屋舍人物,逐一因其自然而为之,所谓笔到意生。如渔父如桃源,渐逢妙境,初意不至是也,乃为画家三昧耳。
之所以一个普通山樵的作品经黄子久妙添数笔,便气象丛生,成为奇品,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山樵尽管长久居于黄山,却只熟悉黄山的表面风光,未能识得画家三昧。黄公望则不同,李日华的另一则小品中说:“黄子久终日只顾荒山乱石、丛木深盵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可见他是以自己的心灵直接同自然对话的,自然万象的生机已了然于胸,固可以发现山樵作品的不中所在,在他“熟视久之”的这段时间内,恐怕其思绪不仅仅停留在眼前的画面上,而“神与物游”,经历了心灵与自然的共鸣。如此仅仅了了数笔,便画龙点睛,将一幅平凡之作化为神奇之作,因为这几笔之中,实则是倾注了画家的生命情调,因而这几笔也给这幅画注入了生命,成为一幅具有融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机于一体的意象之美的作品。
李日华另一段关于绘画的重要小品,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性,其中说明了绘画中四个不同层次的美:
竹阇曰: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形者,方圆平扁之类,可以笔取者也;势者,转折趋向之态,可以笔取,不可以笔尽取,参以意象,必有笔所不到者焉;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而得之也;性者,物自然之天,技艺之熟照极而自呈,不容错意者也。
他把绘画作品的高低分为形、势、韵、性四个层次,所谓“形”,指的是所给物象的具体形态,这是可以由画家之笔决定的;所谓“势”,指的是作品中经营布局而形成的一种趋向,它可以由画家之笔达到,但却不能完全达到,作品的“势”还决定于其笔墨的浓淡、构图的虚实、位置的错落等其他方面,而参发意象,说明“势”的形成中须参入画家对自然气势的主观理解与阐释;所谓“韵”,指的是作品所传达出的生动趣味,是超越了形式美的意象之美,因而只能神游意会,偶尔得之;最高层次的所谓“性”,可以说是意象中的最高层次“意境”。叶朗先生认为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并且指出:“‘意境’,就是超越具有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李日华这里所讲的画之“性”,就是这种具有形而上味道的意象。只有技艺极为纯熟、对宇宙自然之天性有所领悟的艺术家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晚明其他一些人在其小品文中也谈到了书画艺术意象的特征。顾凝远《画引》中说:“六法中第一气韵生动,有气韵则有生动矣。气韵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于四时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积墨也。”说明了作品的气韵不仅在于画境之中,更存在于画境之外,而这种境外之气韵,便是艺术中超越了具体事物、场景的审美意象。杨慎的《画品》中为画作序曰:“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妙将入神,灵能通圣,岂止开橱则失,挂壁则飞而已哉?”能够将宇宙间万类事物与千里空间收于纤毫之笔端与方寸之纸上,是因为艺术家对于宇宙与时间的形而上的一种整体把握,如此在这纤毫方寸之间,有具体形象的万事成物得以展示,没有具体形象的人的精神世界也由之生发,于是画作具有了所谓“入神”、“通圣”的意境,而入神、通圣,实际上就是对超乎具体物象与时空的无限世界的把握。杜琼的《论画》在概括绘画艺术时也说明了其意象创造的特点:“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活气。”他这里所说的胸中造化,显然是一种情、景交融的东西,而它具有恍惚变幻、象其物宜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取源于自然物象,又渗入了人的心灵情感,因而仿佛类似物象,又带有抽象朦胧之感。
书法较之写意的绘画在审美上更为抽象,或者说对书法的审美除了对字体、结构、布局等方面的欣赏外,深入领悟其所传达的意象与意境之美更为重要。项穆的《书法雅言》中谈到了书法审美的关键在于寻求其所蕴含的意象,他将其称为“神化”:“书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所愿,斯可称神。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所谓神化者,岂复有外于规矩哉?规矩入巧,乃名神化,固不滞不执,有圆通之妙焉。况大造之玄功,宣泄于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日月星辰之经纬,寒暑昼夜之代迁,风雷云雨之聚散,山岳河海之流峙,非天地之变化乎?高士之振衣长啸,挥麈谈玄;佳人之临镜拂花,舞袖流盼。如艳卉之迎风泫露,似好鸟之调舌搜翎,千态万状,愈出愈奇。更若烟雾林影,有相难着;潜鳞翔翼,无迹可寻,此万物之变化也。人之于书,形质法度,端厚和平,参互错综,玲珑飞逸,诚能如是,可以语神矣。世之论神化者,徒指体势之异常,毫端之奋笔,同声而赞赏之,所识何浅陋者哉。约本其由,深探其旨,不过曰相时而动,从心所欲云尔。”书法之作如能将宇宙天地、时空万物的千变万化发于笔端,在他看来便是“神化”,而神化的本由则是艺术家相时而动,从心所欲的创造。
此外,吴从先的《倪云林画论》说明了如何才能创造出蕴含审美意象的作品:“虽然,云林竟以画累之矣。人固有以画重者,而画亦有以人重者。画以托意,意以传神。山水之趣,不为笔墨而飞;笔墨之间,偶缘山水而合。以此思画,画可为也。”画以人重,即谓作画之人有高远的胸襟,其以画托意,以意传神,则其作品中自有常人所无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