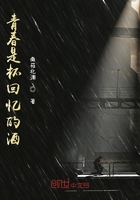小巷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酒吧,那闪闪的霓虹灯被这飘飘洒洒的雪掩盖住了往日的艳丽,甚至连名字都被掩盖。今天是新年里的首次营业,澹台余推门走了进去,屋内温度很高,但人并不多,毕竟现在已是半夜,澹台余要了一杯柳橙汁,静静的坐在吧台外侧。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戴着一顶毛线织成的灰帽,这些是李新接他出院时为他买的,这样的打扮在昏黄的灯光下很不起眼。
“这几天的天气很反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家伙喃喃自语。这个位置离澹台余不远,澹台余回头看了一下,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这人的对面没有灯,所以他的脸被黑暗笼罩,那人穿着一身讲究的休闲西装,很有绅士风范。他一定是新来的,因为刚才澹台余并没有发现他。
澹台余拿着饮料走了过去,坐在他的对面,整个人都走进了黑暗,但是脸却被灯光照亮。
“这里最早是马市,那时候这座城还不叫京城,后来城市扩建,成了戏园子,隔壁则是个妓院,这里几乎成了下九流集聚地,再后来又成了住宅区,然后又变成了一个茶楼,最后成了这酒吧。”那个中年人带着一丝沧桑的语气说。
“你知道这条小巷为什么叫做‘海田’巷吗?”那人的语气有些伤感。
“你可以告诉我。”澹台余说。
“因为沧海桑田。”那人抬头看了看澹台余,灯光把澹台余的影子照到了墙上,但很模糊,也许是酒吧里的灯光比较散。那人笑了笑继续说:“这条巷子是北京城最古老的巷子了,最早建成这巷子时这座城市还被叫作中都。”
那人打量了一下澹台余,说:“这里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年轻人在凌晨一点钟时喝……,呃,果汁的情形。这个时间段是失眠的人喝酒的时间。年轻人喝杯酒怎么样?我请客。”
“那你为什么失眠?”澹台余问。
“因为我通常在白天睡觉,”那人说:“你为什么失眠呢?”
澹台余想了想说:“我希望夜长一点,只有不睡觉,夜才显得长。”
“这真是个美妙的答案,当浮一大白。”那人说完,转身叫了一杯酒,然后对澹台余继续说:“这杯酒的名字叫‘永夜’,只有希望夜永恒的人才配喝它。”
“为什么?”澹台余不懂。
“大凡喝酒的人总要就着点什么才能下酒,不然与喝白水何异?‘永夜’就是要就着故事去喝,”那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你介意让我听听你的故事吗?”
澹台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故事,他又有什么故事好讲,过了良久他才反问:“你在这里常听人讲故事?”
“你是说那些来这里喝‘白水’的人?呵呵,我不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不用讲我也知道他们的故事。油盐酱醋,琐碎无聊的事情又有什么好听的,只会平白污了我的耳朵。”那人不屑的说。
那人大约觉着这么说有些太绝对便又补充了几句:“也有几人的故事有些特别,最近比较幸运,我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叫董伯仁的家伙讲的,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确定,却要给我讲故事,不过他的故事听着不错,最起码不会显得太过俗不可耐。另一个讲故事的则是个小女娃,她叫叶风青。”
澹台余听到董伯仁三个字,眼角抽了一下,心里敞亮了不少,不着痕迹的问:“故事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那人说:“但我不能告诉你,如果大嘴巴,可就不会有人给我讲故事了。”
澹台余想了想说:“很抱歉我没法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没关系,认识一下,我叫白少河。”那人说。
澹台余也说了自己的名字,白少河见他自从坐在这里就没有笑过便说:“如果你有什么难处我一定会帮忙,我是说我能帮得上的话。”
澹台余想起了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问:“我们坐在这里聊天喝酒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你是个不存在的人现在却存在着,并且还在喝着我请的酒,这是很诡异的。”白少河说。
“什么是‘理’?”澹台余神情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
白少河深深地看了澹台余一眼,说:“就是天理,天的道理,更多的人称它为天道,说白了就是大自然的平衡,它代表的是诸天万物的意志,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会有偏袒也不会有憎恶。嗯,我给你打个易懂的比方,人类肆无忌惮的采伐树木,致使飞禽走兽不能栖息,大自然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就是不合理的。天理不容,才会有泥石流,沙尘暴等等灾害发生,让人类受到惩罚。但是如果小范围的影响这种平衡,比如说轻度伐木也就不会有什么灾难降临,毕竟弱肉强食,人类也得生存不是吗,而且小范围的伐木大自然也是可以自我修复的。”
白少河将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光继续说:“只要别太过分就行。当然如果你伐了大树,又栽上了几棵小树就更没有问题了,这叫生态还原。嗯,没准还会有好处,假如你栽的是梧桐,没准会引来凤凰呢。”
白少河的话澹台余隐约听明白了,如果把天理比喻成一个大气球,那么自己就是一枚针,只要自己别把气球扎破了,那么气球是不会来找茬的。澹台余自问是绝对没有把整个亚马逊热带雨林砍光的本事,所以他解决了目前最揪心的“天理”问题,澹台余终于把心完全放到了肚子里,脸上有了少许笑容,他意识到自己今晚不虚此行。
澹台余长出一口气说:“你难道与董伯仁不一样,为什么人能看到你?”
“你见过董伯仁?”白少河微感惊讶,但是也没细问接着说:“我比他活的久些,本事自然也多一些,严格来说我是个仙,肉身腐朽之后神魂不灭,凝聚实体轻而易举。而董伯仁只是个刚到人间的小鬼,道行浅薄,人类当然看不到他。如果有一天他能找到自己的道,也可以凝聚实体,人前显形。”
“道?什么道?”澹台余问。
“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存在的理由,只有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天理才会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白少河说。
澹台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就是那三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出神了好一会儿才说:“这问题有答案吗?”
“所以啊,人都活不长。”白少河说。
澹台余立时无语:“能向我说一下你的理由吗?”
“很简单,以前我还活着的时候救了一只鸟,然后鸟的主人为了报答我,就送给我一枚丹药,我吃了之后也没觉着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等我死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解体成了地仙。”白少河洒脱的说。
澹台余听的目瞪口呆,被雷的是里嫩外焦,半晌才说:“这理由真是……,非常充分。”
白少河说得兴起,有些口干了想要再叫一杯酒,澹台余赶忙把自己尚未沾唇的“永夜”递给他,只听白少河接着说:“你知道站在自己的棺材旁看着躺在棺材里的自己是什么感觉吗?哈哈,你一定想不到,那真的是很爽,嗳,有机会你也应该试试。”
澹台余闻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急忙摆手:“不不……,您还是留着机会慢慢爽吧。我消受不起。”
“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是不存在的?”澹台余问。
“我还以为你准备把这个问题放到肚子里呢,”白少河笑着说:“其实大年三十的那个雷雨夜我就见到你了,天有异象必有反常,当我赶过去时,你正被几个医生往救护车里抬。当然,让我真正判断出你不存在的原因在于你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周围的人以及我的精神波动,这种精神波动说白了就是生物磁场,一个人从孕育至死亡都在向周围不停地发射生物磁波,当几种生物磁波处于相近空间时就形成了磁场,而你的到来却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磁场波动,也就是说磁场效应对你无效,要知道磁场本身就是天理的一部分,所以我判断你是不存在的,确切的说是不合理的存在。”
澹台余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尽快恢复记忆,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澹台余忽然想起了点事情,用手指蘸着果汁在桌上写了几个逝去文明的文字,问白少河:“你认识这几个字吗?”
白少河看了一会儿说:“看着眼熟,这应该是山海时期的文字,关于这种文字的使用不知道开始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消亡于什么时候,恐怕比我还要古老几个文明史呢,我以前当皇帝时,有人从大海给我带回来几片龟甲,上面就刻着类似的奇怪文字,据说记载着成仙的秘密,可惜我看不懂。”
澹台余敏锐地捕捉的了一个词语:“你当皇帝?你是哪个皇帝?”
“我说我当皇帝了?你一定听错了。”白少河有些纳闷,心想顺嘴了。
“我对我的耳朵非常自信,你一定有健忘症,说过就忘,”澹台余揶揄说:“这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当过皇帝事情也就是向我们说说,全当乐子讲讲,挺好的。你难不成还要向现代人讲?他们会把你当成疯子的!”
“就凭你这几句话,放在我当皇帝时就当诛九族,”白少河翻了个白眼,正要争辩几句,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一下泄了气,有气无力的继续说:“如果你来自于这个山海时期,那就比我还要老。”
“你还没说你是哪个皇帝呢,我从昨天开始翻遍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也没见到有个皇帝叫白少河的,就连姓白的都没有。”澹台余似乎很感兴趣。
“我是周穆王姬满。”白少河有些兴趣缺缺,原本他是资格最老的,辈分最高的,不论走到哪儿都是小仙礼敬,小鬼侍奉,现在忽然冒出一个祖宗级人物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穆天子?那你干嘛叫白少河?”澹台余准备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你觉着姬满这个名字好听吗?太缺少创造力了。所以我把‘穆’字拆开,变成了白少河,这听着多儒雅。”白少河有些沾沾自喜,似乎为自己的创造力感到高兴。
白少河看着那几个将要变干的字迹恼火地说:“你别老岔开话题,皇帝神马的都是浮云,你说这些文字到底是不是真的记载着仙的秘密,你难道是……。”
澹台余知道他要说什么,很干脆的打断了他的话:“你见过哪个神仙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再说现在就连中科院都储存了四十多个字,马上就要烂大街了。再者你看我的身体,完全就是肉体凡胎,哪有神仙应有的姿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