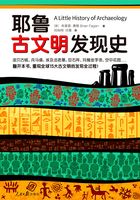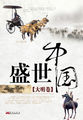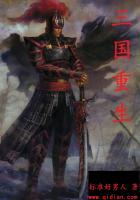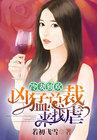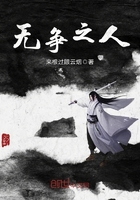第一节 洋务派思想与西学的传入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经历了一段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公元1862~1874年,同治是清穆宗载淳的年号)。这时清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化并形成顽固派与沣务派。顽固派以倭仁、宋晋等人为代表。他们死抱住封建纲常名教不放,故步自封,盲目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洋务派则是一批实力派官僚军阀,先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与顽固派相同之处,就是双方都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其思想体系;不同之处是,洋务派主张“时务”、“洋务”或“西学”,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
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洋务”机构,包括当时颇有名气的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在内。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主持;江南制造局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主持。这样的西学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饱尝外国侵略之苦,寄希望于认真学习“西学”,以为只要这样就能够使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
这一时期经由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国际公法、粗浅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基督教神学。洋务派没有可能认真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初由伽利略所奠定、17世纪末由牛顿所完成的近代古典力学体系,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于19世纪科学上一系列重大发现,包括30年代的细胞学说,40年代的能量转化定律,50年代的生物进化论,60年代的光谱分析、遗传实验和元素周期律,70年代的曲面空间与群论的研究,80年代的细菌与微生物学方面的发现,90年代的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游离电荷的测定以及其他一系列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和贡献,都没有被引进到中国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竟被外国传教士用来当作神学创世说的根据。
尽管是粗浅的自然科学,也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旧的封建士大夫营垒里开始分化出的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中国在面临新的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必须正确地认真地认识世界并努力改造自己,才能跻身近代国家之林。他们逐步自觉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希望变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为富强独立的近代国家。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面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形态。早期维新派或称早期新学派就是他们的思想代表。大多数早期维新派出身于洋务派,然而他们对当权的洋务派表现出一定的不满,进行了有限度的批评。他们大都是从洋务派出身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洋务派中,有一个“学问半通官半显”的颇堪注目的人物,那就是郭嵩焘。他的思想言论中已开始流露出与洋务派官僚有所不同的新因素。
郭嵩焘(公元1818~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任广东巡抚和出使英、法。他虽然属于洋务派上层集团,但是对西学却有其独特的见解,而与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当权派不同。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责难当时的洋务派说:“窃谓今时办理洋务,一曰求制胜之术,其大原大本处,不敢遽言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时之无事”。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说:“凡名为知洋务者……无通知其本末者”。他特别指出洋务派的重点所在,即军事工业,实际上乃是末中之末。他说:“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这就明确指出了本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的论点是:“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新学派阵营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薛福成、严复、谭嗣同等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并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基本看法。他开始把眼光从追求船坚炮利转移到探索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上来,提出“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他还对比了中学与西学的异同,认为其间区别在于“西夷专主实用”,“中国虚文无实”。这一观点也为后来的严复所直接继承,并加以阐发。严复留学英国时,郭嵩焘正任驻英公使,和严“引为忘年交”,两人“论析中西学术,穷日夕勿休”。郭死后,严挽郭曾有“平生蒙国士之知”,“入世负独醒之累”的话。上一句说严复本人受到郭的垂青,下一句则指郭的思想不合当时洋务派的时宜。这两句话可以反映出两人的深交及其思想面貌的共同点。
郭嵩焘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这里所谓“天地之机”,他的解说是:“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与友人论仿行西人》)。这就是说,中国不应该要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而应该要自由资本主义。郭嵩焘还指责洋务派口头上侈谈富强,但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他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中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这里的“民”是作为与洋务派官僚有别的另一个范畴而被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当权而又希望发展近代企业的地主、商人等士绅阶层。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改革措施。郭嵩焘把重点放在“学”这一方面,强调学习西学的重要性。郭嵩焘已开始提出:“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又谈到他自己“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尚空文。”所以,他主张中国“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意”。郭嵩焘还说:“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求所以自主。”这实际上也是后来所有的新学派的基本命题。
洋务派的基本理论即历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虽然在60年代初,冯桂芬曾有过类似“中体西用”的提法,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具有打破旧学的一统天下、要求学习西方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意在为西学争地位。这和洋务派的公式、词句虽然相似,实际上却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在西学开始得到传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民权平等之说”而发的,其意主要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个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它是洋务派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概括。
张之洞援引汉代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作为论据。他所以援引董仲舒这一命题,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新学思想。他也讲“西学”,但只是指为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服务的某些知识。在他看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所谓“中学治身心”,就是宣传尊孔读经和封建道统,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他说:“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清)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摒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者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所谓“西学应世事”,就是办“洋务”。他说:“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诫。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这里洋务派所说的“实用”和“时需”,就是指“练兵”、“制器”之类的“自强”和办厂开矿之类的“求富”,以及“兴学”,“育才”之类培养办“洋务”人才的一系列措施。
第二节 李善兰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思想
在洋务派所经营的企业及其附属机构中走出来了一批具有近代自然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只有这批人才可能首先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他们大都有爱国的思想。为了抵御外侮,他们曾努力向西方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为靠科学可以救国。他们所介绍的自然科学知识构成19世纪末的西学知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一段话,很好地描绘了戊戌前夕新学派学习西学的情形。他说:“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厚;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光启——引者)李(之藻——引者);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派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渴至是而极矣。”
在介绍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过程中,这批早期自然科学家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其中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便是杰出的代表。
李善兰(公元1810~1882年)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早年曾从当时著名学者陈奂受业,后去上海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人翻译了大理科学书籍。有一个时期,他曾入曾国藩幕;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经郭嵩焘的推荐到北京同文馆,任算学总教学,直至逝世。他一生的经历在中国近代早期的自然科学家中是颇为典型的。他的著作汇集为《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译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后九卷)》。此前明末徐光启曾译有该书前六卷,至是由他补足全书,从而向中国思想界完整地介绍了一种新的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后来康有为的早年著作《实理公法》,就是采用这种几何学的演绎方式来进行推论的。此外,他译有罗密士(Loomis)《代微积拾级》、侯失勒(J。Herschel)《谈天》、胡威立(Whewell)《重学》和奈端(今译牛顿)《数理》,后一部书即《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后由另一位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在戊戌前夕补译完成)。
早在1864年在他所著的《方圆阐幽》中,李善兰即已独立地摸索到微分积分的一些初步概念。后来他译《代微积拾级》时,对于这一通过数学形式而表现的辩证法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我朝康熙时(17世纪——引者)西国来本之(即德国的莱布尼兹——引者)奈端(即英国的牛顿——引者)二家又创立微分积分二术……其理实发千古未有之奇秘”;又说:“微分积分以甲乙丙丁诸元代常数,以天地人物诸元代变数。其理之大要,凡线而体,皆设为由小渐大。一刹那中所增之积即微分也,其全积即积分也。故积分逐层分之为无数微分,合无数微分仍为积分。”
关于数学中的无限这一概念,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已有若干天才的直觉,如《庄子》中所述辩者的光辉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但是只有到了近代微分积分概念的成立,有关无限性的辩证思维才获得了明确的、近代科学的表述形式。应用这一概念,人们便可以精确地描述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在一切理论成就中,未必再有什么像17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那样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了。”微积分学的出现是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变化和运动的辩证观点一旦引入数学之后,就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而在中国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这一近代思想的巨大成果的,就是李善兰。
除了数学方面的贡献而外,李善兰在天文学方面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使我国的思想界对于近代天文学概念有了科学的理解。在物理学上,他介绍了牛顿的古典力学体系,从而打破了明末清初以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界的垄断和封锁的局面。从哥白尼开始到牛顿集大成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及其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已奠定了200年之后,到李善兰才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并逐步为中国学者所熟悉。
李善兰在哲学上的贡献,值得提到的是他对于阮元思想的批评(关于阮元思想详见第三章第六节及第四章)。这在他所翻译的《谈天》一书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谈天》一书是英国天文学家小侯失勒(公元1792~1871年)的科学著作。原书出版于1851年,李译本出版于1859年,译本中并增附有1851年以后天文学的新成就。《谈天》的问世,在近代自然科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瞩目的事件。李善兰介绍说,“此书以哥白尼之理为真”;就是说,他是拥护太阳中心说、反对中世纪的地球中心说的。在思想方法论上,他在《谈天》卷首着重指出:“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里所谓“习闻之虚说”,即指中世纪的神学世界体系;所谓“新得之实事”,即指近代的古典力学体系。他要求人们以自然科学的真理去探求和解答万事万物的奥秘,表现出笃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对阮元株守圣经贤传而不敢离开经学教条的治学态度的有力驳斥。
针对阮元所谓“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的论点,李善兰提出“此书之法非纯言当然之理,亦非纯言所以然之理,而并用此二理;因第二理更合于学,故多用之”。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阮元的两个基本论点:一是认为哥白尼学说是“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一是认为托勒密体系和近代古典体系都只是人们主观上的方便假定,“其实不过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李善兰针锋相对地指出:“窃谓议者(即指阮元——引者)盖未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古今谈天者,莫善于子舆氏‘苟求其故’之一语。西士(指从哥白尼到牛顿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引者)善于求其故者也。”这里实际上就是以科学的真理批评封建儒家经典的权威。他并且根据古典力学的原理,说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是不可动摇和不可移易的。这就否定了阮元所主张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论点。在李善兰看来,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从被人们认识的,而并非如阮元所断定的那样,即由人们主观设想所虚构出来的“假象”。因此,当时另一位数学家华蘅芳在论及这场思想论战时,就肯定了李善兰在科学上能坚持“顺天以求合,而非求合以验天”的巨大功绩。“顺天以求合”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为合以验天”则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想先验地强加于自然界。
李善兰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间有色者不能无形,有形者不能无体。盖色由形著,形由体呈。今试以墨做一点于纸上,此形之至小者也,然非凭虚而有,乃墨所成。既为墨所成,则其墨非体乎?是故点者,体之小而微者也;线者,体之长而细者也;面者,体之阔而薄者也。”(《方圆阐幽》)这个论点并不准确,因为他没有能够正确把握抽象与具体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自然科学家思想水平还处于幼稚的阶段。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里面还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他把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摆在第一位,而认为人们思维中的抽象概念只是第二位的东西,从而把感性经验当作理性认识的基础。李善兰之坚持感觉经验先于思想,代表着近代早期自然科学思想对于神学说教的怀疑和否定。
以李善兰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家,是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是: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工业发达,而工业发达又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李善兰在《重学·序》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这种见解并没有超出早期新学派的思想范围。它是后来“科学救国论”的先声。
第三节 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
不论是洋务派思想或19世纪60~70年代期间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思想,在设计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时,都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即政治制度问题。当早期维新思想出现后,才多少接触到政治体制问题。
早期维新思潮,上承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思想,是19世纪后期中国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思潮之一。这个思潮的主要人物有: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江苏吴县人),王韬(公元1828~1897年,江苏苏州人),薛福成(公元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陈炽(公元?~1899年,江西瑞金人),马建忠(公元1844~1900年,江苏丹徒人),郑观应(公元1841~1920年,广东香山人)等。他们受过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是也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提出了进行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要求。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想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但是在经济上则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反映出当时正在形成中而又极其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
早期维新思潮的重要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的中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而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相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新学派或西学派。他们希望发愤图强,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邵作舟叙述当时学西学的情形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邵氏危言·纲纪》)这颇能道出当时这批人的思想面貌。
早期维新思潮不但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开始注意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等等。他们不满于洋务派和西方传教士所谈的“西学”,要求重新成立机构,组织力量,翻译他们认为是最迫切需要的西学书籍。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就指责同文馆、制造局这类洋务机构“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译专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因此,他主张应该系统地翻译三类书籍,一是“各国之时政”,二是“居官者考订之书”(包括“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这里反映出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区别。
早期维新思想家大多是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着眼,以为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科学与工业的发达,所以主张中国必须“兴工艺之学”。但是,他们本身的科学训练却很有限,他们既没有能接触到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也没有能把自然科学提高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上加以理解和阐释。在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调和折衷的倾向。郑观应关于“道”和“器”的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为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盛世危言·道器》)他试图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说成是道与器的关系,主张用“道”(旧学)来统率“器”(新学),使旧学居于支配的地位。这样就把科学仍然局限在封建儒家正宗思想的框架之内。但是,关于人们的认识过程,他却肯定了应该是从具体的“形器之学”出发,认为“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浅迹不足以穷神”,则是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论断。
不仅如此,早期维新思潮还认为,“道”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器”才是可变的。他们甚至要求以西方的“器数之学”来卫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些都说明他们还不能摆脱封建主义旧学的束缚。他们对当时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分肤浅的阶段。
早期维新思潮还探讨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而且还有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从政教风俗和社会制度方面去探索西方先进国家所以富强的本原,就成为早期改良派的特色之一。马建忠曾留学欧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引者),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又说:“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这里透露了他对资产阶级民权的向往。但是,他并没有正面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他和薛福成一样,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的地位较高,因而也就对封建政权表现出更大的依附性。至于社会地位较低的王韬、陈炽、郑观应等人则比较公开地宣传“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的优点。王韬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盚(指君臣上下相与讨论——引者),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园文录》外编)陈炽也指出,“泰西议院之法”,是“合君民如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认为这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又说:“君民共主之国所以威行海表,未艾方兴者,非常也,数也。圣人复起,无以易之也。”(《庸言》外编)郑观应则宣传“议院兴而民志合,民志强”,并把君主立宪政体说成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惟一出路。他强调说:“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以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所以“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中国)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情,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盛世危言》)但是,他们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猝难仿行”,而只能“变通其法”(陈虬《救时要义·开议院》)。怎样变通呢?就是把各地方的书院变成“议院”,即一种清议机构。这种观点表明,早期改良派心目中的民权,实质上是绅权。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尝试掌握政权之前,最初曾把眼光放在要求发展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方面,把这当做是国家民族的惟一出路。当时,王韬提出“持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应则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思潮而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构成封建主义经济思想“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反题,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郑观应在《商战》中比较详尽地阐发了这种思想的基本观点。他说:“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西方列强——引者)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又说,列强用武力“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卷三《商战》)郑观应的这一论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和愿望: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要认真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包括经济侵略在内。他特别强调以“商战”弥补“兵战”的不足,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这样,他就把发展民族工商业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谋求国家的富强联结起来了。
在郑观应之前,薛福成就提出过:“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陈炽也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通商与用兵而已矣”,把西学或新学归结为通商(富)与用兵(强)二者。这种观点构成中国近代早期重商主义的基本公式。郑观应则更进一步把它发展为“人尽其材”、“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纲领。应该指出的是:商战论不单纯是经济纲领,它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质。因为既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所攫取的各种特权。陈炽就指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郑观应在《商战》中也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他们都主张保护关税,尤其反对西方列强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关税。郑观应就说:“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盛世危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商战论的政治含义。但是,早期改良派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由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压迫使得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而缺乏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力量,商战论就只能流为一种空洞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