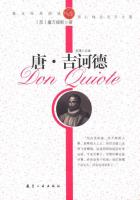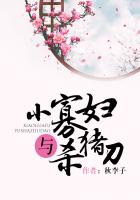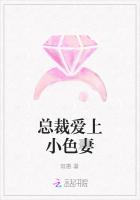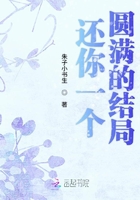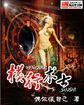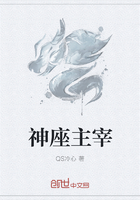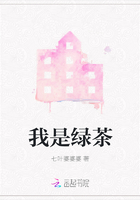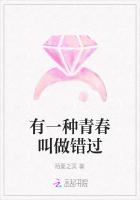在19世纪,由于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了很多普及科学理论的小册子。无论这些小册子的理论价值如何,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理论一旦拥有普及的形式,就会与它们尚属于科学探讨领域时有所不同——例如,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和物竞天择理论,都已不同于达尔文以及与他争论的学者们的理论。它已被改造成社会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了。20世纪的领袖们,例如希特勒,其知识仅仅源于科普小册子,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头脑中不可思议的知识混乱。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之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同时自欺欺人地认为:脚下没有万丈深渊,同时要记住,眼睛千万不能往深渊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由苏联窜改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知识的双倍庸俗化。曾几何时,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森林体现的是受到为数不多的某些基本法则控制的树木集合体。似乎砍光森林里的树木,在原地种下新的树种,过了一定年份,就会得到一座新的、符合人的愿望的与过去森林相像的森林。但今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森林是由苔藓、土壤、各种植被、树木和青草等等,在复杂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当森林里的树木被砍光之后,那些苔藓和各种植被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品种共生原则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新森林就成了与忽视植物社会学的人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有机体。斯大林主义者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起码的知识。他们不但不想听到这些,还谴责那些在这方面做研究的、有才华的学者和作家——因为这样的研究有悖于正统思想——以至于阻碍人类获得有关自身的知识的可能性。学说的情绪化和说教成分如此强烈,以致改变了正常比例。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科学的——运用到人文科学方面,主要在于根据一时的需要,将人文科学任意改造为它想建立的学说。人在踏上难度被大大简化了的学说吊桥时,就不可能再有退路可走了。甚至不允许真正的学者胆战心惊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尽管他们只是说科学法则是假设的,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和所运用的象征。人类历史的数世纪,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结果只用几个术语就高度概括了。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对此还得附加一点,即借助唯物主义(例如“物质不灭”的理论)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而我们就会看到,当斯大林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自有生命以来的历史顶点之时,整个圆就奇妙而又合逻辑地画成了。
接受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子弟只能按照学校要求的方式来思考——二乘二等于四。报刊与文学也都帮助学校这样教育学生;报刊和文学也为年轻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提供例证,就像圣徒和殉道者的生平传记为神学提供例证那样。与此同时,绘画、电影与戏剧也都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论点提供种种例证。认为迄今仍不存在价值的双重性的论点也许是不精确的。但反驳是情绪化的,在那种涉及反应纯理性化的地方,这种情绪化的反驳很少能与之相抗衡。
由于采取了一套有效推行庸俗化的措施,那些还没做好准备接受这一切的大脑,即那些推理能力太差的人,他们要学会思考;经过训练的人开始相信,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尽管暂时看起来还不够完善。“参与文化”的人越多,即上学、读书报、上剧院看戏和参观展览的人越多,辩证法学说影响的范围越扩大,威胁哲学家统治的危险就越小。
有些人即使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但推理能力却很差,他们完全不受源于黑格尔的哲学的影响。就像无法教会母鸡游泳一样,无法使那些属于注定要被制度消灭的社会集团的人信服。如果那些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许就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希望,可是他们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前途,所以他们会去寻找精神出路。这些人是制度的敌人,理应被推到社会的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搞什么活动,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客观上他们属于敌对阶级。
敌人的思维是辩证法学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常常把反动分子当作社会典型来研究。让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反动分子——这就是我们对他们所下的定论。从反动分子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某些特征:一个反动分子尽管是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没有能力理解20世纪的成果——各种现象之间产生的相互依存性。由于采用孤立的概念思考,他的政治想象力极其有限。一个学过社会学的人,从每一种现象中,都可以立即归纳出一系列推论——确定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就像一个古生物学家那样,从古化石中推测出产生化石的层系构造。如果你们拿出某个国家诗人的诗歌,或者拿出绘画,甚至一件衣服的某一部分给他看,他即刻就能告诉你,这些东西出自哪个历史年代。他的一系列推论也许是错误的;但至少他知道,在一定的文明范围里是没有偶然性的,他会把一切都当作征兆来审视。反动分子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世界在他看来是一系列没有关联、平行发展的事件。例如,纳粹主义,按照他的想法,仅仅是希特勒及其同党采取行动的结果;革命运动则是莫斯科策划的阴谋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乃是暴力强制使然;如果能发生什么奇迹来消灭这种暴力,那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这令人联想到,暴涨的河水淹没了某个人的花园,这个人预料,洪水退去之后,能找到过去的花畦;但是泛滥的河水不仅冲毁了花畦,还冲走了大片土地,冲倒了树木,留下的只是沉积的淤泥和乱石——旧日的花园早已变成了一块完全变了样的、只有几平方米的一小块土地。反动分子无法理解什么是运动。他自己使用的语言也让他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尽管看到一切都在变化,但他的观念也不会因此而更新。曾经有一部由劳莱与哈台演出的滑稽片:劳莱在片中饰演一位“一战”中的美国大兵,当他的连队出发去进攻时,他被命令留守在战壕的机关枪旁。这件事刚好发生在停战之前,在签署停战协议的混乱之中,他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年之后,人们找到了他,只见战壕旁边罐头堆积如山——他就是靠这些罐头活命的。当航空公司的客机飞临他的头顶上方时,他就坐在机关枪旁,拿起机关枪朝天射击。反动分子的表现与劳莱一模一样,他知道必须向飞机射击,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飞机已经不是他接受命令时的飞机了。
反动分子,甚至在阅读了很多有关辩证法的书籍之后,依然不能抓住其中的要义:他脑子里缺少一根筋。正因如此,比方说他对人的心理评价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辩证论者知道,人的理性生活与感情生活一直都处于运动的状态,因此,将个体视为在一切情况下都维持不变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信仰与反应会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反动分子惊讶地看着人们的变化,他们一边观察身边的熟人怎样慢慢变成制度的拥护者,同时还试图以十分愚蠢的方式,将这一切解释为“机会主义”、“怯懦”和“背叛”;反动分子必须给自己找到某种标签,如果缺少了这些,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推理是建立在“非此即彼”的原则之上的,他试图将自己周围的人分为“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尽管在人民民主国家,这种推理早已经失去了根基,凡是在辩证法影响人们生活的地方,谁想采用过去的逻辑,谁就一定会感到心理失衡。
反动分子的遭遇总是如此:他所使用的概念,会突然失去一切内容,给他留下的只是空洞乏味的只字和词组,他的熟人、朋友在一年之前还带着喜爱之情一再重复着这些只字和词组,而现在却避之唯恐不及,认为它们太概括、意义不够明确,且与现实格格不入。反动分子绝望地反复叨念着“荣誉”、“祖国”、“民族”、“自由”,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于生活在已发生了变化(每天都在变化)的环境里的人,这些抽象名词已有了具体而又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涵义。
由于反动分子具有这些特点,因此辩证论者认为反动分子比起他们自己来要笨得多,并因而相信,这些人对他们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他们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合乎上述定义的反动分子曾是有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有鉴于此,要牢牢抓住知识分子,在消灭了有产阶级之后,控制知识分子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那些较有活力的知识分子代表正转向新的思想立场,其余的人则思想退化,越来越与世隔绝,越来越“跟不上”周围环境的变化,社会地位也就随之越来越低下。新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广大农民和昔日的小资产阶级还残存着反动倾向,但是这样的倾向却没有在思想上表现出来。那些借着创造新的生活条件培养出来的民众,尽管怀有不满情绪,可他们与有纲领的反动分子之间的思想距离仍每个月都在扩大。政治移民则是间接帮助当权者统治国家的重要因素。按照上述定义,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反动分子。他们在电台发出的呼吁和演说,都令人联想起可怜的劳莱向飞机开枪的故事。听众听他们抱怨自己也并不喜欢的政府时不无快感,但并没把他们的话当真。
在这些政治家善用的词汇与实际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辩证论者常常批评反动分子,说他们明显地“自视过高”。这类对反动分子意思含混、令人尴尬困惑的恶意评价暗示了:那些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他们的思想还未成熟。人们不愿与反动分子协同一致(人民群众本能地感到他们属于弱势),这加深了他们的宿命感。
因此,控制民众的思想没有受到阻碍。智力的能量,无论出现在哪里,也只能找到一个宣泄口。此外,在观察民众的情感生活时能感觉到,他们在思想上存在极度的愤懑情绪。这种愤懑情绪不能仅仅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论述偏少,因此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某些意料不到的隐忧,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首先是宗教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尽管可以对基督教本身存在的诸多弱点进行抨击,并且能获得成功。但天主教教会在封建体系改革之初,激烈地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科学思想,从神学领域中夺走了最具才智的头脑,这使欧洲的宗教遭到重大打击。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的迅速传播,尽管这种思想起初只为极少数头脑所拥有;为了了解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进程,有时只需追踪观察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敏感的个人思想发展的方向就足矣。那种在某一时期内浮在表面的东西(例如某些文学风格)会让位于新的因素——尽管它作为次要或三流的区域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有复兴的可能)。在欧洲也曾发生这样的情况:神学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教会失去了知识分子但也没能赢得新兴工人阶层的支持——这两个群体都是党特别重视的。如今基督教的精神生活在教会的边缘发展,只剩下一些试图使天主教哲学顺应时代新需要的小群体。
然而,宗教需求在大众中依然存在。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定这种需求也许是错误的,或许把所有居民都改造成工人,就能够消除这种需求;但也说不准哪天这种需求又会冒出来。当然,这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实际上,人在理智地解释某种现象时,内心却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反抗。在20世纪,基督教的逻辑盔甲是如此不堪一击,儿童在学校被新的思想方法强迫洗脑,尽管这样,理智之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地带犹存,我们总是遇到难解的哑谜。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巴甫洛夫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ПетровичПавлов,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教授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东正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是杰出的学者而且年事已高,在莫斯科没有人敢去找他的麻烦。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他所发明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反驳某种永恒的“人性”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宗教的扞卫者在援引这种“人的天性”的同时,强调它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既然数千年以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一直存在着神只和教会,也就可以预知,宗教还会继续存留下去。如果两种概念体系——科学体系和宗教体系,并存于巴甫洛夫教授的头脑里,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呢?
那种促使人们笃信宗教的趋势,究竟是“人的天性”使然,还是数世纪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一直存在。甚至于苏联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也需要把东正教的牧师从被人遗忘的尘土中挖出来,让他们激发民众的民族感情。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会有荒诞的灵光一闪,认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连辩证唯物主义也会突然展示它不过是空洞的数学公式而已。人从巧妙架设的吊桥上落入深渊时,仍宁愿迷信于圣像的魔力。
党知道,它本身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党对地球的专政和对人类的改造,都有赖于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的非理性趋势规定方向,并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单单用正确的推理说服人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俱乐部举行各种活动,诸如组织诗歌朗诵、阅读小说、看电影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诗歌、小说和电影能触动人们的灵魂深处——正是在那里隐藏着感情的反抗,不能容忍任何别的教会,例如基督教。基督教是党的头号敌人,大众对彻底改造人的一切疑虑都能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支持。如果按照福音的说法:“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不也意味着不可伤害“富农”吗?如果不该把至高荣耀归给人,那么过分崇拜诸如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天才人物,难道就不算是偶像崇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