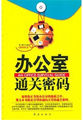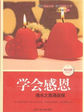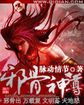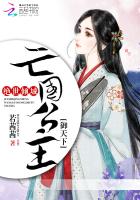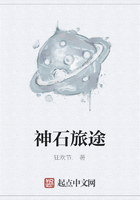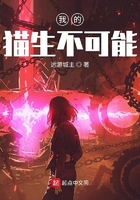以少见多,化繁为简,以重复衬托差异,以喜剧衬托悲剧,用形式化来提升内容,这些其实已都是叙述的辩证法了。但余华的许多惊人之笔使我不得不再专门谈一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读到许三观一家在饥饿中“用嘴炒菜”这一节戏剧性的对话场景之前,我曾对《许三观卖血记》这部作品和余华同其他先锋作家等量齐观。但这一小节叙述却改变了我的看法,也使我对余华的阅读与理解上升到一个新视界。我知道这样的描写是一种标志,在此之前,不只关于一个年代的饥饿记忆的描写已经多得可以车载斗量,而且它们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地相似,只有这个让人发笑的故事才震撼了我:同样的经验原来可以用如此不同的“经验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文学的减法”,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但却一定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被认识,被实践。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没有哪一个细节能够像这段描写这样使我感受到叙述的戏剧魅力,感受到辩证法的力量。同样的例子还有“家庭批判会”一节,许三观和三个儿子被迫在家中组织对妻子许玉兰不成体统的批判,但这场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会,却让人备感“良知的震撼”,而对人物有了大悲悯的体验。还有,余华在《活着》中还将苦根的死安排为“被撑死”,这也是一个极其有力的证明,它表明,余华叙述辩证法的力量已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撑死”实在是饿死的极致,没有疯狂的饥饿感,怎么会导致撑死呢?显然,这是它所以令我们久久感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也许鲁迅的例子还是值得一谈的。以往人们在对鲁迅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离,比如总是过多地将他看作了思想的化身,再以此来谈论他的文学作品。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把“新文学”等同于“新文化”的话,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鲁迅的小说文本和小说艺术。我想,时至今日还没有那一个新文学作家敢于说他在文体方面、他在小说艺术的成就方面已经“超过了”鲁迅,而就是这样一个作为新文学和现代白话小说典范的鲁迅,支撑其地位的作品不过了了三十来个短篇小说,区区十几万字的规模。这其中奥妙何在?固然因为是鲁迅占了“第一个”的先机,可是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所创造的文体和表达方式所具有的难以超越的经典意义。在这个经典的构成里,我以为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他深通“辩证法”的简约而富有戏剧活力的形式,二是他的经验的深度、经验的概括力,以及翻新古老的小说经验方式的能力。这使他的表与里两个方面都臻及了“最高的范本”的境地。鲁迅的“减法”是通过细节重复照应来实现的,他勾勒一个人物的命运,常常就是通过几个互相近似又有微小区别的细节,来简约地呈现出“时间的痕迹”,并衬托出人物的变化,祥林嫂和孔乙己都是最生动的例子。重复在鲁迅这里不但没有造成繁复和臃肿,相反它所造成的恰恰是戏剧化的结构,与高度形式感的叙事线路。而且,这种叙事的线索所造成的戏剧性,常常就是主题本身。另外,他还喜欢刻意用“弱智”的笔法,用喜剧化的情境来反衬悲剧性的意蕴,《阿Q正传》、《孔乙己》都是例子。
不难看出,余华是当代作家中深知鲁迅的小说三昧、并且有所承继和光大的一个。在1989年的一篇有名的随笔《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表达了他对“陈旧的文学经验”的厌恶,对“缺少想象力”和被“日常生活所围困的经验”的超越欲望。但他却说,“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他追求真实,但以往的陈旧僵死的经验方式却使人远离真实的经验。因此他在寻找一种看起来更“虚伪”的形式,当他写下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发生在“现实”之中的《现实一种》——这幕“现代主义悲剧”的时候,他又得出了“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真实”的结论。显然,余华是最谙熟“虚伪”和“真实”之间的辩证法的,由于这样的理解使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后期,都是一种“真实的谎言”或“用谎言来表述的真实”——一如加缪所推崇的笛福的话,“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只不过在前期是“由虚伪抵达真实”、后期则是“从虚拟的真实抵达了更像真实的真实”。特殊的抽象能力使他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经验世界。
因此在这一部分里,我要谈一谈余华的“叙述的辩证法”的几个侧面:他的多与少、简与繁、轻与重、悲与喜、甚至智与愚。不过,在这一系列的“二元关系”中,低调的“减法”仍然是他的轴心。
先看简与繁。前文说简约成了余华小说的诀窍,然而在他这里简约从来不是产生自简单,而是产生自复杂。对余华来说,人们惊讶的是他的前期和后期作品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前期他是如此的执迷于复杂的叙述实验,给读者制造繁难的障碍;而后期他看上去却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以至于连孩子和粗通文墨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读者。于是就有了一个现成的说法,认为以《活着》为标志,出现了一个从先锋到回归、从实验到返朴归真的“现实主义的转型”。但这样一个“转型说”是十分表面的,只要稍细心些我们就会发现,早期余华的小说中“简化”的意图也同样是强烈的,只不过那时人们面对他“复杂”的表象似乎还很难从容地解读其所追求的“简单”。我感到,余华的卓尔不群正在于,他从介入文学的开始就没有一味地追求复杂,而是同时将两只脚伸向了复杂和简单的两极。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这种意向就十分的明显。它简化了这样一些要素:事件的背景,特别是简化了“时间”坐标;简化了过程中的逻辑,事件与事件之间没有了所谓的因果必然性,没有了虚构出来的“人物性格的发展”;它甚至简化了细节,把人们通常以为非常关键的“描述”变成了“叙述”……但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简化,使作品具有了通常所不可能具有的丰富与复杂。它变成了一个寓言,一个种族的神话:人就是这样地在受骗的经历中完成了他十八岁的“成人仪式”,他的纯洁童年的破产之时,便是他成熟的成年到来之际。血的教训完成了他的蜕变,由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少年,到成年人的恶、在是非的颠倒和生活的教训面前,终将变得见怪不怪,对人性之恶视若无睹。其实,这样的小说已经可以达到与《狂人日记》和《药》、与鲁迅的很多小说并驾齐驱的高度了——《狂人日记》的主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成人仪式”,一个未被规训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因为说出了“吃人”二字,而受到成人世界的威压与迫害,当他完成了这个被规训的过程时,便似乎是医好了病,“赴某地候补”去了。
早期余华的任何一个作品其实都包含了他简约的意图,只是由于余华在这时所追求的,并非叙事表层的经验化和活跃的戏剧性场景,所以在阅读上很难同时给所有层次的读者带来《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直觉的快乐。但类似《两个人的历史》这样简约之极的小说,也可以来反证他在1990年代、在《活着》以后的作品中的“简单中的复杂”。其实没有哪一个作家会轻易地就完成一种“转型”,在我看来,余华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甚至《兄弟》这样的作品,也绝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余华前后“两个阶段”的作品,其差异不过是在于,前期追求的是“形式的简单”,后期追求的则是“叙事的简单”;而就其经验的简化和还原于生活的程度来讲,其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与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于历史和生存。其实余华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看作标准的“寓言”,不惟前期那些以繁难著称的中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也一样。寓言式的写法不但成就了他的精致、质朴和令人惊奇的简单,同时也造就了他的复杂、深邃和叙述上最大的恍惚感。
余华的叙述的辩证法表现在很多方面。像伊恩·瓦特对笛福的赞扬一样,他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痛苦与欢乐、真实和虚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减法”在某些时候会变成各种形式的“节制”甚至“反讽”,比如人们会震惊他对于惨剧和苦难的漫不经心的描写,在《现实一种》里哥哥山岗对弟弟山峰的报复,竟是让他死于一个令他大笑不止的游戏;在《活着》中,劫后余生的苦根竟是夭折于“撑死”——他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悲剧的内容,用平和的承受、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来体味地狱的苦难,这在《活着》中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例子还有《兄弟》中宋凡平被打断了胳膊,却还在孩子们面前表演“晃来晃去”的好玩,“让它休息几天”。余华能够把奇闻讲述得如此朴素真切,源于他近乎残酷的神经和控制力。
刻意单调的“重复”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化”,这大约是一种最能掩人耳目的辩证法了——它戏剧性地将重复和简化混于一谈。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行为与说话;二是叙述者自己的语言方式。许三观一次次卖血时的“例行程序”——不停地喝水,然后行贿“血头”,然后卖血,然后到河上的饭店里要上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和孔乙己三次重复又有微妙不同地在咸亨酒店里出现的情景可谓神似;许玉兰对着大街一遍遍地喊“我前世真是造了孽了”的场面,同祥林嫂对行人一次次诉说阿毛之死的絮叨,也是如出一辙。这就是“重复”的意义,鲁迅是最懂得减法的,余华也懂得。这种重复的“加”里实则是包含了真正的“减”和“简”,反之亦然。某种意义上,戏剧性、形式感、经验化和节奏意味都与这种“重复”有很大关系。余华抓住了人们经验与记忆的奥秘,他的叙述给人留下了不绝于耳的余音,而且其中人物的声音和作者叙述的声音还彼此呼应着,混响着,延伸在“虚构的风中”。余华不无得意地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这效果有些始料不及,但也是真实的,并非矫情。
智与愚的反照是余华另一叙述智慧的体现。无疑,他的文本的智性含量是最大的,但他的叙述人却常常“装傻”,他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所驱使的“只有命运没有性格”的符号,不只早期小说中的大量人物(他们有许多是没有名字的)都被余华“删减”为叙事的符码,人物的智能和判断力都随着其社会标识的消失而被剔除;就连福贵、许三观、许玉兰、李光头、赵诗人、刘作家这些活动在“真实”语境中的人物,也都是一些典型的“弱智者”,他们因此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的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
其实还有一点可能是构成了事实却又被忽略了的,这就是余华早期所刻意追求的繁,和近期所极尽追求的简之间所形成的对比反照。可以作这样一个发问:如果没有早期那些刻意的繁,人们是否还会如此情愿地承认他的简?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余华,而是另外一个没有先锋实验小说履历和背景的作家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否还会得到读者(特别是国内读者)如此的“高看”呢?反过来,如果余华没有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人们会不会已经像对待马原、洪峰等早期的先锋小说家那样,把他那些绞尽脑汁的叙事实验置之脑后、不再给以认真的关注了呢?这当然都纯属假设而无法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它们自己所形成的反差,从繁至简、或从“繁中的简”到“简中的繁”本身,也构成了余华自己的张力。从这一点,我们无论是按照古典批评家的“整体”理念,还是按照结构主义者的“文本”理念来理解余华,事实上都有了一个先在的背景和暗示,我们已经充分地知道了余华的能力,并将这种“了解”作为解读余华的前提。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余华具有“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脚踩在两个相距遥远的端点上,从容地玩他的游戏,徒然地令人艳羡和妒忌——他是聪明的。
“叙述的辩证法”还体现在“虚伪”与真诚、“高尚”与自私的关系问题上。1992年,余华在他的《活着·前言》里面写下了一句自我赞美的话:“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我理解这是一个提醒和辩解,余华非常担心人们会在两个极点的某一方面来理解他——不是担心误解他的能力,而是担心误读他的立场。他所要证明的是,自己不仅是一个高明的作家,还是一个高尚的作家。因为人们通常会过分看重他的叙述实验,而忽略了他的作品中的现实态度和情感含量。同时,在更深一个层次上,人们也通常会把余华看成是一个有“哲学倾向”的作家,而不太倾向于将他看做一个具有“历史倾向”的作家。我想,“高尚的作品”在其精髓上,当然更亲和于历史而不是哲学。
所以在这里,我要把他当作一个“书写历史”的作家来分析。的确,像加缪、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余华有哲学性的一面,但在我看来,余华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具有罕见的多面性。他的叙述虽然由于时间因素的剔除而导致了“对历史的抽象化”,消除了当代一般小说叙事中易见的“历史——社会模式”,凸显出另一个更带有普遍和抽象色彩的“生存——人性模式”,但在他的小说中,所谓现实和历史是没有界限的,他对永恒的讲述的同时就充满了历史感,甚至真切的历史情境。在这方面,不止《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等早期作品,连《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也都是好的例证。他的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对历史——现实的哲学分析”,在这里,他刻意混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或者说,他是“把历史当作现实”来写的。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它实际上是以一个少年的角度对当代历史的一种追忆,即良知被出卖、“强盗”畅行无阻的历史,受骗即意味着人生的开始,他将因此而成熟,开始地狱之旅。这简直就是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翻版了。不要忘记,在1986、1987年前后余华登上文坛之时,正是当代小说“文化——历史主义思潮”处于峰巅和走向深化的年代,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正欲萌发的时期,余华不可能没有受到这种趋向的感染,像苏童最初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一样,余华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文化——历史小说”的转型时期的路口上。
如果这样地看,很多作品就找到了答案。《一九八六年》所讲述的,实际是“历史是如何被遗忘的”这样一个命题。多年前的“历史教师”被抓走,意味着对历史的解释将成为一个谜。他被误认为已经死了,但他实际上却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人们眼中的“疯子”,而他所讲述的各种酷刑,正是历史的核心结构。他的“妻子和女儿”是现实的化身,她们和历史之间无论是怎样的遗忘和断裂,仍然有着扯不断的血脉关系。她们是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记忆中的“死者”,但“死者”——当年的历史教师,也似乎永远生存于被遗弃的历史之中、而无法“返回”到今天的所谓现实之中……在这个作品里,余华良苦的历史用心和对历史情境的敏感体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九八六,这个年份距一九六六这个特定的符号,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余华标定这个时间的点,是意在唤起人们对一个“历史单元”的关注。
《往事与刑罚》是另一个例子,它使我相信,余华说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绝不是虚夸。它的出现,确立了余华小说中“历史——刑罚”的基本模型,这篇小说几乎是不可思议地预见了不久之后的重大事件。它可以说是一篇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作品,在呈现为不断重复的刑罚的历史面前,知识分子显现了他们的二重性,即其注定下地狱、注定受误解的悲壮,和永远无法摆脱的软弱。他只能在无数次的惩罚经历中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并以包含了怯懦的死(自缢)来完成自己的自我拯救——从精神、人格和道义上的自救,勉强地续写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光荣的“士人”——知识分子的传统。这大约也是余华对当代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喜欢”的一个理由吧,他们总是找不到起点,而总是免不了重复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余华探讨历史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他在《鲜血梅花》、《古典爱情》这样的作品中,甚至以超验的文化理念与姿态进行历史的虚拟探讨;在《现实一种》里,他用一个近乎神话的残杀故事来隐喻中国人自残的本性与历史。但我要强调,余华对历史的叙述也同样是运用了“减法”。这减法的核心就是对历史的复杂枝叶与“广阔生活”的背景的剪除,通过对历史的叙事简化,使其“由历史抽象至哲学”。包括他自己个人童年的历史记忆也是这样,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里,历史作为个人经验,与宏伟的政治历史几乎已看不出有任何关系,但看不出并不意味着没有关系,主人公对众多惨痛的死亡的记忆和对“被抛掷”(海德格尔语)的处境的绝望感受,还有对历史与记忆的恍惚感,仍然有效地透视出一段历史的本质。
当然,“历史的减法”运用最好的,仍然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其实《活着》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红色历史小说的翻版”,它是真正的“历史背面”的写作。红色小说写的是“穷人的翻身”,而它写的则是“富人的败落”。只是余华简化了它的意识形态色调,将之还原为一个纯粹的生存着的个体。这样,它就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叙事——尽管它依然包含了历史。要是让我来概括,它所揭示的是这样三个层面:作为哲学,人的一生就是“输”的过程;作为历史,它是当代中国农人生存的苦难史;作为美学,它是中国人永恒的诗篇,就像《红楼梦》、《水浒传》的续篇,是“没有不散的筵席”,是“生者对于死者和死亡的回忆”。实际上《活着》所揭示的这一切,不但可以构成“历史的文本”,而且更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诗学”,是中国人在历史方面的经验之精髓。《许三观卖血记》也一样,他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当代底层中国人的个人历史档案。作为哲学,“卖血”即其生存的基本形式,是“用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作为政治,血是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基本形象和隐喻方式;作为美学,卖血的重复叙述构成了生命和时间的音乐。它同样是映现着中国人历史诗学的一个生动文本。
无疑,余华对历史的简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历史内涵的更趋丰富和多面。我们当然可以说,余华回避了当代历史的某些敏感的部分,但他同样用“虚伪”的担承方式,实现了相当“高尚”的主题理念。他的值得推崇之处在于,他不是着眼于历史的“社会性”构成,而是力图将之还原于人的“个体”处境、还原到“人”本身。这样他的作品可能削弱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力量”,但却获得了更久远的“人性力量”。在这方面,我相信余华是真诚的,虽然他“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但他的作品中无疑也饱含了知识分子式的历史良知和理想情怀。他秉笔直书,把锋芒直插到现实、历史和生存的最疼处。与此同时,他又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这是他的高度所在和真诚品质的另一体现。
但是这个“减法”也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结果:它使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很早就不得不面临着一个“熟透”的问题。“过早”的返璞归真,使他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这是他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但余华自己要重新胀破自己很难,而且读者的期待也被吊至很高,某种意义上《兄弟》之所以备受批评,与这种局面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