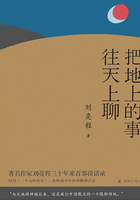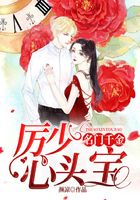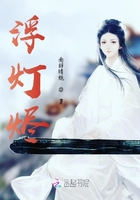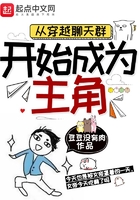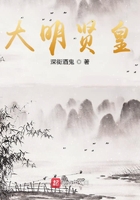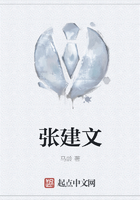然而曹老毕竟没有活到一百岁。这对中国文学艺术界来说是一大损失,对他的学生和朋友来说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我辈凡人谁也无法抗御。我们只能用这个来安慰自己。同时,我又想到,年过九十,也算是寿登耄耋,在世界上,自古以来,就是十分罕见的。曹老可以安息了。
北大以老教授多闻名全国。我自己虽然久已年逾古稀,但是抬眼向前看,比我年纪大的还有一大排,我只能算是小弟弟,不敢言老,心中更无老意,常常感到,在燕园中,自己是幸福的人。然而近二三年以来,老成颇多凋谢,蓦抬头:我眼前的队伍逐渐缩短了,宛如深秋古木,在不知不觉中,叶片一片片地飘然落下。我虽然自谓能用唯物的态度对待生死问题,然而内心深处也难免引起一阵阵的颤抖了。
嗟乎,死者已矣。我们生者的责任更大起来了。我感到自己肩头沉重了起来。
1987年9月13日
悼念姜椿芳同志
我认识姜老已经三十多年了。最初我们接触非常少,记得只谈过马恩著作的翻译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曾有过一个初译草稿,后来编译局要了去加工出版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温文尔雅,恂恂然儒者风度。
但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了解。只不过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以交往而已。
只是到了最近一些年,姜老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我也应邀参加,共同开了不少的会,我才逐渐加深了对他的认识。我对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我最初确实认识很不够。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我记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庆,在广州,在杭州,当然也在北京,我参加的会议内容颇为复杂,宗教、历史、文学、语言都有。姜老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但是,说句老实话,同样内容的讲话我至少听过三四次,我觉得简直有点厌烦了。可是,到了最后,我一下子“顿悟”过来,他那种执着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
姜老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他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异常关心。搞文化事业离不开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了解知识分子,他爱护团结知识分子,他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我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有一套具体的解决办法,可惜没能实现。他还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硬是拉了我参加他倡导的一个学会,多次寄票给我,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艺术细胞的人学会了欣赏。他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
拿中国目前的标准来衡量,姜老还不能算是很老。他的身体虽然不算很好,但是原来也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病。我原以为他还能活下去的,我从来没有把他同死亡联系在一起,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去做啊!对我个人来说,我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的打算要拉我共同去实现。我在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我幻想,总有一天,他会对我讲出来的。然而,谁人能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我的直觉落空了,好多同我一样的老知识分子失掉了一位知心朋友,我们能不悲从中来吗?
最近几年,师友谢世者好像陡然多了起来,我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一方面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抗御,也用不着去抗御。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大概也真正是老了,不免想到一些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事情。生死事大,古人屡屡讲到。古代有一些人对于生死貌似豁达,实则是斤斤计较,六朝的阮籍等人就属于这一类。我个人认为,过分计较大可不必,装出豁达的样子也有点可笑。但是,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师友一个个离开人间,能不无动于衷吗?我只是想,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我从来不相信轮回转生。既然如此,一个人就应该在这短暂的只有一次的生命中努力做一些对别人有益,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的事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能做到这一步,一生再短暂,也算是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了。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做到了。我认为,姜椿芳同志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椿芳同志可以问心无愧地安息了,永远安息了。
1988年1月22日
悼念沈从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离打电话告诉我,从文先生病危,已经准备好了后事。我听了大吃一惊,悲从中来,一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诧为倚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过了几天,肖离又告诉我说,从文先生已经脱险回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边一丢,从心头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书山稿海之中,从此“云深不知处”了。
到了今年,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应该写点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再动笔,一直拖到今天。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不太正常,我也有点不平。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披挂上阵吧。
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求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也许就是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彼此音问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的。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就是中山公园之类。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
小事过后,来了一件大事: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厄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这一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我没有资格对这一篇文章发表意见。但是,沈先生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不清;他有什么苦恼,我也说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凭了他那一股惊人的钻研的能力,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的赞扬。他成了这方面权威。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他手中的写小说的笔被“瞥”掉的时候,从国外沸沸扬扬传来了消息,说国外一些人士想推选他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奖,迷信的劲头,非常可笑。试拿我们中国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的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与小丘。同此辈争一日之长,有这个必要吗!推选沈先生当候选人的事是否进行过,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样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这里提起这一件事,只不过把它当作沈先生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点?),我不喜欢拜访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师友,比如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非常敬佩,但在他们健在时,我很少去拜访。对沈先生也一样。偶尔在什么会上,甚至在公共汽车上相遇,我感到非常亲切,他好像也有同样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我心里曾几次动过念头:去看一看这一位可爱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终没有行动。现在人天隔绝,想见面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规律。我知道,这个规律是违抗不得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违抗。古代许多圣君贤相,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方设法,去与这个规律对抗,妄想什么长生不老,结果却事与愿违,空留了一场笑话。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生离死别,我又不能无动于衷。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现在从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对我来说,忧思却着实难以排遣。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了。我只觉得大地茫茫,顿生凄凉之感。我没有别的本领,只能把自己的忧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1988年11月2日写于香港中文大学会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