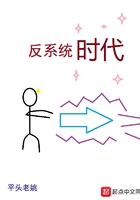腊月二十七那天,沈思一夜没睡,沈思并不是换了个环境就睡不着的那种人,只是躺在这诺大的船舱里,沈思的心里说不出来的紧张。他隐隐的感觉的自己离父亲很近,也许就一步之遥,也许相隔的就是船板的距离。看到他睡不着的样子,黄牙凑过来,“鱼儿,你要习惯,从明儿开始,至少有三个半月要在船上,要是老这么睡不着,可是还没到南洋也累垮了。”我知道他为我好,便点了点头,躺下身,闭上眼睛。
腊月二十八,是个干冷干冷的天,这天也是福清港最热闹的一天,昌丰号出港的消息一发出来,更多的人趁夜前往福清港。沈思站在船上看着那些人,心里也说不出来,这个时候总是要有活着的有死的,就看命硬不硬,就看运气好不好。这时候那沉甸甸的银子也不一定管事儿,但是没有银子,肯定是上不了昌丰号。
沈思也知道,昌丰号一般腊月不出港,但那是一般的时候,不是非常时期。现在如果再呆在福清港,说不准下一刻自己就变成屠刀底下冰冷的尸体。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很多人和沈思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很多人都挤上了船。
同沈思一样头天晚上上船的还有卢勤一家四口,听说卢大掌柜把妻儿带上,把小妾们全都扔在了福清城里,沈思觉得卢勤就是那种喜欢就喜欢的透彻,狠就狠到骨子里的人。
不过让沈思意外的是,霍老板并没有上船。二十七的晚上,钟爷遣奎生叔去福来酒馆找霍老板,但是霍老板却对奎生叔说,他要守着他的福来酒馆,把平时舍不得喝的,都喝了,一摊子一摊子的喝,喝到最后,一滴都不给那些畜生们留。而这些是沈思第二天听黄牙叔说给他的,黄牙叔说完后一笑,沈思瞅着那笑比哭还难看,“霍老板把那些珍藏了多年的酒一壶一壶的都喝了个精光,今儿一早奎生就看到他躺在那些酒坛子里,怎么叫也叫不醒了,他娘的多好的酒啊,把霍胖子都灌的醒不来了。”
沈思听完,想这样也好,好歹霍老板是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命,比屈死在屠刀下爽快的多了。虽然短短几个月,但是霍老板却像一位慈父一样处处照顾他,也会有训骂他的时候,但沈思知道,他是为自己好。
虽然心底觉得霍老板算是没屈着自个儿,但私底下沈思还是偷偷地哭了一场,黄牙看到沈思红红的核桃眼儿时并没有打趣儿这个孩子,他只是跟奎生叔说了句,“这孩子跟程大少爷像得很。”
沈思能上昌丰号,在别人看来是太幸运了,比如说平日里唠唠叨叨的大李。大李并没有沈思那么幸运,他是第二天才往昌丰号上挤。沈思站在船边看到奋力向前挤着的大李,看到他使劲的拽着前面人的衣衫,前面是一个体型庞大的中年男子,竟是用脚踢开了拽着他的大李。大李摔在地上,愣了一下又狠劲的往上爬,但是,灿狼见到他要爬上来,直接把他丢了下去,嘴里骂骂咧咧着,“滚,滚犊子,滚到安庆号上去。”大李含恨的盯着灿狼,“你还是我叔呢,你这么狠的心,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吗?”
灿狼的脸色不善,见他又要爬到船上,一手揪起他的衣领,“你他娘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老子给你只条明道你怎么这么想死啊。”大李挣扎着,但是灿狼还是狠狠地把他抛到岸上,我想这一下大李是完了,因为大李动了动腿却没起来,灿狼恶狠狠地看了一眼,便推开人群走出去。
大李见灿狼下来了,便腾的站起来,灿狼叔一手揪着他的衣领往上拽,一手扒开人群,“你他娘的就不听老子的,到时候别哭着让老子留你一命。”大李见灿狼把他带到船上,也不听灿狼嘴里叨叨的话,便高兴地说着,“叔,我知道错了,叔,我就是死也得跟着叔啊,我可就叔这么一个亲人了。”灿狼却狠狠的将大李摔在船板上。
沈思这才知道,原来福来酒馆的伙计们都是这些跑船客的孩子,大李的爹是跑船客,后来才得知,大李的爹就是死在十五年前,那一次死了八个弟兄,其中有一个就是大李的爹。
沈思是很在意灿狼刚才的话,他很少这么凶神恶煞的说些这样的话,他不是一个喜欢吓唬人的人,况且大李还是他的亲侄子。沈思站在边儿上,不知所措的看着灿狼气汹汹的走过去。
“鱼儿,原来你在这儿。”大李看到沈思兴奋地跑过来,“你小子是不是钟爷私生的,怎么对你这么好,顶亲生儿子都好。”沈思看了看大李,不明白他的话,大李见自己说的沈思都不知道,便有些得意的说了,“你不知道,钟爷的亲儿子听说昨晚上哭闹了一宿,今儿愣是送上了福顺号。”说完,大李突然偷偷看了看外面,凑过来说道,“你知道为嘛这船不让上自己人吗?”我摇摇头,大李又是得意的一笑,“昌丰号上一个就是一个人头钱,你上自己人,谁好意思收钱不是。”
沈思有点发晕的皱了皱眉头,这解释实在是幼稚的可以,到这节骨眼上还认钱不要命的当真是少。不过话说回来,十五年前的钟爷不就是要钱不要命,硬是把船出了。但钟爷这种人是把自己的命跟着银子一起掂量,但把家里人的命看的可比银子沉,对于家里人的性命,他定是不会有半点冒失的。
沈思看着大李一脸得意的表情看着船外面那些往死里挤得人们,突然觉得,自己也算是福清县幸运的。想起钟老大那句保他到南洋的话,却是让沈思有如身坐针毡。沈思心里掂量着,如果船出了事,他也一样到不了南洋,如果船没出事,这船上上百口子人也都一并到了南洋。况且,只要船靠了岸便是到了南洋,何来的只保他一人?沈思紧皱着眉头,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
“大侄子,这是又想什么呢,”卢勤并没有好事儿的看那挣扎往上爬的人,他则是走到沈思旁边,便打量着这条船便跟沈思说话。“没有,这船很大。”沈思随便说了一句,卢勤却把打量船的目光移到沈思身上,有些神秘的说道,“这船变了。”
沈思不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卢勤,卢勤无奈的摇了摇头,“只是觉得它变了,却看不出哪里变了。”
沈思听了这句话,没来由的翻了个白眼,便也开始打量这艘乌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