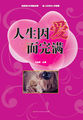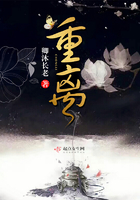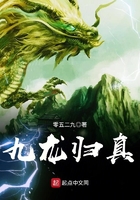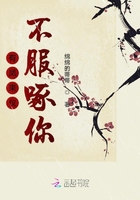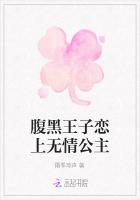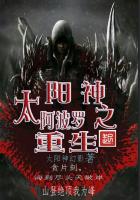锺惺(1574—1625)名下有多种《诗经》学著作,今存如《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明末拥万堂刻本),《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
二十四卷(明末拥万堂刻本),题锺惺、韦调鼎撰《诗经备考》二十四卷(崇祯十四年刻本),以及评点《诗经》等,不过除所评《诗经》确然可考外,其余诸种四库馆臣已疑其伪托,今人李先耕亦有考辨证之。锺氏评点《诗经》之作,《明史· 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皆未著录(《千顷堂书目》卷一“诗类”仅有吴骞补入“锺惺《毛诗解》又《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传是楼书目》著录“锺惺《锺评诗经》二卷/二本”,姚际恒《好古堂书目》著录“锺惺《批评诗经硃评》五本”,其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据大陆所藏,大致可分为凌序朱墨套印四卷本、泰昌元年三色套印五卷本、卢之颐溪香堂刻三卷本三个系统。
锺惺对于《诗经》的特殊兴趣,据其自述,首先缘于“家世受《诗》”,然由其《家传》述祖父、嗣父及生父的生平行迹推测他们的教育背景,此不过是门面话;而友人凌濛初说锺惺“以《诗》
起家”,倒是实情,锺氏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第,出《诗》房,座师为雷思霈。而之所以以文人手眼评点《诗经》,当与其为宣示竟陵派文学主张,与同乡谭元春推出古唐诗选评本《诗归》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该著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初步选定,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冬刻成;至于锺氏所评《诗经》,据凌濛初《锺伯敬批点〈诗经〉序》,锺氏尝于北京官邸中向他出示此评本,则亦至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秋前当已成稿(因锺惺此锺惺《诗论》,锺评《诗经》四卷《小序》一卷卷首,三色套印本。
《锺伯敬批点〈诗经〉序》,锺评《诗经》四卷卷首,朱墨套印本。
后即僦居南都,乞改南后未再任职于京师),凌氏随后携归吴兴,授侄凌杜若梓行,是即凌序朱墨套印本,为初评本(溪香堂刻本亦初评本)。锺惺《诗论》中所言“业已刻之吴兴”亦可证,此后则“再取披一过”,示又重评,今卷首收录锺氏此《诗论》的三色套印本,当属增刻再评本,其以朱、黛两色笔圈评,即为区别初、再评,《诗论》即锺惺为此增刻再评本所作序,末署“明泰昌纪元岁庚申(1620)冬十一月竟陵锺惺书”,可据以获知相应的刊刻时间。本文所引锺氏《诗经》评语,即据此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序及正文首页钤“沧苇”、“丁福保印”、“丁福保字仲祜”、“震旦大学图书馆丁氏文库”等印,反映丁氏得季振宜旧藏、又以文库入藏震旦大学图书馆的递迁关系。
一、从经学笺注到文学评点
关于明代《诗经》学的演变情况,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当专门而深入的探讨,可以参看,这里仅对锺惺评点《诗经》产生的背景再略作交代。明初官学,袭元之旧,朱熹《诗集传》定于一尊,尤其永乐间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奉敕纂修《五经四书大全》,《诗》“实本元安成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命科举以为程式,于是不仅古人传注训释几废,且因经生以帖括为顾梦麟《诗经说约》卷首自序即批评说:“《诗大全》本疏义,犹《四书大全》本辑释,皆抹去向人,奄为己物。然《四书大全》之为数繁,繁则虽费料拣,已厌众观;《诗大全》略矣,至疏义中精析比兴处,又尽芟之……”(崇祯织帘居刻本)务,又专以诵习时文为捷径,连经义亦被割裂遮蔽,此可以看作是阐释者与经典之间的主体性的断裂,《诗经》学之衰,因成必然之势。明中叶以来,人们正是在对此弊有所反省的基础上,开始萌发重建包括《诗经》学在内的经学阐释之自觉要求,而其清算的标的,很自然最终指向了一家独尊的朱熹。这种重建《诗经》阐释的运动,大抵朝着如下两端开展:一是所谓复古的面向,即摒弃墨守朱子一家,通过杂采旁搜宋元以上诸家疏义训释,较为系统地复原一种历史经验结构,尤其汉儒的解说,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重新被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其权威性而特加标举,这是一种知识的、客观的重构路径与要求,实际上成为清代汉学的发端,然其成就与影响确尚有限。一是在心学的影响下,将圣人之学看作是“学以求尽心而已”,因而自逞胸臆,大胆怀疑一切,试图依靠个人体察或经验,超越历史性存在的规定,达成对作者意图及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的重新认识,从而为经典的自由阐释开启了空间,这是一种体验的、主观的重构路径与要求,虽然不可切断与宋学语境的联系,但因阐释的客观性与权威性被颠覆,朱熹之学仍被作为主要的诋排对象,如锺评《诗经》即标明是针对朱氏《诗集传》,谓欲“稍为之导其滞,醒其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径其迂”(《诗论》),亦算是一种“自信于心”的表现。
经学在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为文学的独立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本来在诸经中,《诗经》便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文本,故如俞樾发现,早在唐代,就有成伯璵《毛诗指说》在其第四篇“文体”
中,于《诗》作句法、字法、章法之评,开了以后世文法解经之先;而在宋人诗话中,亦不乏对《诗经》所作的文学解读法。然而,亦唯有在明代中晚,这种强调《诗经》的文学特性、要求以诗沈万钶《诗经类考》卷首沈思孝所撰序曰:“每谓晚近墨守一家言,兀兀以帖括明《诗》,卒不知《诗》为帖括障也,傥先贤有知,宁不为此经失叹。”(万历间刻本)王阳明《重修山阴县学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四部丛刊影隆庆刻本。
俞樾《以后世文法读经》,《九九销夏录》卷二,光绪十八年刻本。
解《诗》的阐释才蔚成风气。如袁仁《毛诗或问》,不仅“诋朱子解诗,如盲人扪象”,并且申论《诗》与他经不同,“他经可理测,而《诗》则不落理路;他经可意会,而《诗》则不涉意想”,实已着眼于《诗经》特有的文学性,而欲将对其解读从诸经经义中剥离出来,故四库馆臣指斥“其言甚诞”,认为“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于持以解经乎”;至于乌程闵氏朱墨所刊戴君恩之《读风臆评》,更被四库馆臣论定为“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自明代中期以来,虽然因为举业,已有书坊在所刻《四书》上加以圈评,并且文学家们亦已将文学评点的手段运用于史籍,显示了一种文学批评的眼光在集部以外的拓展,但敢于在《五经》一类经籍上施加圈评者毕竟不多见,更何况不是从经学自身的传统去评经,这仍需要非常人所有的胆识。
其代表人物,一个是孙鑛,另一个便是锺惺,顾炎武就曾引述钱谦益《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中讥弹他们有关评点为“非圣无法”的议论,指出:“钱氏谓古人之于经传,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谁敢僭而加之评骘。评骘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锺氏。”故自然被视作“败坏天下”之人而大加挞伐。
我们从冯元仲为孙鑛《诗经》评点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到他一再申诉《诗经》在诸经中如何“别竖宗派”,无非在于“用韵”、“咏歌”等诗歌特性方面“其奇更甚他经”,因而要求将之置于整个诗歌史序列中加以认识:“夫《诗》之系,一传为骚,再传为汉魏乐府,再传为六朝,再传为四唐,嘻,观止矣。乃盱衡畴昔,而中晚不及盛初,盛初不及六朝,六朝不及汉魏,汉魏不及骚,骚不及经,而欲望宋之腐生、今之博士弟子明之,其与秦□汉溺,是何异《日知录集释》卷十八“锺惺”条原注,道光西溪草庐刻本。
邪?”尽管其所持仍是传统一种复古的文学史观,并无多大新意,然有意重申这一点,却明显是为孙、锺辈消解《诗经》神圣的儒学光环张本的,他以王世贞为孙氏先导,锺惺为孙氏踵武,而锺惺确亦以所评《诗经》与《古唐诗归》构成相互衔接的诗歌批评史系列,实现了这样一种要求。鉴于孙鑛在文学上的兴趣与成就毕竟有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运用一种相对定型、成熟的评点法评骘《诗经》,真正从经学解释的立场转到文学鉴赏批评,并藉以宣示其体系性批评观念与文学主张的,是始于锺惺这位竟陵派代表作家,更何况这种对《诗经》施以主观鉴赏之批评的影响亦自竟陵乃大,稍后如章调鼎《诗经备考》、钱天锡《诗牖》、万时华《诗经偶笺》、贺贻孙《诗触》等皆承其门径,因而被视作是竟陵《诗》解之流亚。
与竟陵派作家交情颇深的万时华,在崇祯六年(1633)为《诗经偶笺》所作的自序中,曾为申张自己的作意,总结出当时解读《诗经》的三大蔽障:“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读《诗》往往“易入处便入”,而少“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经有传,而逐传者遗经,因传而生训诂,而袭训诂者迷传,塾师讲堂,转转讹谬,失古人之唱叹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句字以为纲,强疏其支派以为断,千年风雅,几为迂缀庸陋之书,嗟乎,蔽又甚矣”,可以看作在晚明特定的时代风气下对传统《诗经》学的一种宣战,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承锺惺以主观鉴赏之文学批评解《诗》的一种声援与表彰,锺惺《诗经》评点的积极意义亦恰可从此中抉发。首先,这一种评点是以诗人为职志,建立其《诗经》阐释的主体性,故其立场完全站到了文学本身,从阐释目标来说,基本摒弃了汉儒的政治化意图与宋儒欲在经典中抉发所含深刻道德内涵和形上原则的意图,而由阐发上述意义转到了揭示作者“如何表现”的艺术经验,从而终于将《诗》从经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了其文学生命。其次,强调从己意出发,发挥阐释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去发现作者“深心”,发现作品中的“玄致”,亦即意味着肯定个人独特的阅读经验,相信个人阐释的有效性。再次,从阐释方法上说,因《诗经》的文学特性,敢于破除传统注疏之学那种知识主义、理性主义的藩篱,而将阐释者对于文本的理解看作是一种读者与作者直接联结的心理重构过程,从而在超越存在的历史性规定的同时,为自由阐释、自由接受进一步拓展了空间。
二、《诗》为活物:《诗论》的阐释观念
锺评《诗经》卷首所列《诗论》一篇,是锺惺阐述其说《诗》观的总论性文章,然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经》学的范畴。可以说,这种以诗人手眼解经的方式,亦是对明代评点之学的一种开拓,因而,它所表明的观点,于《诗经》之文学阐释以及整个诗歌评点之学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有关《诗经》的阐释,虽然自汉以后已由纯粹的经学领域逐渐拓展至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域,但是从解读者的立场来说,能够完全抛开经学传统而自觉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去指导阅读的,毕竟要到中晚明才真正形成。锺惺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立场下,提出《诗》为“活物”的阐释观念。其论如下: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能如是,而《诗》
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
他援孔子及其弟子所引《诗》,春秋列国大夫于盟会聘享所赋之《诗》及汉韩婴所传之《诗》,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又觉未尝不合为例,说明“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本来就是随时、随事、随人、随场景等的不同,而取断章之义以应之,求其一端而已。用古之断章取义的事例以为论据,不过是他的论辩策略,实际上他真正想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说《诗》者,他的解读都受到其主观的阐释角度及其对作品语境、事理、构架等认知程度的限制,事实上不可能企及与《诗经》原创之全部意义的重合,是谓“不必皆有当于《诗》”,而这与其说是历代说《诗》者自身主观条件的差异造成了《诗经》意义诠释的活泛多变,毋宁说是《诗》本身所贯注的天机般宇宙人文精神之大规定了其为“活物”的性质。因此,他认为《诗》的存在自完自足、自现自明,并不以历代说《诗》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所以为经也。
“活物”一说,本来是性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心性之体用相联结,讲的是人心之自我觉照,如朱熹在答“仁有生意如何”之问时,谓“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乌能辞逊、羞恶、是非”;蔡清解孟子《尽心章句上》则曰:“心是活物,大凡说心处,都是指其活者,言所谓虚灵知觉者也。”虽然其指归在于“主敬”而见仁体,在于常存天理之大本,因而具有道德伦理的属性,然从其涉及的有关思维形式及作用的探讨来看,仍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锺惺在这里将原本运用于认识主体的这一概念移植到认识客体身上,我们确可以理解为他是将“心”外化为一种客观意识,即将《诗》视作常道所寄的一种本原性精神存在,“此《诗》所以为经也”。这种本原性存在神明不测,无定在,无穷尽,在说《诗》者因其知觉、思虑而默自体认,此即谭元春所说的“传世者之精神,其佳妙者,原不能定为何处,在后人各以心目合之”。既如此,历来说《诗》者所抉发的意义,原不过是阐释者自己主观经验所触发的那一部分特定的关联,并不能因此说穷尽了《诗》的全部意义:
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
锺惺认为,无论汉儒的据《小序》说《诗》,还是朱熹之注,尽管被奉为权威,然其所指人、事本来就未必可信,更何况“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不过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它应该是帮助读《诗》之人立想的起点,所谓“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者也”。对于说《诗》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体认独立存在于文辞之外的神明莫测的“精神”。其道理与谭元春在说《庄子》时“益叹是书那复须注,不易之言也”是一样的,就算你完全解通了文辞,但对其文辞间所发放出来的真正意义却可能毫无所感。再进而论之,古之作者与述者在阐述与注解的过程中,本来又有预设的主观叙述立场与角度,其目的亦在启发觉悟而不在画地为牢,万万不可遂将之视作解读《诗经》之意义的终结:
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肖立想,而贤者听之。解经者,从极愚立想,而明者听之。今以其立想之处,遂认为究极之地,可乎?
至此,锺惺的《诗》为“活物”说已颇为明了。
首先,他将《诗》的解读认定为说《诗》者对一种本原性精神存在的体悟,《诗经》作为这样一种认识对象自完自足、神明不测,它在为每一个认识个体提供某种超历史的客观性阐释可能的同时,成为他们各自“虚灵知觉”的载体,这便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共享的主观感通性的基础。其次,对于说《诗》者这一认识主体来说,不仅所发挥的认知作用是能动的、自觉的,而且其认知所得的主观经验亦是个别的、独特的,所主在我,“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普遍性的解读意义,倒是这种对本原性精神存在的体悟要求赋予了他们“神而明之,引而伸之”的解读规则。再次,这个体悟、认知的过程并非是固定、封闭的,而是一种不断变化、开放的活动,读者个人的主观情趣不仅随时代的变化而不同,而且随各自处境的变化而“能新”,“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此所谓“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在这种情形下,正如他又一次以驳论的形式所强调的:“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而这种认识的开放性,在锺惺看来,恰恰亦是《诗》无定在、无穷尽的本原性特征所赋予的———“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因此,他最后得出结论:
故说《诗》者散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
之用且万。
我们看到,与谭元春《诗归序》所说的“古人大矣,往印之辄合,遍散之各足”如出一辙,这种以“活物”视《诗》的观点,说到底还是围绕着说《诗》者这一认识主体体道证悟式的“虚灵知觉”作用展开的,《诗经》与说《诗》者之间构成体用关系,不仅令他们的以述为作归之于心性潜能的自我实现,而且在肯定这种个人阐释活动合理性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认识空间,这又好比谭元春为其《遇庄》解题所说的“‘遇’之为言,甚活甚圆”,是为“活物”说要义之所在。
当然,锺惺《诗》为“活物”说的提出,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主要是为他们如同选评古、唐诗那样真正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解读《诗经》作品张本,据此,他可以大胆废弃既有之传笺注,而如《诗归》评点一般,感必由己,取其会心而已,“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其指归则落实于“求古人真诗所在”。如果要在说《诗》的传统中探溯锺惺此说之渊源或者说根基的话,我们很容易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发生联想,后人早已将这样的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然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记载的“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其原义不过是说,对于《诗经》文本的理解,不应该拘泥于一例字辞义项的诠释,而应该据其所述语境的具体变化与字面背后的含义灵活分析。虽然这种观点与孟子强调说《诗》的主观性有相通的一面,但它仍然是在文本释读层面上论说的,王应麟指出:“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是一种极为精审的判断。叶维廉在解说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一段话时,认为它含有两个传释活动的题旨,“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是关及“部分与整体”相互的关系,而“以意逆志”是关及读者与作者之间在作品上相遇所必须有的“调协”、“调整”,应该也是看到了两个传释活动有不同的指向。
而如锺、谭那样试图超越文本释读层面,直取作者之文心,显然主要是以孟子之“以意逆志”说为依据的,这不仅因为孟子的“以意逆志”本来就具有心性说的哲学基础,而且因为此说运用于文学鉴赏时,关注的亦始终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内省直觉的精神感通。事实上,竟陵派作家也正是自我标榜以孟子“以意逆志”说为准的而推展至所有诗歌作品之鉴赏批评的。
在谭元春与蔡复一的一封书信中,他这样说道:
《易》曰:殊途同归。以春小儒之见,上下今古,诗人之致,诣之深浅、力之厚薄不同,而同者归也。孟子曰:固哉!
高叟之为《诗》。又曰:以意逆志。又曰: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世。此三言者,千古选诗者之准矣。春虽不能至,窃以自勖。
这段话庶几可以当做《诗归》的纲领。所谓“归”,作为一种目的的指向性,当然是指一种本原性的精神存在,所求“古人真诗”,亦即这样一种“精神所为”。尽管古今人我根器各有不同,但因所求指归相同,读者与作者便可期相遇,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被展开的。孟子所说的“固哉!高叟之为《诗》”,除了可以理解为高叟说《诗》过于拘泥文辞表面的意思而未获其全旨外,还可理解为他未能真正推其心去领悟诗人之本心;而对于读者来说,“以意逆志”就是要以一种充分内省的体察去以心会心;至于“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世”,则是实现这种精神感通的主要格致手段,逆志必须知人,知人必须论世,它们是维系读者与作者之间主观共通性的一项重要条件,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读者同时认知他自己的历史依存关系。故谭元春引孟子“三言”以为选诗标准,重心只在“以意逆志”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对于孟子“以意逆志”之“意”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歧义。《孟子》旧注如赵岐注以为“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注亦认为: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都明确将此“意”看作是读者主观之心意,且是先于阅读文本而已独立存在,解读的过程乃是读者之意与作者之志调协的过程。而如清人吴淇则力辩曰:
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意曰志……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
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者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将“意”理解作作者之意,它是作者之志的载体,而又非外显的文辞层面,读者应循此内蕴去求获古人之“心事”,因而在使“意”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同时,要求读者直觉地把握。竟陵派作家的《诗》为“活物”说当然是承前一种理解而来,从上面分析的锺惺《诗论》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说《诗》“不必皆有当于《诗》”,“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神而明之,引而伸之”,所强调的皆为读者主观之意,其“意有所得,间拈数语”之“意”亦可为证。不过,由于这种读者之意,是基于人性论的心与心相通,而诗人之志的指向又具有某种形而上意味,两者在容受“道”
的过程中“殊途同归”,故又要求读者“虚怀独往”,在文辞之外直觉地经验作者所经验的审美状态或活动,如锺惺又说过:
要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则经纬开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它们可能在共同体认山水之精神的场合下遇合,这时的读者之意也就化为某种客观意识,与作者之志不分彼此,自然也就超越了述作之分限。从这一角度理解锺惺的“一往深心”,与那种“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的客观性诠释要求似乎并非不可调和。
这表明竟陵派作家运用“以意逆志”说所建立的文学鉴赏批评的原则,与创作上“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在强调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始终有“古人之精神”这一客体化认识目标的内在规定。也就是说,这种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恰恰是在与“古人之精神”感通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的对象与体验者对诗的本质冥想亦因而构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三、锺评《诗经》的阐释
方法与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个人阅读经验记录的文本,要从锺惺的《诗经》评点这样印象式的随兴之笔中归纳出其阐释方法与基本特征,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好在先已有其友人凌濛初在《锺伯敬批点〈诗经〉序》中,为读者总结出了“领会要归,表章性情,摘发字句,标示指月”十六字要诀,并认为其作“为言虽无多,而说《诗》
诸法种种具备”,可看作是有相同评点经验与取向之同道会意的提点,值得援据。大致说来,其中前两句关乎文本阐释的内容,要在通过一种“体验的”阅读方式,发现作者的意图;后两句关乎文本阐释的形式,由表层的言语构成分析,进入对意义的揭示,只不过根据诗歌“神在象先,意在言外”的特性,这种对意义的揭示无法完全依靠语言解释加以实现,而须是一种“妙悟”的指引。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摘发字句,标示指月”。俞樾曾将明代中叶以来包括锺惺在内突起的经学阐释变异,概括为“以后世文法读经”(见前引),有据而不尽确然。锺评《诗经》的阐释是通过字句的圈点与眉批、夹批、尾批及总批等评语得以呈现的,其对《诗经》文本言语构成的分析,确可分为字法、句法、章法等样式,他与谭元春评选的《古唐诗归》亦同此例。字法如: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黛笔眉批:“‘关关’二字叠得妙,妙在生而有意,叠字之法熟不得。”
《周南·桃夭》“宜其室家”朱笔眉批:“‘宜’字妙,只是个停当相安意思,女子无非无仪,一停当相安,便是求加焉,即失之矣。”
《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下上其音”黛笔眉批:“‘音’字从‘飞’字看出,故曰‘下上’,妙乎!”
《邶风· 凯风》“吹彼棘心”、“吹彼棘薪”朱笔眉批:“‘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用笔之工若此。”“有子七人”
黛笔夹批:“四字严甚。”
《邶风·静女》“说怿女美”黛笔眉批:“四字简妙,可该篇末二语之义。”
句法如: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黛笔眉批:“看此四句,情思起止,不可语人,亦不能自主。”
《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黛笔眉批:“重一句,妙。”
《召南· 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朱笔夹批:
“句法。”
《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黛笔眉批:“‘我心匪石’四句,皆深一层,妙极,皆不是寻常自反之言。”
《邶风· 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黛笔眉批:
“各后二句与前二句,紧缓全不相蒙。”
章法如:
《周南·卷耳》“陟彼砠矣”一章黛笔眉批:“此章促节甚,调甚悲。”篇末黛笔总批:“此诗妙在诵全篇,章章不断,诵一章,句句不断,虚象实境,章法甚妙。”
《周南·麟之趾》黛笔总批:“各章末句接得极简极直矣,却用‘吁嗟’二字,多少回翔,此古人笔力之高,笔意之妙。”
《邶风·匏有苦叶》朱笔眉批:“妙在四章开说,若不相蒙。”
黛笔总批:“四章止‘济盈不濡轨’二句带刺,余皆说正理,而其失自见,此立言深至处也。”
《邶风·简兮》“山有榛”一章朱笔尾批:“要知末章意,即在前三章内,非两层。”朱笔总批:“此诗前三章,自是一种素位之乐;末一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然一时俱有,无两层。”
从以上随机所取例证,可以看到,锺惺《诗经》阐释的关注点,确已转到了语言分析和写作本身。但首先,这种由字句入手的分析、提点,与传统笺注之学的“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那种“因辞演义”的阐释程序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通过文本的逐字逐句训释,包括古今名物制度的证考,以求著明经典的语义与旨趣,复原一种他们相信存在的本文意义,而是相当随兴地将自己对诗艺的直觉体验、感悟揭示出来,所谓“意有所得,间拈数语”(《诗论》),形式相当自由,它可以是评介诗学技法上的用意与妙处,如对“关关”叠字生新的欣然会意,对《卷耳》章法勾连的细读;也可以因个人对字、句含义的申发,发掘作品的深意,如对《桃夭》“宜”字的阐发,对《简兮》各章表意的揣度;即便偶有对字、词的解释,主要亦服务于赏文析义的需求,从阐释功能上说,很显然是由诠释转到了鉴赏批评。而与时文相关的评点相比,不可否认,《诗经》评点的产生,是受到了制艺的圈点评骘以及文章家为将古文之法用于时文而施行经典评点的影响,看似皆侧重辞章作法,然却已非那种专为讲求起承转合的文章法式结构分析所能涵盖———那不过是用于文本表层结构重建的一种模仿。在锺惺的《诗经》评点中,虽然也注重字句章法的结构分析,勾划段落层次,标示语脉文经,但文法本身不是目的,我们从其对《柏舟》、《简兮》的句法、章法分析中,可以看到如何在字句篇章的关系中求获意义;从《麟之趾》的章法分析中,可以看到如何将文法的承接与意义之外的诗味之体验联系起来;总之,是抓住他自以为关键的字句,通过揭示其在文法关系中的特殊意味与作用,展现作者“如何表现”的审美经验及文学旨趣,表达诗人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目的在于他在《诗归序》中所说的,“求古人精神所在”、“古人真诗所在”,因而仍是一种直取“文心”式的鉴赏批评。
其次,既然是真正从以诗解《诗》的立场出发,鉴于对诗歌象喻性特质的认知,即诗歌传达超越言、意层面的认知,我们看到,锺惺的《诗经》评点尽管也从文本表层的言语构成———字句入手,却全然不循笺注之学为求更为准确、客观的诠释,建立更为谨严之规则体系的发展路径,而相反是运用一种郭象注庄式的阐释方式,寥寥数语,探其玄致,但求会心妙悟,常常是以泛涵性极大的暗示性阐释话语,标示理解的可能性,甚至“不说破”、“说不出”,意在通过悬置意义指引人们突破理障,拒绝定着的思维,然也因此走向一种神秘主义;其目的说起来只是为不解者提供灯烛舆杖,借径开悟,发覆指迷,而非答案本身,此即所谓“标示指月”,背后又有对本文意义是否能必然获致的“遇”、“合”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却是对传统经学诠释方式的一种大解构。
这种阐释方式与话语,在他与谭元春评选的《诗归》中有相当鲜明的呈现,而在上举《诗经》评点中同样存在,如多处出现的“妙”
评,有的并无具体说明,《江有汜》“不我以”何以“重一句”即“妙”,全凭读者自己意会;《召南· 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朱笔眉批:“悟此二语,省得多少心力,落得多少受用。”为何解悟后可以省心受用,有暗示但却相当活泛;其他未见上举的例子尚有很多,如《召南· 小星》“寔命不同”,黛笔眉批曰:“大识语。”
《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黛笔眉批曰:“‘怀春’二字甚微,莫粗看。”而在不少诗章的字句夹批中,诸如“厚语”、“奇语”、“深”、“婆心”、“不必解”、“文字奥甚”之类,更像是禅宗“活参”式的解读,表明他确实将《诗经》评点完全视同《诗归》评点。
推究其来源,应是受到了刘辰翁诗歌评点很大的影响,故尽管自钱谦益以来,清人不断讥评他们这种阐释方式与话语为“尖新隽冷”、“钩深抉异”、“一知半解”,却毕竟开放了一种自由阐释、自由接受的意义空间。
再看所谓的“领会要归,表章性情”。诗道性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命题,虽经历代变迁而内蕴有很大差异,然以性情为诗歌表现之指归却终未改变。从整个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来看,性情说在风云激荡的中晚明诗坛亦已重新构成中心话语,而与崛起的新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因此,锺惺在《诗经》评点中以“表章性情”为阐释意向与使命,是自然而然之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兹举二例:《邶风·绿衣》黛笔眉批:“‘俾无訧兮’,失意之人不求他好,但求立身无过之地,以免于罪而已,犹有畏心;‘实获我心’,若以为固而安之矣。”该诗黛笔总批:“诗可以怨,非一于怨,亦非一于不怨,盖自有处怨之道,‘我思古人’,处怨之道也。”《召南· 摽有梅》朱笔总批:“三个求字,急忙中甚有分寸。”黛笔眉批:“《诗》至摽梅,而后可与权,此女子是机警人。
予尝谓女子全节,不专在贞一,而在机警。”锺惺在这里颇不惜笔墨,对诗中所表现对象之心理、行为作了种种揣测、阐发,情思既极细腻,论议又重在表现自己独到的识见,并且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表章性情”,其实同时亦关涉到阐释的方法,即如何通过性情的体察,发现作者的意图,达成“以意逆志”,意味着将阐释者对于文本的理解看作是一种读者与作者直接联结的心理重构过程。宋儒的经学阐释实际上已经有意将之标举为新方法、新见解,如朱熹就曾说过:“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表明欲直接在对文本的虚心涵泳、切己省察中获致作者之志,令《诗经》阐释从繁琐的经师之业中解放出来,明代的心学不过是通过“心即理”的本体转换,将之更推向一种极致。
诗有言外之意,对诗人而言,性情亦有隐微,要发现并理解作者的意图,完全依赖词语的语义诠释恐怕未必可行,程颐早就看到这一点:“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晚明文人更是极端,如与锺惺同时的沈守正,认为“《诗》之微妙,须人自会,出口落笔,便成筌蹄。政如宣尼提诲三千,忽欲无言;释迦说法四十九年,未曾有字。妙得斯旨,方可言诗;若株守陈编,翻成毒药”;谭元春在多次阅读了《庄子》本文、郭象、吕惠卿注及其时焦竑、陆西星诸人的注解后,“益叹是书那复须注,不易之言也。注弥明,吾疑其明;注弥贯,吾疑其贯”。以此为理由,锺惺的《诗经》评点干脆拆除章句训诂的阶梯而直接进入玩味、体察,期待与古人的精神遇合。这种体验本身是完形的而非解析的,因而便有“领会要归”的要求,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其说出的往往是个人体验的结果而非过程,不过,锺惺的文学家手眼,亦会令他在一种即时的情境体验中,将自己的心理经验开示于人,上举《卷耳》黛笔眉批从首四句看出“情思起止,不可语人,亦不能自主”,便是一很好的例证;即便如《关雎》黛笔总批:“哀乐,情也,不伤不淫,情而不失其性也。‘思无邪’亦是此意。诗理性情,故以为《诗》始,然皆根‘窈窕淑女’来,故章章言之。”看上去只是申发汉、宋之儒说了又说的陈词,但因此为朱笔眉批“看他‘窈窕淑女’三章说四遍”的补笔,实亦仍从一种情境体验出发来表章作者的主旨。
在锺惺的《诗经》评点中,比较突出地显示他那种“领会要归,表章性情”特点的,是自《卫风· 有狐》之下,渐始将诗旨标出,如:
《有狐》,“思配也”。
《木瓜》,“笃友也”。
《黍离》,“悲故都也”。
《君子于役》,“闺思也”。
《遇庄序》,《鹄湾集九卷遇庄一卷》卷首。
《中谷有蓷》,“悲离也”。
《葛藟》,“叹依人也”。
《采葛》,“有所思也”。
《大车》,“畏也”。
这种做法,看似与《小序》首句所标并无二致,若细究其内蕴,却已明显体现出上述阐释方法的变化。《有狐》,《小序》以为“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朱熹《诗集传》承其说并《郑笺》,谓“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陈子展先生嫌其多此一举而“未免授人笑柄”,而锺惺据文本语境,直以“思配”标出。《木瓜》,《小序》
谓“美齐桓公也”,是卫人为厚报桓公救援所作;朱熹以其对文本的体味,提出新说:“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锺惺未取其说,以“笃友”作解,清人如姚际恒、崔述,亦皆以此诗为朋友馈赠之作。《黍离》,《小序》谓“闵宗周也”,朱熹承其说,而锺惺亦只是将之一般化为“悲故都也”。这里要讨论的,还不是哪一种解释更为接近作者本来的意图,而是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锺惺所标出的诗旨,已完全将诗歌阐释与汉儒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考察与政治化话语脱离开来,而只是将之推展到一种普遍性的寻常人情来加以体认,其体验的目标,与理学家欲在经典中抉发所包含的深刻道德内涵和形而上原则亦不相同(当然还不能说全然无关),这种诗旨的把握,实际上就成为他深入每一首诗不同情境的钥匙。
以上主要围绕锺惺《诗论》以及《诗经》正文评点,对其在《诗经》阐释方面的观念、方法与基本特征以及积极意义作一些初浅的探析。其实,关于锺惺的《诗经》评点还有许多面向值得进一步考察,而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在晚明《诗经》学变异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尚需要将之与中晚明其他各种类型的《诗经》学著作作更为深细的比较研究;同时,也需要将之与锺惺、谭元春评选的《古唐诗归》进一步联系起来加以考量,以求更为完整地揭示锺惺在诗歌评点学方面的特色与贡献;此外,还应该充分注意到锺惺《诗经》评点的局限及其负面效应。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在此一专题上继续延展探讨的研究空间。
(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9辑,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