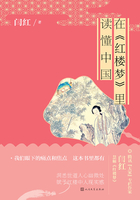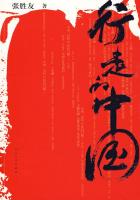莫言:我一直把“变化”作为自己写作的追求,总是希望新作不重复旧作,即便做不到脱胎换骨,哪怕有一些变化,也是好的,否则我的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但每个人都有局限,这局限就是所谓的“风格”。这是令人痛苦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关于儿童视角,在我的创作之初,是一种下意识,后来上海的程德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产生了警惕。在以后的创作中,尤其是长篇创作中,我几乎没有使用儿童视角。但这部《四十一炮》,却是我有意识地从我的武器库里,再次拣起“儿童视角”这门生满了红锈的“追击炮”,当然我也打磨了它。我觉得应该把我的“儿童视角”进行一次告别式的使用。过去我的儿童视角小说中,那些孩子不但精神没有长大,连身体也没有长大。但《四十一炮》中的主人公罗小通,身体已经是成年人,没长大的只是精神。他其实是想借着这个诉说的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童年。当他把自己的童年故事讲完,他就应该长大成人了。所以我在后记中写:《四十一炮》之后,我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将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
关于乡土,我想不仅仅是我难以逃脱,绝大部分作家都难以逃脱。即便你给你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另起一个名字,甚至把许多外地的风景和风俗移植过来,但骨子里,还是你自己的那块乡土。你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语言,只能是你熟悉的那部分人的思想和语言。另外,关于乡土,我的理解并不仅仅是指农村。乡土应该是一个和童年紧密相连的概念。也就是说,你童年时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乡土。上海也是乡土,北京也是乡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乡土作家。对乡土的依恋,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并不仅仅限于作家。这种依恋,含义很丰富,其中有爱,也有恨。
作家不为批评家写作。
杨扬:对于《四十一炮》,我想批评的阐释不会像《檀香刑》那么顺当,你很难一下子迅速提炼某个明确的写作意图。不知道您在这部新作写作中,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意图要表达,或者说,希望得到哪方面的批评回应?
莫言:这部小说,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结构上,都与《檀香刑》有区别,内容上区别更大。《檀香刑》肯定不是为了评论家写作,说句很不合时宜的话,是为了我自己的写作。评论家喜欢什么,我并不清楚。而且,评论家也是各有各的喜爱,要想投他们所好,何其难也。
书写完了,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现在,我的兴奋是在一部新的作品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反映我会留意,但决不会为了几句批评和夸奖而改变自己。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其实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后来的因素,只能让他对这些作品做一些微调,不会有大的改变。
不要把批判和反思当作旗号,
扛出来吓人。
杨扬:您在苏州大学演讲中谈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问题,想必是期望与那种戴着知识分子有色眼镜的“为老百姓写作”的启蒙文本做出区分?我想这也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反省。现在批判和反思成为一种标签,评论家说一个作家作品深刻,便说该作家作品是对现实的批判。但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别,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不同见不到了,好像一提批判,艺术便会自动形成。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作家对待现实不要反思、批判,而是说那种知识分子腔的文本写作,首先是从摆弄所谓的批判姿态开始的。表面上,搞得像真的一样,一会儿提倡这个,一会儿又提倡那个,但创作是越来越疲乏,只有一大堆所谓的思想在那里。您在新作后记中对所谓谈思想的批评家和作家表示了一种轻蔑,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个提法是针对着包括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家们那种畸形心态的,本身并不严谨。大家听听而已,不必认真。我的想法是:第一,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既不能建党建国,更不能亡党亡国。第二,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那么神圣那么崇高。作家就是一个老百姓,无论别人怎么吹捧,你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你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那别说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连“为老百姓写作”也不大可能。年轻人虚荣一点,把作家会员证放在火车的桌子上,吸引一些目光,这可以理解,但老了还这样,那就有点滑稽。我们老家的人对作家的认识比较正确,他们说:作家,就是记者吗?前几年我每次回去,村子里的人就对我说:你应该去当官,当了官,我们好跟着沾点光。我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比较低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的乡亲。
关于批判和反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做。但如果把这个当成旗号,扛出来吓人,就失去了意义。我在《四十一炮》后记里说自己一向以没有思想为荣,指得是在写小说时,还是要从人物从形象出发,不要在小说中说教,也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许多被思想者们弄得很虚玄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很朴素的老问题。思想者们总是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总是喜欢小题大做,总是喜欢大惊小怪。
我在农村长大,学到了最朴素最简捷的思想方法,这让我少了很多烦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写几篇小说,算不上知识分子。你比那些乡村中会讲故事的老人,无非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但有的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只能用低调写作,因为低调才是真正贴近生活的。
杨扬:我对您新作中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怀有兴趣。这是不同于您以往笔下的农村景观,见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北方非农化状态下的农村。包括老兰、罗通这样的农民,的确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形象。我注意到您对老兰这样的暴发户形象的把握,一改以往那种文学描写的模式:要么无情地贬抑,写其为富不仁;要么一味歌功颂德,写农民企业家的所谓新思路、创业精神。其实说老兰好也好,说他恶也好,都是奉着一种高调的批评旨意在写作。对于生活现实中的普通人而言,远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人物,很好地体现了您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低姿态、低声调的文学表达,而不是高调的社会批判。我想听听您对老兰以及对今天农村生活的看法。
莫言:写作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开篇之前,不得不考虑技术问题,但进入写作过程之后,技术问题就退到幕后,这时在作者头脑中活动着的,当然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着的场面。所以尽管我在后记中那样强调了所谓的技术,但读者要看的和看到的,大多还是故事、人物、场面、评论家的阅读,可能会更多地注意语言、结构等技术层面,但故事、人物、场面,依然会牵扯他,小说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故事。
老兰这种人,在我过去的小说中,尽管没有出现过,但我对他们,一直是很熟悉的。因为我的笔触一直没伸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乡村和由乡村发展成的城镇,所以这样的人物也就没有写到。老兰是亦正亦邪的人,这样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很难说他们好,也很难说他们不好。其实,不仅仅是在农村,在其他行业,这样的人也很多。因为本书是用罗小通的口吻诉说,作者深藏幕后,或者说,在这本书里,没有作者的思想。而罗小通的思想,罗小通对老兰的矛盾心态,正代表着民间的标准。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往肉里注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种肉会损害我的健康和利益,但从罗小通和老兰们的角度看,那就是注水有理。你如果不注,别人也要注。农民往肉里注水,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诸多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这跟出版行业中的盗版、制药行业中的假药、医疗行业里的红包、官员们的假数字和贪污腐化等是一样性质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痛苦。你看看,一谈到这些黑暗现象,我就义愤填膺,但如果我把这些激愤的情绪贯注到小说中去,这部小说就成了高调小说了。
我只能用低调写作,因为低调才是真正贴近生活的。
这本书如果让我自己概括主题,我想会有两个:一个是食,一个是色。
杨扬:情爱的冲动在作品中少了,有什么考虑吗?
莫言:情爱的冲动,在本书中,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本书如果让我自己概括主题,我想会有两个:一个是食,一个是色。罗小通吃肉,大和尚渔色。而且都是登峰造极。这里有我深藏着的反讽。五通神庙、肉神庙、肉食节、吃肉大赛、谢肉大游行,都有反讽的意思。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恋乳症。罗小通对肉的迷恋、大和尚对美色的迷恋,罗小通超人的食肉能力和大和尚超人的性能力,都不是写实的笔法,而是象征性的。我感觉到这些情节和描写都有超出了本事本物的意味,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也说不好。如果我想得太明白,那反而没有意味了。
叙事狂欢与价值迷失——评莫言的《四十一炮》
■李钧
对许多读者来说,莫言始终像一个谜团。他的思想活力和叙事变化使他的小说具有无限可能性:他身上民间“返魅”的原始冲动力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魔力,渗透到读者心底;他像一个“语言巫师”,骑着想象的扫帚,驰掠过汉语庙堂的古旧坟场与废墟,飞向民间的丰饶乡土,以“童年记忆”打造自己独有的“民间”叙事乐土,“由此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地的感官’,也由一个民间的歌手,变成了一个‘现代’的作家”。
莫言的《四十一炮》可以说是其“民间理论”的具体写作实践。笔者发现,《四十一炮》以其独特的“后现代”结构技法,叙述了当下中国的“现代性”故事,然而“狂欢化”背后却凝结着一片浓浓的古典乡愁,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表现出的张力,代表了莫言此时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
《四十一炮》以“癫狂”“诉说”和“复式结构”,在“魔幻现实主义”氛围营造中,创造出一种“狂欢化”、开放型的小说艺术形式。
作品采用莫言惯用的“儿童视角”。主人公罗小通是一个吹牛撒谎的“炮”孩。莫言让他承载起民间文化“无礼的游戏”、讽刺性模拟、俗俚妙语、发散性思维等“众声喧哗”的特质,使“诉说”在民间诙谐文化的沃土上生成了深刻的哲学认识论和人类文化学意义。正如《檀香刑》以“猫腔”为腔调,《四十一炮》中“炮孩子”的“诉说”成为全书主线: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解构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主体,使“言说者”成为“话语”工具,就连阅读主体也只能随着语流起伏前行。应当说,这是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但是“这个”罗小通的“说书人”角色与“听众”大和尚,又与中国传统“口口相传”的民间话本文学相通。于是,跨时空的错位对接,使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与民族性、传统性与(后)现代性的融通感。不管是有意运用还是无意实施,《四十一炮》的叙事手法在客观上实现了“古今中西”的结合。
莫言在后记中谈到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对他“讲故事”手法的启发。有人怀疑《四十一炮》有模仿《铁皮鼓》之嫌。其实比较两部作品就会发现,二者大异其趣:内容完全不同自不待言,人物塑造则“反其道而行之”:罗小通身体长大而精神滞留在童年;而奥斯卡·马策拉特却是一个身体拒绝长大而智商相当于普通人三倍的侏儒。我认为,君特·格拉斯对莫言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方面。君特·格拉斯“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莫言则力图通过一个孩子的“言说”找回童年,找回梦里故乡,找到他表达精神“乡愁”的方式。正如写在书封上的那段话:“看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虽然莫言惯于运用儿童口吻,讲述儿童视角里的社会人生,但“罗小通”这样一个“多旋律织体”的“杂语者”,在莫言作品中前所未有。在叙述过程中,罗小通创造了一个少年,他童年缺失的东西都在他的叙述中得到了满足,他用叙述挽留自己的少年,圆满自己的少年,实现自己的少年。
莫言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结构手法非自《四十一炮》开始。1984年莫言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只看了不到十万字,就“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创作了《红高粱家族》。而《檀香刑》开篇第一句“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爹的手里”,则毫无疑问来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语……莫言在小说形式上的“仿戏”恰恰说明他善于寻找突破口,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眼光,只有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这样的借鉴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