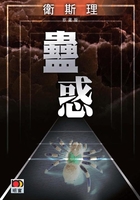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多老套的章目)
我在看信,信是由一個相當古怪的朋友寫來的——我自己人很正常,可是怪朋友之多,可以說天下第一。才和一個怪人胡明分手不久,又接到了齊白的信,大家還記得齊白嗎?他就是那個盜墓專家。
自從上次和齊白分手之後,他照例音訊全無,不過他這個人,有一個好處,隔上一年半載,只要他忽然想起你來,不論他在天涯海角,總會和你通一下音訊。
我現在在看的這封信,發自泰國北部的城市清邁,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城市,神秘而且動人。齊白的信文十分簡單,大意是:年來仍以掘墓為業,冀有所獲,乏善足陳,閣下若有可盜之墓,千萬勿秘而自享。
這傢伙,自己盜墓成癖,彷彿全世界人都和他一樣,會喜歡盜墓。
我看着信,想起了陳長青那屋子的地窖,那放置了那麼多靈柩之處,不知算不算是一座大墓?幸虧齊白不知道,要是他知道的話,那自然非得把所有的靈柩全都弄開來看看不可了。
我又想到,李規範他們,也算是神通廣大了,雖然說錢多好辦事,但是那麼多具靈柩,一下子就運走,運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什麼地方入土為安了,我曾打聽了一下,卻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出來,好像根本就沒有這件事發生過一樣。
他們那一伙人,過慣了隱秘的生活,行事作風,未免有點鬼氣森森,溫寶裕把良辰美景當成了“紅衣女鬼”,倒也不是偶然的事。
推測,那些棺木,多半是運回他們各自上代的家鄉去了,只怕也正因為事情發生在不為人在意的閉塞地區,所以才不為人知的。
我挪開了齊白的信,在信紙一揚之間,恰好迎向燈的燈光,在一剎那間,令得白紙在燈光的透視下,變成了半透明。
這本來是十分普通的一種現象,可是就在那一閃之間,我卻看到,潔白的信紙之中,有着一些暗影。
通常,考究的紙張中,會有“水印”,水印也必須向着光線才能看出來,也是用陰影的形式出現的。而這時在我手中的信紙,又不像是該有水印,而且,我想到齊白一生在古墓之中鑽進鑽出,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傢伙做起事來,也不免有點鬼頭鬼腦,大有可能是在信紙之中,藏了什麼信息,察看我是小心留意了,還是大意疏忽了過去。
要是我竟然疏忽了,沒有注意,那麼自然成為下次和他見面時的取笑資料了。
所以我心中一動,就着燈光,去看紙中的那些陰影,一看之下,認出那是自一到〇的阿拉伯數字,和自A到Z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數字用尋常小型計算機的位置排列,英文字母則照尋常英文打字機的排列位置。
數字和字母,是什麼意思,我沒有法子懂,因為根據那些數字和字母,幾乎可以排列出任何數碼和字句來。看了一會,我就放了下來,心知齊白用了這樣一張有水印的紙來寫信,一定有原因的,說不定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寫給我的,但是一時之間,既然猜不出原因何在,自然只好不去想它。
正在這時,我聽得樓下,老蔡正在大呼小叫:“小寶,你想死了,弄那麼多這種東西進來。”
老蔡年紀大了,的確特別喜歡大呼小叫,而溫寶裕也不好,經常有一些叫老人家看了幾乎把他當作是外星人的奇怪行為,所以一老一少,相處得並不是十分融洽。平時好在他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就算偶然見着了,也不免要小小衝突一番。
這時,聽得老蔡這樣叫嚷,我知道溫寶裕必然不服,定要還嘴,別看只有他們兩個人,要是吵將起來,我住所這小小空間,也和大戰場差不多,難得有什麼安靜可言。
我知道,那得等事態還沒有擴大之際,我非先出面“彈壓”不可。
所以,在還未曾聽到溫寶裕的聲音之前,我已經揚聲叫道:“小寶,你上來,我有話對你說。”
我的意思是,把他叫上來,把齊白的那封信給他看,叫他猜猜齊白在信紙上,有着什麼啞謎,讓他有一點事情做做,他就半天可安靜了。
溫寶裕的反應,出乎意料地順從,只聽得他大聲答應着,接着,便是他上樓梯的聲音,他竟然並沒有對老蔡的呼喝抗辯什麼,真是不容易,我正想稱讚他幾句,已看到他背向着門,閃身進來,手中捧着一隻相當大的盤子。
他用這樣的怪姿勢走進來,自然是為了保護手中的盤子,他一進門,就轉過身來,我先看到他賊忒嘻嘻的笑容,接着,就看到了他捧着的那只大盤子中所放着的東西。
我也不禁陡地挺了挺身子,而且立即明白,老蔡的大聲呼喝,實在十分有理。
在那只直徑約有五十公分,本來不知是作何用途的漆盤之上,全是大大小小,蠕蠕而動,有的縮成一團,有的拉長了身體,有的通身碧綠,有的黃黑相間,有的茸毛絢麗,有的花斑奇特,至少有上百條,各種各樣的毛蟲。有的還糾纏成一團,有的則在盤子邊緣昂首,想要離開盤子的範圍。
雖然說在他們的身上,有着自然界美麗顏色的一半以上,可是由於形態實在醜惡,而且一看到了之後,就使人想到,這些毛蟲,多半會放出毒素,令人的皮膚,起異樣的敏感,變成又紅又腫,又痛又癢,所以更在心理上造成極度的不舒服。
我吸了一口氣:“小寶,你這是幹什麼?”
溫寶裕本來是笑嘻嘻的,多半還以為我見他捧了一盤毛蟲進來,還會讚他幾句哩,一看到我面色不善,這小子倒也知機,眨了眨眼:“這——全是胡說要我捉的,他是昆蟲專家,捉了來,好研究它們的生態。”
他說的話,聽來大是有理,要是我是閉着眼睛聽他說的,也就相信了。可是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正盯着他,他一面說,一面眼珠亂轉,又不敢正面看我。孔老夫子的話,有時很有道理,他說人心術不正,則眸子不正,叫人可以觀人於眸。所以,我一下子就知道這小子是在說謊。
我悶哼了一聲:“是麼?是胡說叫你捉的?”然後,我陡地提高了聲音,大喝:“我看這全是你在胡說。”
溫寶裕正以為他的謊言可以將我瞞騙,忽然給我大喝一聲揭穿,那令他陡然嚇了一大跳,雙手一震,盤子向上揚了一揚,盤子中的毛蟲,倒有一半,揚跌了出來,至少有二三十條,沒頭沒腦,落在他的身上。
這下子,輪到他怪叫了起來,雙手亂舞,鼻子上掛着一條身子一躬一躬、努力想向他額頭上爬去的毛蟲,怪聲諠譁,那種狼狽樣子,逗得我哈哈大笑。
他放下盤子,大叫着:“別動,一動會踩死它們,我好不容易才抓了那麼多來的。”
一面叫,一面手忙腳亂。我笑了一會,看他的樣子實在可憐,也幫着他,捉了幾條毛蟲進盤子去,等到所有的毛蟲,看來都捉進盤子去了時,他忽然怪模怪樣,縮着脖子,愁眉苦臉望着我:“會不會有幾條,從我衣領裡鑽了進去。”
我笑道:“大有可能。”
他忙拉出衫腳來,跳着,蹦着,又亂了好一陣子,肯定沒有毛蟲在他背上爬行了,才鬆了一口氣,定了下來。我望着那些令人看了絕無快感的毛蟲,皺着眉:“你捉了這些東西來,究竟有什麼用?”
溫寶裕的神情,得意忘形:“連你看到了也會感到害怕,她們一定更害怕。”
我怔了怔:“她們?她們是誰?”
溫寶裕像是一下子說漏了嘴,俊臉自然而然漲得通紅,眼睛不斷眨着。我看了這種情形,不禁大奇,盯着他看了半晌,他才恢復了正常,裝成若無其事:“到學校去嚇同學,不過真的,胡說鼓勵我捉毛蟲,他說,毛蟲的種類,各有不同,每一種毛蟲,將來會變什麼成蟲,是一定的;雖然他們在變成是蛹的時候,躲在繭裡,看起來個個差不多,可是,到了變成蟲的時候,就千奇百怪,再也不會相同。”
他顯然是為了要掩飾他的窘態,所以才一口氣地說着,我自然知道他的目的。
可是,我想想,他要用毛蟲去嚇唬同學,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值得深究,所以也沒有再問下去。
溫寶裕找到了一隻紙盒,又把毛蟲搬了一次家,逐條捉進紙盒中去,我看他十分起勁,就道:“這裡至少有二十種不同的毛蟲,每一種毛蟲,通常只吃固定的一種植物的葉子,你怎知道哪一種毛蟲吃什麼葉子,怎能養得活牠們?別說看牠們變成蟲了。”
溫寶裕道:“胡說是專家,他會告訴我的。”
說了之後,他又道:“毛蟲可以說是最簡單低級的生物了,居然在食物方面,也有那麼固執的選擇,若是沒有他要吃的樹葉,他決不會去吃別的樹葉。算起來,所有樹葉的成分都不會差太多,是什麼告訴他們要選擇特定的樹葉的呢?”
我笑道:“這問題問得有點意思了,那是遺傳因子決定的,遺傳因子中有密碼,只要是這一種毛蟲,就必然照着那一組密碼生活,沒有一條會逸出規範,胡說是生物學家,他應該可以給你更專門的回答。”
溫寶裕笑了笑:“大自然的奧秘真多。”
他捧起了紙盒,看來準備告辭,那時,電話鈴響起,我拿起來一聽,聽到一個氣急敗壞的聲音:“小寶在不在?對不起,衛先生,請他聽聽電話。”
我聽出是胡說的聲音,而且顯而易見,他有非常緊急的事要找溫寶裕。胡說和溫寶裕一起在研究陳長青的那幢房子的過程之中成了好朋友,幾乎天天在一起,還找得他那麼急幹什麼?
我順手把電話遞給了溫寶裕,溫寶裕對於有人打電話到我這裡來找他,表示訝異,連聲向我道歉,並且保證,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
我聽得聽筒中,傳來胡說的大叫聲:“快聽電話,慢慢道歉。”
胡說為人斯文,性格淡定,不是性急暴躁的人,可是這時卻又心急得驚人。溫寶裕大叫一聲:“來了。”
他把聽筒湊到耳際,才聽了兩句,就臉上變色,失聲道:“不會是她們吧,如果是,那太過分了。”
接着,他又皺着眉,電話聽筒中傳來一陣急促的語聲,我自然聽不真切,只聽到一陣“嗡嗡”聲,溫寶裕更是有點臉青唇白,頻頻道:“這太過分了,太過分了,這——她們太過分了。”
接下來,又是一陣子“嗡嗡”聲——胡說急速地說着話,溫寶裕道:“你先別急,別叫她們在暗中看了笑話,我立刻就來。”
他說着,放下了電話,神情顯得十分嚴重。
我卻一點也沒有在意,我知道,在胡說和溫寶裕之間,可能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但那也一定是青年人之間的事,兒童、少年、青年,各有他們以為十分緊張,彷彿世界末日就要到來的緊張事,但這一類事,在成年人看來,卻不值一哂。
所以,胡說和溫寶裕緊張他們的,我一點也不去關心他們,溫寶裕放下了電話,向我一揮手,向外便衝,我大叫一聲:“喂,你的毛蟲。”
他已經打開了門,跳上了樓梯的扶手,直向下滑了下去(老蔡曾發狠要在那上面釘上幾枚釘子,不讓溫寶裕滑下去),一面叫道:“暫且寄放一陣,我有急事。”
我還想說我才不會去將各種不同的樹葉餵他們,餓死了不關我事。可是一想,和這種少年人多費唇舌則甚,也就懶得出聲了。
當日黃昏時分,白素回來,我想起那一盒毛蟲,又想到女性對這種昆蟲,大都有一種先天性的厭惡,白素雖然是出類拔萃的女性,但要是不小心揭開了那紙盒,觀感也不一定會愉快。
所以,我叮囑了一句:“書房有一隻紙盒,別去打開它”
白素用疑惑的眼光向我望來,我笑道:“是小寶留下來的一盒毛蟲!”
白素作了一個怪臉:“毛蟲!小寶要來幹什麼?”
我笑了起來:“他說要來嚇人。”
白素不以為然地搖着頭:“他也不小了,應該到了送玫瑰花給女孩子的年齡了,怎麼還無聊地用毛毛蟲嚇女孩子?”
我順口道:“你怎麼肯定他是嚇女孩子的?”
白素瞪了我一眼:“動動腦筋就知道了,男孩子自己敢去捉毛蟲,怎會給毛蟲嚇着了?”
我不禁失笑:“真是,不知道什麼人家的女孩子倒了霉,惹上了溫寶裕這個小煞星。”
白素笑得柔和:“少年男女在打打罵罵聲中,另有難以形容的甜蜜和樂趣!嗯,今晚上的音樂會——”
我忙道:“我們當然一起去!”
晚上,有三位音樂家自北歐來,是室樂演奏的高手,在白素的一位朋友的家中,有一個規模不大的聚會,參加者大約五十到六十人,音樂家會演奏A小調鋼琴三重奏:柴可夫斯基的“紀念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白素是古典音樂的愛好者,我無可無不可,本來想推掉不去,看來現在是非去不可的了。
白素一面走向樓上,一面道:“看今天的報紙沒有?胡說很出風頭。”
我笑了起來:“還是那幾個木乃伊的事?”
白素答應着,逕自上樓去了。我拿過報紙來,早幾天,報上就有消息說,本地的博物館,借了十具木乃伊來展覽,供市民參觀。本地博物館主其事者是胡說——自然是通過了他堂叔在埃及考古界的地位而達成這件事的。
記者還說,由於本地博物館,從來未曾有過木乃伊展出過,所以一定會引起轟動云云。
在今天的報紙上,我又看到了木乃伊運到,胡說在主持裝載木乃伊的箱子搬進博物館時的情形,樣子挺神氣,照片上可以看到,溫寶裕也擠在人堆中湊熱鬧。
而且,博物館的通知也登在報上,正式展出的日期是兩天之後。
我放下報紙,自然而然想起下午溫寶裕在我這裡時,胡說那個氣急敗壞的電話來。心想十具木乃伊一到,寫說明,安排展出,夠他忙的了,還有什麼事,會要來找小寶商量,而且還那麼緊張?
照說,他工作上忙成那樣,是沒有什麼時間再另外出什麼花樣的了。可是,他和小寶在一起,誰知道又會玩出什麼新鮮花樣來。
我只是想了想,並沒有再去注意。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那樣,不去注意的,實際上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而本來認為是一個相當平淡的音樂聚會,卻有意想不到的遭遇。
進行音樂聚會的是一幢大洋房,主人雅愛音樂,有小型的演奏廳,我和白素到達的時候,客人已到了一大半,大都圍着三位演奏家在談天,我聽了一會,拿着酒杯走開去,沒有目的地走着,看着屋子的佈置。
屋主人毫無疑問是音樂迷,在他屋中所有的陳設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在寬大的走廊上,全懸掛着音樂家的畫像,我信步走着,在一幅李斯特的全身像前,停了下來。李斯特是一個充滿了傳奇性的音樂家,他一生的事跡,被拍成不少次電影,畫像中的音樂家,挺拔超群,氣宇不凡。
我正在欣賞着的時候,感到有人來到了我的身邊站下,維持着禮貌上應該維持的距離,我轉頭看了一看,是一個樣貌相當普通,可是雙目卻神光燦然,一望而知十分有內涵的西方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頭髮有點不注意的凌亂,是一個陌生人。
在這種場合下,主人交遊廣,賓客之間互相不認識,是十分尋常的事,我看他手中也拿着一杯酒,就向他微笑了一下,略舉了舉杯,他也報以微笑,然後開口,居然是一口標準的中國國語:“可惜攝影術發明得太遲了,以致歷史上許多著名的人物,都沒有相片留下來,留下的只是他們的畫像。”
我隨口應道:“是啊,寫實主義的油畫,算是肖像畫中能保留人的真面目的了,中國畫就沒有這個優點,歷代偉人是什麼樣子的,大都各憑想像。”
他也笑了一下:“也有連想像都沒有法子想像的。”
我“嗯”地一聲:“那大多數是年代久遠的人,軒轅黃帝,誰能想像他是什麼樣子的?蚩尤,也不知道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他轉動着手中的酒杯,眼睛也望着酒杯:“相當近代的人物,也有無法想像樣子的,太平天國,不算是很久的事情吧,可是那些領導人物是什麼樣子的,就無從想像起。”
本來,在這樣的情形下,遇到陌生人,最多只是閒談幾句就算,然後各奔東西,誰還會記得什麼時候說過什麼話。所以我一聽得他這樣說,雖然覺得他提出了太平天國和人像的問題來,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為什麼值得研究,下面的談話中會說明),我也不打算多說下去,只是隨口“嗯”了一聲。他卻在這時,抬起眼來,直視着我。
他眼中的神色有點殷切,也有點挑戰的性質:“我有一個問題,常想有機會問問中國朋友——”
我不等他說完,就作了一個手勢:“和中國有關的問題,並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而且也不必要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的一切。
他連聲道:“是,是。”
這洋人,顯然是“中國通”,對中國人的滑頭脾氣,也學得相當到家,一面“是是”地答應着,一面又突然來一個轉折,以“可是”為開始:“可是,衛先生,你不是尋常的中國人啊!而且,有一些相當神秘的事情,你總有點獨特的解釋的。”
好傢伙,這人不但早就認識我,有備而來,而且一上來就給我幾頂高帽子,想用高帽子罩住我,我當然不會那麼容易上他的當,微笑着:“你說得太客氣了,閣下是——”
他忙伸手入袋,取出了一張名片來,遞了給我,我接過來一看,上面印的是漢字:班登。旁邊還有一行小字,註明他是一家大學的東方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
在我看他名片的時候,他有點油腔滑調:“和班家套套近乎,班固班昭班勇班超,實在太出名了。”
我心中好笑,心想這倒好,歷史上的幾個有名的姓班的人,全叫他數出來了,洋人取中國名字,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倒是他先知道了我是誰,再用陌生人偶然相遇的方式來和我交談,這種鬼頭鬼腦的過程,我不是很喜歡,所以應對之間,也比較冷淡了一些:“東方歷史的內容太廣泛了,閣下的研究專題是——”
他忙道:“太平天國,我一直在研究太平天國。”
我點了點頭:“這是中國近代史中很值得研究的一段,也十分驚心動魄,中國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也很多,畢竟時間並不太久遠,資料也容易取得。”
班登一面雖然不住點着頭,可是卻一副並不同意,還有很多話要說的樣子。我已經準備結束和他的談話,準備離去了,他卻突然問:“衛先生,太平天國時期,喜歡在牆上繪畫——”
我答:“是啊,太平天國的壁畫,十分有特色。”
班登卻道:“最大的特色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壁畫之中,全然沒有人物。”
我怔了一怔,是的,我有一個時期,對太平天國這樁歷史事件也相當有興趣,曾看過不少有關資料,主要是由於有一件事,當事人的上代,是當過“長毛”(太平軍)的,那件事牽涉到了太平軍大潰敗時的一批寶藏,和一個被長期禁錮在一塊木炭中的靈魂,詭異莫測。
(整件事,記述在題為“木炭”的這個故事中。)
在那時,我已留意到很多記載上,都提及太平天國的壁畫中沒有人物,甚至在應該有人物的情形下,也全然不繪人物。
但我一直未曾將之當作那是什麼特別的問題。班登對太平天國的一切,顯然有相當程度的研究,所以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
我略想了一想:“是,不但是壁畫,太平天國好像自上到下,特別不喜歡人物畫,所有的領袖,沒有一個有肖像畫留下來的?”
我在最後一句話中用了詢問的語意,是由於我未能肯定是否如此之故。
班登卻肯定道:“是的,衛先生,我想知道為什麼?是不是有特別神秘的成分在內?”
這個問題,自然是不好回答之極,我“嗯”了一聲,想不出該如何回答才好,班登又道:“是不是那些人都有見不得人之處,還是由於別的什麼原因,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有真面目留下來了?”
我仍然無法回答,只好道:“或許沒有什麼神秘,只不過是他們的習慣?”
班登忽然變得十分急切,甚至揮舞着雙手,講話也急促起來:“不,不,一定有極其神秘的原因的。真可惜,不多久,攝影術就發明了,要是早幾年,太平天國那些人的樣子,一定可以留下一些來的。”
我覺得他的態度十分可笑:“你想知道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那些人的樣子,有什麼用呢?”
他瞪大了眼望着我,一副失望的神情,還有一點很不滿意的神氣在內,看來他沒有在言語上對我不滿,已經是十分客氣的了,他道:“知道他們是什麼樣貌的,自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是他們為什麼不讓他們的樣貌有任何留下來的可能,卻十分值得研究。”
他仍然望着我,想知道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覺得他根本是在鑽牛角尖,很多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抓住一點小問題,小題大做,可以寫出洋洋灑灑的論文來。
所以,我只是十分冷淡地道:“是麼?照我看——”
我正找不出該和他說些什麼話時,有人在叫:“演奏開始了,請各位到演奏廳去。”
這一下叫喚,正好為我解了圍,我向班登作了一個手勢,就不再理他,自顧自走了開去。
當我離開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神情很失望,而且一副還想和我說話的樣子,可能是由於他看出了我的冷淡,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所以沒有出聲,而我根本不想和他說下去,所以趁機就和他分開了。
演奏會自然精采絕倫,在四十五分鐘左右,當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演奏完了之後,在熱烈的掌聲之中,音樂家又奏了幾段小品,才告結束,賓客陸續離去,主人走過來向我打招呼。
我和主人不是太熟,只知道他是一位銀行家而已,寒暄幾句之際,他看來是順口道:“班登醫生是一個怪人,你們談得很投機,講了些什麼?”
我陡然一怔,反問:“班登醫生?還是班登博士?”
主人是用英文在交談的,“醫生”和“博士”是同一個字,自然難以分得清。
而班登如果是一個歷史學家的話,他有博士的頭銜,自然十分尋常,如果他同時又是一位醫生,那就非常之特出了。
主人道:“他是醫生,是——”
他只講了一半,忽然陡地住口,神情十分不好意思:“他——十分古怪,早十年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十分出色的醫生,後來忽然把醫生的頭銜棄而不顧,真是怪人。”
我又怔了一怔,在我的經驗之中,還未曾知道過有什麼人把醫生的頭銜拋棄掉的。如果一個人為了研究中國近代史,而把醫生的頭銜扔掉,雖然談不上什麼可惜不可惜,總是一件相當怪異的行為。
看來,班登這個人真不簡單,我應該和他多講一會的。一想到這一點,我就四面張望着,主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意:“他早就離開了,甚至沒有聽演奏,真可惜。他是聽說你會在今晚出現,所以特地來的。”
我“啊”地一聲低呼,一時之間,頗有失落之感。想起我急於擺脫他;不顧和他交談時他的那種失望的神情,心中很不是味道。
原來他是專門找機會來和我見面的。
他要和我見面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就是為了討論太平天國那些頭子為什麼連畫像都沒有留下來?我又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專家,這種冷僻的問題,和我討論,會有什麼結果呢?
當時,我的思緒相當紊亂。人的思緒相當奇怪,有時在對一些主要的事,惘然而沒有頭緒之際,反倒會想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枝節問題來。
我那時的情形,就是這樣,忽然想起了班登的年齡問題來,他看起來,只不過三十歲左右,而主人卻說他十年之前,已經是醫生了。一個人可以在二十左右成為出類拔萃的藝術家、運動家等等,但醫生是要受長時期的嚴格訓練的,沒聽說什麼人憑天才可以成為醫生的。
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在二十歲左右就當了醫生,那是十分罕有的事。
我一想到,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沒想到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令得主人神色尷尬,忸怩了一會,才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輕了許多,你知道,醫生——他們總有辦法把自己弄得看來年輕一些的,他們管的就是人的身體。”
這算是什麼回答,我自然不會滿意。可是當我還想追問時,有好幾個人過來和主人打招呼,主人也像是要避開我一樣,向我抱歉地笑着,轉過去和別人應酬去了。
這時,白素也來到了我的身邊,她看出我有點心神不屬的樣子,就用眼色向我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我無可奈何地笑了一下:“遇到一個怪人,日後只怕要麻煩你去打探一下他的來歷。”
白素有點愕然:“我認識這個怪人?”
我笑了起來,指着主人:“主人認識,而我覺得他不是很肯說,要你出馬才行。”
白素當下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在回家途中,我把和班登晤面的經過,向白素說了一遍,她也覺得十分訝異:“由醫生改作去研究歷史的例子太少了。”
我道:“是啊,而且研究的課題還十分冷僻:太平天國的壁畫中,為什麼沒有人像,哼。”
白素想了一會,也認為有點難以想像:“如果今晚的主人,對班登的來歷知道的話,我一定可以探聽出來的,明晚還有同樣的演奏,我會早一點來,和主人談談。”
我忙道:“演奏的確十分精采,可是我——”
白素不等我說完,也明白了我的意思:“明晚准你免役吧,你這種俗人,難得聽一次好音樂,就像是受罪。”
我笑了起來:“反正是俗人,聽多幾次音樂也雅不起來,樂得做點自己更有興趣的事。”
白素不置可否,到家之後,我有點急不及待,去翻閱太平天國的史料,有一些專門講述那時期壁畫的資料,提到太平軍不論佔領了什麼巨廈大宅之後,都喜歡在牆上留下大量的壁畫,可是所有的壁畫上,都沒有人物,並且有明文規定,畫畫的時候,不能畫人像上去,至於為什麼,史料卻沒有解釋。
這本來是歷史上鮮為人知,也很少有人注意的一個小問題,但是一提起來,從神秘的角度來設想,也就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想像了。
這時,我倒真希望班登能突然出現,我好聽聽他的意見、因為他既然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雖然沒有結果,至少有了一定的設想了,聽聽他的設想,也是好的。
可是在看着史料,時間溜過去時,沒有等到班登,倒等來了胡說和溫寶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