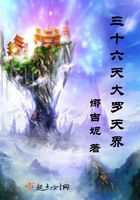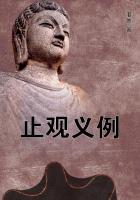男孩挽着裤腿,没穿鞋,桶里的水荡出来,弄湿了他的脚,路面上便拓下了一串脚印。这是一条青石板路,无数的日子和鞋底将它打磨得又光滑又细腻,干爽的路面是铁灰色的,湿湿的脚印拓在上面,颜色深了一块,像游弋在他身后的一串鱼。
一大早,我就被一个声音吵醒了。
支起耳朵一听,听见身子底下有哗哗的流水声。怎么会有水声?是睡在船上吗?睡意随着流水声渐渐淡去。我想起来了,是睡在卧房里,而卧房是悬在水面上的,靠水的那一边用几根粗粗的木头柱子撑着,让人觉得像是一排巨人背着房子站在水里。这就是吊脚楼。
这条老街叫北边街,一溜都是这样的吊脚楼。吊脚楼一面濒河,一面临街,褐木黑瓦,灵巧古朴,远远看去,像是童话里的景致。
昨天一到这里,就好新奇这里的房子。
首先是那两扇腰门——在高大的双开的木门前面有两个小小的门扇,比我高出许多,须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将下巴搁在门框上。而腰门的高度正好是大门的一半,是因为这个就叫它“腰门”?
但一开始,我自以为是地听成了“妖门”,说了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好好一件事就会想歪去,不得要领。只是我想不明白,怎么会叫“妖门”,是妖精进出的门?这里会有妖精?要是真有,我倒觉得来这里寄养是来对了,有妖精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听过彼得·潘的故事,那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可爱的小妖精。
后来我常倚在门边等候妖精。我特别留意黄昏这段时间——据说,这是妖精出没的时段。
有一回,我等来了一只白猫,它“喵”的一声从虚掩的“妖门”挤进来,它有着纯然一色的白毛和湛蓝的夜空一样的眼睛,它站在门边歪着头望着我,那神情自负而又娇憨,而它的眼睛在沉暗的天光中闪着诡秘的光。我正要过去抱它,但它闪烁的眼光让我突然警醒起来:它会不会是妖精变的?
立马,跟踪追进来了一个男孩,把它抱走了。
还有一次,也是黄昏的时候,有一片白色的羽毛从“妖门”飘了进来,落在地上。我捡起来,那羽毛十分柔软,我只轻轻地哈了口气它就好像要飘浮开去。凭我已有的经验,我不能断定它是鸡、或是鸭、或是鹅、或是别的什么动物的羽毛。突然,我又想到了妖精,是妖精的羽毛?妖精是可以千变万化的,那么,这回她又变成了什么呢?肯定是一种会飞的东西,羽毛都飘进来了,说明她就在附近。
一时间,我兴奋得浑身战栗起来。我趴在“妖门”上,恐惧而又欢欣地期待着。
我自然是白等了。
推门进去就是厅堂,厅堂是结结实实地建在地面上的,往里走才是木地板的卧房,人走在上面嗵嗵地响,下面是空的,并有细细柔柔的流水声传来。我走到木格窗前张望,可我太矮了,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从后面环过来一双手,把我抱了起来,还有一个流水一般柔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看看,下面是条河。”
下面果真是一条河,河水清幽幽的,对岸是一排排的麻条石的台阶,一直铺到水里,有好些人蹲在那里洗衣洗菜。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那“桥”很特别,是一个个的石墩连成的,石墩的间隔大约是大人迈一步的距离,我想我是绝对跨不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桥”叫跳岩。
我回过头,看到了一张清秀和善的脸,眼角虽布满了细细密密的皱纹,但微微凹陷的眼睛却闪着煦暖温婉的光,头发一丝不苟地拢在后面,挽了一个圆圆的髻,鬓角有几缕银丝在闪烁。她从后面环住我,轻轻地揽我入怀,她的怀里异常的柔软,我像是靠在一垛棉花包上面,而且,我还闻到了一丝丝类似蒸肉包子的暖暖的香味。
妈妈抱的我动作常常很猛。奶奶带我的时候,妈妈每次离开和见到我都要狠狠地抱我一下,用力地把我往怀里按,好像要把我塞进她的身体里去一样。妈妈瘦,她的肋骨硌得我不大舒服,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汗味。
想起刚刚进门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这是云婆婆。当时我只是瞪着一双眼睛傻傻地看着她,我不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可这会儿,也许是她这轻轻一抱,就突然让我对她没了隔膜,有一种令我自己都惶惶不安的想亲近她的感觉。我居然很乖巧地叫了一声:“云婆婆。”
这一声恰巧被走进来的妈妈听见了。我这样甜甜地主动叫人是十分罕见的,妈妈大大地吃了一惊,随即十分宽慰地笑了,说:“这孩子有点怪,却和你这么有缘,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安顿好了我,妈妈就走了。
云婆婆拉着我的手送妈妈。只送到门口妈妈就不让送了,把我们往屋里推,说:“别送了,我看着难受。”说完背过脸去。
云婆婆扶着我站在小凳子上,我就正好将两只手臂搁在腰门——那时还以为是“妖门”——的上框。我朝妈妈挥着手,可她并没有回头看我。妈妈急匆匆走得好快,好像是怕我追上去,缠住不让她走。
看着妈妈越走越远,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难受起来,正想追过去,“水哎——”我听见一个人在喊。
扭头一看,是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挑着一担水边走边喊。
男孩挽着裤腿,没穿鞋,桶里的水荡出来,弄湿了他的脚,路面上便拓下了一串脚印。这是一条青石板路,无数的日子和鞋底将它打磨得又光滑又细腻,干爽的路面是铁灰色的,湿湿的脚印拓在上面,颜色深了一块,像游弋在他身后的一串鱼。
“水哎——”男孩走过来了,朝着我们喊。
“水,过来。”云婆婆招呼他,并打开了腰门。
他点点头,快乐地、无声地一笑,挑着水欢欢地快步走了过来。进屋,然后把水倒进一口大缸里。云婆婆给了他几分钱。
云婆婆告诉我,这个男孩是以卖水为生的,他和他的麻脸奶奶住在这条老街的西头。麻脸奶奶是个孤老太婆,一脸麻子,很丑。麻脸奶奶不是他的亲奶奶,他其实是被捡来的,麻脸奶奶把他养大。五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麻脸奶奶倾其所有为他治病。麻脸奶奶的“所有”很少,是她平时卖水攒下的一点点钱。命总算是保住了,但病好后他就不会说话了。
麻脸奶奶年纪大了,挑不动水了,男孩就接过了麻脸奶奶的扁担,卖水养活麻脸奶奶。前两年麻脸奶奶中风偏瘫了,他还得伺候麻脸奶奶。
男孩不会说话,却能非常清晰地喊出一个字:“水。”
所以,大家就叫他水。
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早上把我吵醒的是水的吆喝声,而不是楼板底下的流水声。流水声细细碎碎的,蚕丝一般绵绵不绝,正好是可以枕它入梦的。
“水哎——”一声声飘过来,由远而近,我惊醒了。看见一缕阳光从木格窗子的缝隙间挤进来,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跳到裸露着木纹的地板上。
我坐起来,旁边已经没有了云婆婆。云婆婆每天总是起得很早。我赤脚跳下床,跑到窗边,推开窗子,哗地一下,一大堆的阳光和着清凉的晨风迎面扑来。我搬来一张矮凳子,站上去。河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雾气。跳岩那边的雾要浓一些,模糊了石墩和人的脚,从这边看过去,过河的人像是在水面上飘,怪异又有趣。
“水哎——”水过来了。
我赶紧跑到厅堂,云婆婆不在家,可能去买菜了。大门开着,可腰门却插上了——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只要不是出远门,都只把“妖门”插上,只要小妖精不溜进来就是了——那时我总这样想。可这会儿我很想出去,又拔不出闩子——云婆婆用绳子绕住了闩子,我解不开。她不准我出去时就这样。我急得大叫起来:“水,水,过来帮我开开门!”
水的头从腰门上探了进来,很轻松地帮我解开了绳子,打开了腰门。然后,把水挑了进来,倒在水缸里。
他边倒我边在一旁嚷:“可是,我不知道云婆婆要不要买你的水,她现在不在家,我又没有钱给你。”可水不听我的,倒完水后就往外面走。
没走几步,我叫住了他:“水,你帮我把‘妖门’闩上,我跟你去玩好不好?”
水停住,看了我一眼,继续往前走。
“水!水!”我跺着脚尖声尖气地叫。
水终于走过来,把腰门闩好,然后扭头冲我咧嘴一笑,笑容像雨后的阳光一般纯净,并伸手在我的额头上弹了一下。我的额头有点奔,很方便别人弹,弹起来音响效果也不错。不过,水弹得很轻,一点也不痛。我看出来了,水喜欢我,而我也很无拘无束地一下子就接受了水。
我的自闭在带着一个新的名字来到这片别样的土地和别样的人们中间时,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云婆婆话不多,温和又安静;水干脆不会说话,但他是快乐的,无忧无虑,有着十分纯净的笑容,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亲近和心安。
我赶上去,乖巧地拽住了水的手。水的手很粗,有很厚的趼,是从井里打水拉吊绳磨出来的。
我跟着水来到井边。我是第一次看到井。
井口不大,井沿是用麻条石砌成的,上面有一道道的痕迹。看到别人打水我才明白,那些痕迹是让提水的麻绳勒出来的。我暗暗惊诧于绳子的力量,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趴在井沿上。井不太深,我看见离我并不是太遥远的地方又有一块小小的、圆圆的天,还有一张扎着小辫的胖乎乎的女孩的脸,可是,那女孩的头上怎么会长出两只角来呢?惊恐地回过头来,见水站在我身后,无声地坏笑着。再看井里,女孩头上的角没了。
知道是水捣的鬼,可一时还弄不明白水是怎么做的。我有时笨笨的。
我喜欢看他打水,把吊桶放下去,接近水面时,手轻轻一抖,吊桶就一个猛子不动声色地扎了进去,一拎,就是满满的一桶水。
打好了一担水,我就跟在水后面去卖。
“水哎——”这回是我叫的。我的声音水珠一般清亮,听上去又像羽毛一样的轻盈,可以在清晨寂静的老街悠悠地飘来飘去。
水回过头来,我得意地朝他笑笑,水又在我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可没叫几声,就让云婆婆听见了。我以为云婆婆会说我不该一个人跑出来玩,可云婆婆却说:“我看见了,沙吉买水了,还会卖水呢。”说完,就给了水钱。
云婆婆给我买了桐油粑。
桐油粑是用桐油叶包的,打开来就闻到一股桐油的清香。桐油粑是糯米做的,中间有腌菜和腊肉做的馅,油汪汪的,又香又糯。我把头埋在宽大的桐油叶里,吃得抬不起头来,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不过吃到最后一个时,我忍了忍,不再吃,把它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给了水。
以后,云婆婆早起买菜时,就在水缸边放几分钱,听到“水哎——”的声音,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出去叫水。水替我打开腰门,把水担进来,然后我就跟着他出去玩。
我每次都要趴在井沿上看,看什么呢?里面除了一个圆脸的小女孩,也没什么好看的。当然还有绣着白云的天,那云沉在水里,好像一块块泡涨了的馒头。一只鸟从空中飞过,影子印在井里,鱼一般游过——我一惊,真有鱼来吃馒头了吗?
我将身子往里探了探,没想脚下一滑,就直直地朝井里栽去。
水正在井沿边拎水,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伸手猛地一捞,就一把抓住了我的后襟。我的半个身子差不多都栽进去了,两条腿像被捉住的蚂蚱一样,惊慌地蹬着。还好他天天提水,手臂劲很大,一使劲,就把我拽了上来。
两人站稳后,都呆了,四只眼睛互相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想清楚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和接下去有可能发生什么后,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好像要发泄什么,哇啦哇啦哭得惊天动地。我这样惊天动地哭的时候,觉得不那么害怕了。
我哭了一阵后觉得奇怪,水呢?他怎么让我一个人哭,也不来哄我?我扭头一看,吓了一跳: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井——原来水比我怕得更厉害,他一定是非常后怕,我若真掉下去了怎么办?
水这副样子让我立即停止了哭泣,我抹了把泪过去抱住他的手臂,说:“水,没事了,我不哭了,你别害怕。”
可水还是不停地发抖,眼睛像一只受惊的松鼠,在我和井之间惶恐不安地跳来跳去。
我摸了一把额头,额头上是细细密密的一层冷汗,凉凉的。我把凉凉的额头冲着水扬起,说:“弹呀,水,弹我一下你就好了。”
水已经好了一点,没在抖了,脸色也不像刚才那么难看,可还是木木地站着不动。
我就自己弹起来,将中指弯曲抵住大拇指,绷住,像一张弓,然后使劲一弹,咚!脆脆的一声响,好痛!
可水依然无动于衷。任我把自己的脑门当西瓜一样弹得咚咚响。直到我弹到第五下的时候,他才抓住我的手,不让我再弹。
我说:“那你弹我一下。”
水抓住我的手举起来,在空中停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捶打自己的头,也捶得咚咚闷响。水捶了好几下后,我才猛醒过来,大叫:“不要,不要!停下,水!放开我!”
可是水把我抓得好紧,我根本抽不出自己的手,水抓住我的手把自己捶得一下比一下重。我急了,然后急中生智,用另一只手啪啪地打自己的脸。
水没料到我会这样,瞪着我,愣住了。
两人傻傻地对望着,我咧嘴一笑,水也想笑,可他只难看地咧了咧嘴,没笑出来。最后他抬手在我火辣辣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可我觉得水只是用手指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