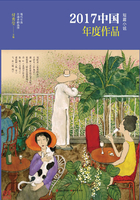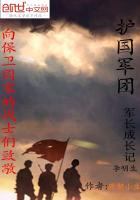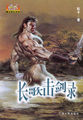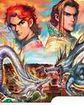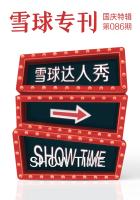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想论
一个人仅仅成为人,是不够的,他或她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仅仅是作品是不够的,文学作品必须有灵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某些艺术作品,虽然从鉴赏力的角度看,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却没有灵魂。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幽雅,但却没有灵魂。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之能事,但却没有灵魂。一些谈吐可以不乏风趣而又娓娓动听,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以说长得漂亮、温雅而又优美动人,但却没有灵魂。”([德]康德:《判断力批判》,见《西方文论选》上卷,56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那么什么是文学的灵魂呢?文学的理想,或者说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文学的灵魂。有灵魂必然有理想,无灵魂必然无理想。
一、西方文学理想论的成功与缺憾在文学理想问题上,西方文论有得也有失。“得”的是西方文论概括出“典型”作为写实型文学的理想,给西方写实型文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失”的是西方文学虽然也有抒情型文学和象征型文学,但是没有像中国古代以“意境”来概括抒情型文学的审美理想,以“意象”来概括象征型文学的理想。我们只能说,在三维的文学理想结构中,他们抓住了一维,其他两维则有待东方文论特别是中国文论给予补充。
那么,文学的理想是什么呢?在西方,认为文学的理想就是“典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德]黑格尔:《美学》,见《西方文论选》下卷,29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认为典型(他直接称为理想)是“艺术美的理念或理想”,把文学理论等同于典型。俄国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则把典型推到极致,他的理论的基石就是典型论。他甚至说:“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6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中国文论界长期受此思想的影响,也认为典型就是文学创造的理想,把一切文学作品都用“典型”与“典型化”去衡量,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削足适履”现象。例如有人把杜甫的《春望》也放到“典型”的框架中去解释,杜甫似乎成了一个写实的小说家。用一种不实用的理论工具去任意宰割对象,结果对象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分析,反而被大大扭曲了。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如《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绝大部分都不走“典型化”的艺术道路,当然也不能用典型这个标准加以衡量。其实西方原始的艺术、抒情诗、现代派的大部分作品,也不适合以典型加以分析。把典型作为文学的唯一理想是西方文论的严重缺陷之一。我们照搬西方的典型论来解释一切文学,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失误。
文学是人的心灵的创造。尽管文学的沃土在现实生活中,但现实生活如果不经过作家的心灵化,是断断不能变成文学作品的。人的心理机能不是单一的,按康德的说法,人的心理机能是知、情、意的三维结构。知是认识、知识等,情是感情、情绪等,意是观念、义理、意向等。中华古代文论对作家的心智结构的论述也印证了康德的观点。自然作家的心理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如感觉、知觉、表象、回忆、联想、想象、情感、理解等,但就这些心理机制的活跃所产生的思维方式而言无非是三种:第一,格物。“十年格物一朝物格”(金圣叹),“格物”是认识,“物格”就是认识的结果,了解世界,掌握世界。这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知”。第二,起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情以物兴”是说情感来源于“感物”,“物以情观”是说作家以诗情看待周围的世界,形成了情感态度,要一吐为快,即激起抒发情感的愿望。这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情”。第三,意向。“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这里的“意”,不是一般的道理,是一种幽深的不可言传的观念。《系辞》不是文论,但其思想与文论相通。这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意”。文学虽然总起来说是一种审美形态,但更细致地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文学有不同的类型,起码我们可以分为象征型文学、抒情型文学和写实型文学。象征型文学倾向于表现人的心理机能中的“意”,抒情型文学倾向于表现人的心理功能中的“情”,写实型文学倾向于表现人的心理功能中的“知”。文学类型的三维构成与人的心理功能是对应的。这就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文学是人的知、情、意的心理机能的全面充分的发挥,或者说文学是人的三维心智所催开的五彩斑斓的花朵。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文学就只有象征、抒情和写实三种形态,既象征也抒情也写实等不易说清的新形态还时时涌现。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学的基本形态就是象征、抒情和写实。
如果文学的三种基本类型这一事实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进一步就要追问,这三种文学的类型达到了艺术的极致,其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更简明地说,三种作品类型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模仿”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文学就是认识,就是社会知识之一种。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模仿成为文学的主流。这样西方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讨论的就是写实型文学的“悲剧”,于是塑造人物性格成为中心,人物典型成为西方文学的理想。无论是荷马创作的叙述特洛伊战争和奥德赛海上冒险的“史诗”、欧里庇德斯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戏剧、法国莫里哀等古典主义作品、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还是19世纪大量涌现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都是模仿,其文学理想都是创造典型。的确,西方文学创造了许多性格独特而又丰富的典型,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成为认识社会的镜子。在典型理论的研究方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揭示了它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历史与文学“两者的区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见《西方文论选》上,65页。)。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亚里士多德说:“所谓‘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
首先要追求这个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见《西方文论选》上,65页。)什么是个别性呢?亚里士多德说:“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同上。)这里所说的亚尔西巴德是雅典的政治家、军事家。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所谓个别性不是属于一种人的共同属性,而是属于像亚尔西巴德这个人的属性,这个人的属性是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亚尔西巴德。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认识到,普遍性寓含在个别性中,普遍性通过个别性表现出来。基于亚里士多德所达到的高度,朱光潜教授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指出:“这正是典型人物的精微意义。”(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此后关于典型问题仍然有不断的争论,经历过从“类型”论到“个性特征”论再到个性与共性统一论的过程。如用“类型”的思想来解释典型,如说要画一个美女就要把全城五个美女各自的美集中于一人身上,不够美的要完全剔除;如说要写一个商人就要搜集三十个商人的共同特性,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不符合商人共同性的要剔除。17世纪法国诗人兼批评家沙坡兰就认为典型就是普遍性,要把不符合普遍性的东西剔除出去,他说:
“艺术所要求的是事物的普遍性,它需要把历史由于它严格的规律而不得不容纳的特殊的缺点和非正规的东西从这些事物排除出去。”([法]沙坡兰:《法兰西学院关于悲喜剧〈熙德〉对某方所提意见的感想》,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5),1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类型化理论导致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但是到了歌德、黑格尔和别林斯基那里,西方的典型论已经充分成熟,个性与共性统一论占了上风。如黑格尔的“理想”(即典型)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论述,别林斯基关于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的论述等,已经把写实型的文学理想的典型,揭示得深刻而充分。西方作家、文论家认识到,文学(他们眼中的文学主要是写实型文学)当然是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要像镜子一般把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映照下来,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宣称: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见《西方文论选》下卷,168页。)但是文学怎样才能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映照下来呢?作家怎样才能成为社会的“书记”?这就要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巴尔扎克就十分清楚,他要成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只有“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糅成典型人物”,来“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从而“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见《西方文论选》下卷,168页。)。应该说,西方文论对于写实型的文学的理想,概括出了“典型”这样一个范畴,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获得了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这是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西方文学的成果主要是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它们像镜子一样,映出许多时代的历史面影,对于人们通过文学认识社会有极大的效益。所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立刻吸收了西方典型论的理论和思想成果,在写实型文学方面开辟了新的局面,也创造出诸如阿Q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反映了新时代的历史面影,这也是成功的。
模仿论及其典型论在西方“雄霸了二千余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推动了写实型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和英国出现浪漫主义思潮,英国湖畔诗人的诗歌以及拜伦、雪莱的诗歌崛起,抒情型文学表现出强劲的势力,理论上也出现了“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切好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诗的目的是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和有效的真理”([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见《西方文论选》下卷,6、9、13页。)等理论概括,但是就抒情型文学的审美理想而言,并没有像写实型的文学理想那样提出新的理论概括。
这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学植根于认识论,其主流是写实,而且传统深厚,但抒情型文学则处于边沿地位,给予的理论关注也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反观中国古代,从六朝开始就有了“意境”说的萌芽,唐代正式提出“意境”说,并作为理论关注的中心而延续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探讨,概括出抒情型文学的审美理想。这是西方文论无法与中国文论相比的一个重要之点。
西方的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立了所谓“现代派”文学的天下。“现代派”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含了西方现代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流派。各种艺术流派的追求也有很大的差异。如20世纪以来的所谓“意识流小说”、“象征派诗歌”和“荒诞派戏剧”,其追求是各异其趣的。但就其成功的作品来说,其中都隐含着象征,大体上可以纳入“象征型文学”的范围。“现代派”的文学理论,标榜各种“主义”,名目众多,纷繁复杂。然而就象征型文学的审美理想来说,他们提出了“意象”和“意象主义”的概念。“意象”被一些人视为象征型文学的理想。“意象主义”(Imagism)是1912—1917年流行于英国,更盛行于美国的诗歌运动,代表人物是庞德。众所周知,庞德是一位对古代中国和日本诗歌极为推崇的西方诗人。他曾翻译过中国古典诗选集《神州集》,对于日本的俳句也极有兴趣。
他惊异于中国古典诗歌只用几个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形象的名词,就构成一句或一首生气盎然的诗歌,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中国古典诗歌中这种略去连接词或介词的句式,被庞德等人看成用“意象”并置来显出诗意,被他们推崇为诗歌的理想。
庞德有句名言:“与其写万卷书,不如一生只写一个意象。”这与一些写实型文学作者的理想———与其著作等身,不如创造一个典型,是一样心理状态。这的确表明庞德和许多诗人把塑造意象看成是诗歌的理想。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刻意模仿中国古诗的所谓“意象并置”或“意象叠加”。如庞德本人就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意象主义”的诗:
在一个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