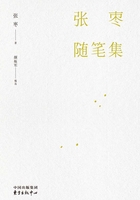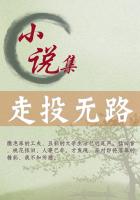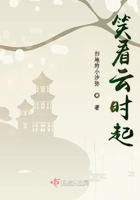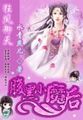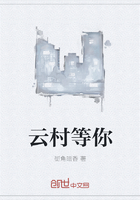1.太阳正在落山
张一弓
当属于你的太阳正在落山
生命的黄昏如无声的狼群向身边弥漫
你听见,你苍老的心脏铿然跳动
如武士的鼓点处变不惊
于是,你依旧弹奏着琴弦走过旷野
不在乎身后边越拖越长的背影
当属于你的季节寒风骤起
老树像抛撒纸钱一样地落叶飘零
你看见,一颗被遗忘的果实高挂枝头
它拒绝成熟而坚守苦涩的生命
于是,你用形同树根的手指弹奏情歌
蓝蚯蚓般鼓突的血管里青春沸腾
当小喇叭不再为你吹奏赞歌
多情的秋波已懒得顾盼回眸
你听见,孤雁划破长空的啼叫
凄厉而清越的长鸣在天际缭绕
于是,你收起喑哑的琴弦加紧赶路
天上和人间的旅途上没有孤独
当林中传来夜猫子的笑声
夜幕如墨染的瀑布铺天而降
那时你身心俱疲,白发飘霜
颤抖的指尖触到了天边的残阳
于是,你轰然点燃了自己
留下一小点儿瞬间消逝的火光
2.我有这样一位父亲——女儿眼中的张一弓
张婷婷
父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听父亲说,虽然我的祖父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祖母是开封女子高中的语文教师,使他自幼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但他原来只是跟新闻有缘。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河南著名的教育家、校长杜孟模先生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当了编辑。那时他还不满十六岁,大家都叫他“编辑娃”。接着又成了“记者娃”,后来又成了《河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当我和妹妹成了报社大院里的孩子,排字房的老工人向我们讲过,父亲第一次到排字房改稿,被他们当成了恶作剧的顽童,揪着他的耳朵,把他逐出了车间。
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小说处女作《金宝和银宝》。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和母亲认识,我还没来得及出生。我没有看到过这本小说,只是听父亲说,那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父亲也没有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表现过喜悦之情,只是表示惊讶说,我怎么敢于把那么幼稚的东西拿出去呢?
1959年,父亲是《河南日报》驻洛阳的记者,在洛阳的文学刊物《牡丹》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主编著文称赞说,就其人物内心刻画的深刻性和生动性来说,它是本刊发表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篇。这时,父亲已经与美丽温柔的广州姑娘黄淑雯结婚,我也在洛阳呱呱坠地,还不知道分享父亲的喜悦。但在1959年那个多事的秋天,《母亲》又变成了“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遭到了口诛笔伐,据说仅发表在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就有二十八篇之多。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从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中挺过来的。但是我知道,《母亲》的遭遇把父亲的文学才华压抑了二十多年,也为他后来艰辛而绚丽的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蓄积了能量。
当我初谙世事、而《母亲》仍被认为是“大毒草”的日子里,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对那顶“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表示不满,只是听到他私下里用排比句表示不平说:“仅仅是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仅仅是在艺术表现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内心刻画的一些手法,难道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挞伐,乃至于在省委机关报上点名批判,这不是用‘喀秋莎大炮’打麻雀吗?怎能这样‘派活儿’!”
我听不懂这些排比句里的含意。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似乎是忙碌而快乐的。“文革”前,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是在对周末一家人欢聚的期盼中,是在父母亲相跟相随的歌声中度过的。舞池中母亲优美的舞姿,球场上父亲矫健的身影,永远是我们小姐俩的骄傲。
20世纪70年代,两个弟弟相继在郑州出生。据父亲那些《河南日报》社的同事们说,得了儿子后,“一弓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在篮球场上一跳八丈高”。两个弟弟也带给我们小姐俩意想不到的快乐和烦恼。家里一下子添了两张嘴,又请了一位保姆奶奶照看,快乐的小家庭一下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日夜赶稿的父亲,把爱不释手的“黄金叶”,换成了一毛多钱一包的“勤俭”烟,还惹来报社里“烟民”伯伯、叔叔们的“讥笑”。母亲为了保证全家人的营养,每天都要让我去肉食店买三毛钱的肉馅儿,而她给父亲盛饭时,总要给父亲那只花瓷大碗中多拨进一些炒得香喷喷的肉馅儿。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我蹲在家门口的大榆树下洗衣服,父亲坐在我对面的马扎儿上。他用商量一件大事儿的口吻说:“婷婷,爸爸想把烟戒了,你看怎么样?”从小习惯了父亲抽烟的我,一直以为抽烟就是父亲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随口答道:“不抽烟就写不出文章了,爸爸不能不抽烟,倒是咱们家一天三毛钱的肉馅儿可以不吃……”父亲被我这一句不经意的回答感动了,他一声不吭地进了屋。许多天以后,这次关于戒烟的对话,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父亲却给我买了一双粉红色的丝袜,真是让我欣喜异常。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件高级消费品,它足足花去了父亲一条半“勤俭”烟的钱呢!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竟有如此大的含金量。这是我今生穿过的第一双丝袜,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双袜子。
在报社,父亲是公认的“笔杆子”。父亲那笼罩在朦胧烟雾中的背影,不时在我少年的脑海里浮现,而他的“笔杆子”却忽而变成了“白”的,忽而变成了“黑”的,忽而又变成了“红”的。他曾经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和文艺观”,曾在“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在“黑帮队”里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他当过记者站站长、理论处处长、报社副总编,还干了几年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但是,官场的沉浮始终不能改变他为人处世的耿直和对生活深刻的思考。“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就在报社对面。一天放学时,同是报社子女的一批小同学说,报社大礼堂里斗黑帮,快去看黑帮啊!我也好奇地跑进了礼堂,却一眼看见,父亲也站在黑帮的行列里。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哭着跑出了礼堂。我不知道这个“大革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记得父亲在批斗会上的站姿与众不同,他低着头,却挺着胸,站得笔直。事后,父亲说:“怪我没学过弯腰,你们的爷爷从我小时候就教我‘站如松,坐如钟’,要直着腰杆儿做人……”
1976年3月,我上高中三年级,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郏县“广阔天地”公社搞社会调查。同学们革命热情高涨,大家一商量,就决心不回来了,要在那里“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给父亲写信说,我出了一个考题,请父亲回答,我决心在农村干革命,你同意吗?那时,父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报社副总编,我以为这是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我是大女儿,家中还有两个学龄前的弟弟需要我帮助母亲照料。没想到父亲回信说,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高兴,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绝大部分同学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家长的反对,四十个同学只留下了六个。我感到自己有一个无私的父亲,这是我的幸运。
在农村时间长了,我们的热情大打折扣,开始为自己的出路发愁。最理想的出路是参军。我又多次向父亲提出参军的要求,希望他能以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帮我说句话。父亲却守口如瓶,不置可否。最后,父亲被我逼急了,说:“你爸爸就是自己闯出来的,没有依靠过任何特权。你想有出息,就自己去闯!”几天后,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军上衣,说:“你不就是想穿穿军装吗?这件军装送你在乡下穿吧。”参军的梦破灭了,但那件军上衣还真让我臭美了好些日子。
我下乡不久,生产队干部知道父亲在省里工作,就托我给队里联系购买一台大马力拖拉机。我回到省城“走后门”,父亲这次还真给面子。当我拿着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的供应指标回到乡下时,受到了英雄模范般的欢迎。
好景不长,政治风浪的沉浮,又将父亲冲到了人生的谷底。我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知青入党的入党,参军的参军,回城工作的回城工作,生产队知青点上黑灯瞎火、清锅冷灶,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回郑州看父亲,父亲被“隔离审查”了。经过批准,我才到“隔离室”见了父亲一面。那是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地方,父亲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人在门外看守着他。父亲面容憔悴,头发很长很乱,对那间阴沉、狭小的隔离室却表现出“宾至如归”的样子,正守着一个小型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英语广播教学。据说,他已经在学习中级班英语教材,而且抄写了厚厚一本《英语九百句》。女儿的到来触动了父亲最柔弱的那一部分感情。自身难保的父亲还必须面对他所支持过的一个“革命行动”给女儿带来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他久久地沉默着,忽然用坚毅的、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要求我:“你一定要刻苦复习功课,必须考上大学。依靠自己吧,这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相信你。”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父亲“逼”我考上大学,给了我决心,也给了我信任,我可能不会在学习和事业上有今天这样的进步。正是在“隔离室”见到父亲的次年,我考上了大学。
我在乡下复习功课时,又一次回家,终于见到了解除“隔离”、卸去乌纱拖累的父亲。报社的叔叔、阿姨私下告诉我,他们很同情我的父亲,因为查了他几年,没有查出一条属于他个人的问题。他在“文革”中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有一篇离开过当时的“红头文件”和省委意图,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那时候,父亲在认真地做着两件事:一是养鸡,他把人吃的药片碾碎,拌在鸡食槽里喂鸡,成功地预防了鸡瘟,十几只“生产白”被父亲伺候得白白胖胖。墙头挂历上,逐日记录着母鸡们的贡献。父亲每收一个鸡蛋,都要十分郑重地在挂历上画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那是五个鸡蛋。父亲在挂历上日积月累地画满了“正”字,这是一家人补充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父亲沉浸在少见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喜悦之中,大发感慨说:“当初要我从事物质生产就好了,在任何政治背景下,鸡蛋就是鸡蛋,它所包含的蛋白质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怎么说,是不会变成‘毒草’的。”父亲的第二件事,却仍然是不可改悔地从事使他伤透了脑筋的精神劳动。他每天晚上都要写作,常常写到次日凌晨。在我家不足五平方米的小过道里,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小木桌,吃饭时一家人坐着马扎儿围在一起,一到晚上大家睡了,父亲就凑着吊在天花板上的一盏电灯,伏在桌边爬格子。因为他那时心情不好,家里人都不敢问他在写些什么,不知道在他写出了那么多的灾难以后为什么还要握住笔杆不放。不久,父亲被下放到距武林名刹少林寺不远的登封县卢店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直到插队三年的我,考入了郑州大学之后,才知道父亲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创作了轰动文坛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家里过道上的那个小饭桌,正是这部小说的“产床”。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是与现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有着直接关系的。1979年底,《收获》编辑向主编巴金先生推荐了从自由来稿中筛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巴金先生看了很喜欢,决定发表。按照当时的惯例,发表作品是要审查作者的。就在审查作者的时候,有关方面以各种理由反对这部小说的发表。是巴金先生毅然拍板,推出了这部后来被称为“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反思文学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在评选“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时,有关方面又出来反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评委会只得把矛盾交给了担任评委会主任的巴金先生。巴金先生不但同意《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得奖,而且力主将其列为一等奖之首。父亲曾说过:“没想到一位文学大师,竟暗暗地保护着一棵小草。”或许是巧合,就在发生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时,我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聆听现代文学老师讲解巴金先生的《家》《春》《秋》三部曲,做梦也想不到巴金先生给予我们这个家的恩惠。当然,这一切最终都得益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就没有我张一弓!”(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
可能是父亲想给陪他一起吃了不少苦的母亲做些补偿,他用小饭桌上的精神创造换来的稿费,给母亲买了一块崭新的瑞士英纳格坤表,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奢侈品。从这时起,父亲把时间都交给了文学,他再也顾不上去照看那群下蛋的老母鸡了。也正赶上省委家属院清理私搭乱建,他就让妹妹把鸡公鸡婆请出了鸡窝,送给了一家“道口烧鸡”老铺,让它们再作一点最后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是父亲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他高产丰收的黄金季节。父亲在这个高峰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年)、《张铁匠的罗曼史》(1982年)、《春妞和她的小嘎斯》(1984年),连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1981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赵镢头的遗嘱》(1981年)、《流泪的红蜡烛》(1982年)、《考验》(1982年)、《山村理发店纪事》(1983年)、《火神》(1983年)等八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有的被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出版界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问世,实践了父亲“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作一些忠实的‘记录’”(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和不断变化、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文学精神。父亲的经历总是大起大落。1983年秋,他又从登封农村被调到省文联专事写作。这时,距他调离新闻工作岗位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已经奠定了作为“文学豫军中的骁将”、“河南文坛的形象大使”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