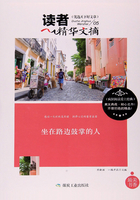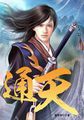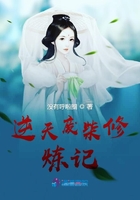乡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一:榨匠
父亲是个榨匠,因此对打榨,我便有比别的行当更多的熟稔。时至今日,父亲那拼尽力气吼出来的嗨哟,以及叮叮当当的牛铃、吱吱呀呀的碾声……常常进入梦里,以至于我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种听一首老歌,欣赏一出舞蹈的感觉。
今年二月,我回到老家,想再看一看榨坊,可没能如愿。那里,别说碾子、榨已没有踪迹,就是想找到一点踪迹一个零件也难。那里早已是一片蒿莱。
榨是用来榨油的。油茶籽、芝麻、桐籽、漆籽这些油料植物要变成油,就要通过榨榨出来。
榨的构造很简单,四块圆木组成的榨身,固定和支起榨身脚,悬吊在榨一旁的撞杆,以及往榨身里添加的种种楔子(排楔、倒楔、上扦、下扦、油饼、坐狗脑、行狗脑、泡子)等。
这一切都是木质的。当然这些木头的材质是硬度和韧度很好的枇杷木、梨木、核桃木、油杉等,而且榨身还需要木头足够宽大,使其能够在中部掏出一个弧,在四块圆木合起来时,能形成一个直径一尺多的圆形空间,用来放置油饼及各种楔子。因此,一合榨便可以装满整整一间屋子。这在乡村,算是庞然大物了。小时候,榨身常是我们“作战”的战场,我们爬到榨身上面,以直伸向上的榨腿为掩体,向对方投射泥土做成的炸弹。可见榨是多么宽大。
撞杆的材质比榨身更要坚实,一般用核桃木做成,两头细,中间粗,像一条巨鲸,打击的一头,装有嵌有铁质十字的铁圈。它重达三百斤左右,垂吊在一根专门的“门”字形的木架上,距地面约半人高,当它从高高的地方划下来时,可以正好打击插在榨身里面的扦脑。
平常,不打榨的时候,它一头抵在地上。我们会骑马一样骑上去,享受摇篮一般的摆动,或者几个同伴骑到两边,像坐跷跷板儿一样玩耍。想来,这也算是我们成长的导具和摇篮吧。
在榨坊里,除了榨,还要有锅、碾、甑等配套设施。锅是用来炒菜籽、芝麻、花生、漆籽的。一般而言,榨食用油,都需要先炒制植物籽实,这样油才更容易榨出来,而且油才香。这也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
碾子就是将用来榨油的菜籽或花生等油料碾烂的工具。它由碾架、碾槽组成。碾架酷似一辆装有两个轮子的架子车。只不过两个碾子是青石打制的,而且一前一后装在碾架上。碾槽装成一个圆圈,碾架的一端固定在这个圆圈的圆心。一般而言,碾架运动的动力是牛、马,或者是水能。
碾子也是十分有趣的。在牛和马拉着碾架绕着碾槽盘旋时,碾盘和碾槽会发出一种咯咕咯咕的声音,碾架和几处转动的地方也有声响,吱吱呀呀地,就像一首舒缓悠长的歌谣,假如那天是一头颈项上佩戴了牛铃的老牛拉碾的话,叮叮当当的牛铃声就会像小河中的浪花一样美丽。这就成了一曲由金、石、木的声音共同组成的绵延不断的交响。
大人说,去给牛赶蚊子去。我们就会爬上碾架,坐在上面,挥舞着一匹棕叶,驱赶在牛、马屁股上面乱咬狂叮的蚊蝇,贪婪地吸着从碾槽里发出来的浓得像稠稠的油一样的芬芳,直到碾槽里的东西碾好了。
一架常用的碾子,碾盘的边缘和碾槽的底部光滑透亮。那是它们被油浸泡了许久许久的缘故。好像它们里面贮满了油,用手一拧,可以拧出金灿灿亮晶晶的油来。
花生和芝麻碾好了,就上作甑了。作甑比蒸饭的甑子要大若干倍,圆周大约两米多,要两人合抱,它被泥巴和土砖“砌”在锅上,不能活动,一般而言,作甑蒸一甑可以装满一榨。为便于操作,它打在地面上,榨的旁边。
这样大的甑子,就要与此相匹配的大锅和大灶。大灶因其蹲在地上,形似一只卧虎,人们就叫它老虎灶。这样的大灶,就有较大的灶门,有很粗的烟囱。因此,作甑一丢火,灶前便是一片火红,灶里发出呼啸的声响,伸到屋脊上的烟囱冒出阵阵幽蓝的炊烟。一会儿,甑上冒气了,气也越来越大,像云雾一样在榨坊内翻滚。
这就是一座榨坊的几大件。有了这些设备,榨匠就可以从花生、芝麻、漆籽等等籽实中榨出亮晶晶香喷喷的油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炒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是碾、蒸、打。这些工序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假如火候和力度掌握不好,则会影响出油,以及油的质量。
譬如说炒。炒是在另一口灶里。先将锅烧热,烧干,待锅内达到一定温度,将被炒的东西倒进锅里,一个人手拿木抄子站在灶台边,用木抄子不断地在锅里搅动,使之受热均匀。待锅里发出一种香味,炒制的人从热锅里抓几颗出来,用拇指和食指一捻,看看翻炒的程度。如果手指上有了油,壳容易捻碎了,估计好了,就迅速将东西铲到事先摆好的晒席上。
炒的关键在于火候,过了,出油少,油老;欠火,油嫩,也差香味。
打桐油是不需要炒制的。但要退壳。桐籽是坚壳类植物,这种坚壳掺杂其间,可使其具有一定的涩性,所谓退壳,就是要退去一定量的坚壳,但退壳的多少也有学问。壳退得少了,壳碎在里面,要裹油;壳退多了,打的时候,容易从草衣里面挤出来。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油就榨不出来了。
又譬如包。包,在家乡称作“包箍”。“箍”的音,在坊间能指称几种东西,一种是包箍的铁圈,一是指榨过油之后的渣饼(可能此箍写作“枯”更合适),还指要上榨的蒸好的箍面。
包箍就是用铁圈、草衣将箍面包成圆饼。包箍也是有奥妙地。首先,每个箍必须是等量的,即每个箍里所包的箍面分量要基本相等,不能有厚有薄。薄了,打的过程中,铁圈靠在一起,油就榨不出来了;厚了,箍面就从草衣里挤出来了,油也不能完全榨出来。所以,榨匠一般都会重视这个环节,而且练就了较好的手感和眼力,三瓢半或者四瓢就是一个箍的分量,而且误差一般不会超过几两。其次,包箍把衣子铺好。所谓“衣子”,就是稻草,将一头扎了,四散抖开,便成了一个圆。把这个圆放在一个圆形模具里,然后就倒进箍面,包起来。
会包箍的榨匠们事先是把三道铁圈放在一块干净锃亮的石板上,然后罩上模子,放入衣子,均匀地打开,放入模具里,这才开始舀作甑里蒸得滚烫的箍面。然后,人站进去,用脚踩紧,待箍面舀到一定高度时,拉上第二道铁圈,再踩,舀满时,拉上第三道铁圈,最后将留在模子外的一段衣子折过去,将箍面包得严严实实。
包得好的箍,每个箍的厚度都是一样的,铁圈之间的间隔也是等距的,衣子的每一根稻草都很均匀,没有箍面会漏出来。它们一个一个码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人高。好像一筒拆开了包装的酥饼放在那里。
当然,打榨最有技术含量,最像舞蹈表演的劳作便是打。
所谓打,就是把沉重的撞杆高举起来,然后猛力击打插进榨身里的大扦。
箍包好后,榨匠把它们一个挨一个放入榨中间的一个凹槽里,然后再塞入排楔、倒楔、狗脑、上扦、下扦等。这些东西,就是挤压箍饼的。排楔是一个约两丈多长的前窄后宽的楔子,就是它,被撞杆打击,一点一点钻进榨身里,因为越进越宽,里面越挤越紧,油便被挤压出来了。打榨打的就是上下两根扦。而倒楔的形状恰与此相反,它前面宽,后面窄。主要是用来抖榨(使挤紧的排楔松开,以便把排楔和箍取出来)。
打有不同的方法:一个人打和多个人打。但无论是几个人打,都需要力量和技巧。
撞杆很重,约三百多斤。举起它除了力量,更要技巧。因此,打榨,即使一个人打,也需要手、脚、眼、气息、声音之间的完美配合。一般是这样:打榨的人左手号住栏杆中间的吊担,右手贴在身体前方的撞杆上,侧身横推着撞杆,让撞杆与榨身成垂直方向游动。这时的游动相当于助跑,为的是更轻易地把几百斤重的撞杆举起来,为后面猛力一击蓄势。这样来回游动两次之后,打榨者就要举起撞杆来了。这时是撞杆回游时的瞬间,他贴在撞杆的右手,哧地一下抠住了撞杆前端的一个凹处,脚下快速地横向远处移动,就在移动到最远处时,嗨地一声,双手将撞杆高举起来,使撞杆与地面垂直,再猛地转身,快速向前,呀地一声吼,将撞杆稳稳地打击在扦上。
这是富有力度的,又是轻盈而灵巧的。在这一击中,打榨人吼出的号子嘹亮而悠远,气吞山河,撞杆与扦的撞击声,干脆而响亮。常常会唤起山谷一波一波的回音。我时常想起这种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是从心底里喊出来的歌谣,这种歌谣会让宁静的乡村顷刻间活跃跳动起来。似乎宁静的乡村就是被这打榨的声音叫醒的。
打榨的动作更是美妙绝伦,分开来看,脚下有垫、转、跨、跳,身体有伸、倾、仰、俯,节奏有快、慢、急、徐,臂有屈、伸、弯、展等若干种,也就是说,这一击,一个人身体的肢体都在协调动作,人的力量和美,也在这一流畅的动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这种打法,主要是用于打花生、芝麻、菜籽、桐籽等,打漆籽是不能这么打的。因为漆油太容易凝固。因此,榨漆油时,就不允许撞杆还有游动的间歇。
打漆子是众多人一齐揪着撞杆,紧促地去打。这种打法叫“拉抱”。
父亲小时候就开始打榨了,在仓坪一带,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榨匠。
仓坪一带盛产桐籽、漆籽、菜籽。清末民初,桐油的出口使得这一带榨油业十分繁荣。一般大户人家,瞄准了桐油和漆油的利润,想方设法开榨坊。
那时的仓坪,时常可以听到山谷里传出打榨的嗨哟声,此起彼伏。
父亲的“榨艺”正是得益于感觉中漫山遍里的榨坊。
建国后,父亲因为一身打榨的功夫,被当时的粮店请去打榨。我二月份回去的时候,专门问了问父亲在粮店打榨的情况。这时的父亲眼里放出光来。
他说,当时粮店里同时请了几个榨匠,榨菜油和桐油。但是那些人都没有他榨出的油多,一榨相差五斤。粮店的负责人问那些人原因,他们总是说榨有问题,或者说灶有问题、菜籽有问题等等,粮店负责人于是举行了一次打榨比赛。他们把四合榨摆在一起,把灶也打在一起,用同一杆秤称重,然后用同一杆秤称油。结果,父亲打出的油还是比别人多五斤。
别人不得不服。
因此,这便成了父亲一生引为自豪的事。他谈到这件事时,脸上微红,像喝了酒一样。
现在想起来,格外觉得这种劳动竞赛很生动,很有气魄。想想看吧,四合榨摆在一起,四口灶筑在一起,这是多么盛大的劳动场面啊,而且,炉火熊熊,蒸气升腾,牛铃当当, 歇斯底里的嗨哟声、撞杆与木楔的撞击声响成一片,这是多么壮观、火热呢?
当然,在父亲的这个辉煌时候,我还没有来到人世,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个盛大得令人振奋甚至惊心动魄的劳动场面,我看到父亲打榨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父亲从粮店里回来,又在队上打榨。那时候,各个小队都保存了一座榨坊。我们队里的榨坊支(设)在小队仓库的下面。父亲去打榨的时候,常常会带着我。
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饥饿。因为我至今记得我们那常常装着野菜粥的饭碗。
也许是因为看打榨有趣,也许是因为饥饿,到榨坊可以奢侈地闻一闻油香,这时候的榨坊是一个大人小孩都喜欢去的地方。每到放学,或者社员放工,小孩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就前去榨枋,在那里看打榨、聊天或吸烟。
大人们会打谜语我们猜:
“婆婆横睡起,老头儿直睡起,老头一使力,婆婆尿直滴。”
猜不出,大人们就笑起来,指着正在哗啦哗啦流油的榨说,真笨,这不是吗?
原来这谜语是说打榨的。于是我们就高喊起来:“婆婆儿横睡起,老头儿直睡起……”嘻嘻一片,乐趣无限。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学到的第一个谜语吧。
当然,我们之所以如此喜欢榨坊,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原因:揩油。
大人们揩油的办法是拿烟叶。他们坐在灶口或者榨边,把烟口袋掏出来,把烟叶放在油碗里浸,然后又用这截浸过油的烟叶去濡染别的烟叶。说这样的烟香。
我们揩油的办法和大人不同,是从碾槽里面抠一点花生末子或芝麻末子吃。
我们都知道打花生油、芝麻油时,都是需要炒熟碾碎的。圆形的碾槽是一断一断有弧度的石槽拼接而成的,碾花生、芝麻时,石槽的拼接处往往会积压一些细末,塞得很紧,刷是刷不起来的。因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空间。我们放学后,书包都来不及放回屋里,就直奔榨坊,等大人们把东西舀起来。这时,我们就一个个趴在碾槽边上,伸手去挖塞在接缝里的花生、芝麻末子吃。我们人很多,一下把碾槽占满了,大人们便笑我们像井台边的蛤蟆一样。
有时,手抠不上来了,有人干脆把脑袋抵进槽里去,用舌头去舔,有大人吼起来了,“哎,东子,你舔什么舔,别人还吃不吃油啊?”又有大人出来说,“人娃子的,舌头干净,又不是猪娃子、狗娃子。”有大人站出来这么说,舔的就大胆而欢畅了。
现在想起这件事,好笑,可是心里酸酸的。
说到这里,偶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碾花生、芝麻要在下午?
一般而言,打榨是早晨开始炒,冷了就碾,碾了蒸,蒸了就打。也就是说,按照程序,碾花生、芝麻应该是在上午。那么,父亲为什么要放在下午来碾呢?是有意让我们回去抠碾槽里面的花生末子吗?
当然,因为父亲打榨,我自然地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譬如我给父亲送饭,母亲不让我在家里吃饭,而是要把饭送了再吃。母亲会把父亲的饭盛得很满。而我把饭交给父亲时,父亲端起碗吃一大半,然后望着同伴杞叔笑一笑说,吃不完了,又望着杞叔笑一下,就会从锅里舀一点点油倒进碗里,把拌了油的饭递给我。
这时是干集体,我知道父亲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是我分明感觉得到,父亲吃过饭后,打的时候,是更卖力了。他的脸膛和颈脖一片鲜红,叫喊时,颈上的青筋粗壮突出。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是想用他的力气把淋在我饭碗里的油榨出来吧。
队上的榨坊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拆掉的。这当然是因为体制的改变和一种新榨的出现。这种新榨人们称作红榨,铁质的,以电为动力,体积很小,但榨油的效率却是木榨的好几倍。
因此,木榨,这个曾给我们的生活无限芳香和滋润的工具,这种最像原始舞蹈的劳作,像一只古老牧歌一样,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队上这合榨原是没收地主老杨家的,这合榨要处理,会计说,五十元钱吧,优先老杨购买。老杨最后五十块钱把这合榨买走了。后来,他当木柴卖给了一个木匠。他自己家里只保留了一个撞杆。
老杨已在十几年前死了。他的后人觉得撞杆放在家里占地方,没用,就劈了当柴禾塞进灶膛里烧了。
这一缕青烟已在几年前飘过。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