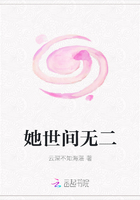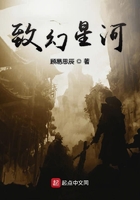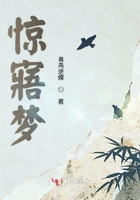CALAVERAS(卡拉维拉斯)。一度看起来最真实、最本原、最自然的东西,后来往往被发现只是一种文化构建的产物。一些民族服装的样式来自轻骑兵花里胡哨的军装,一些玻璃彩绘模仿的是教堂的巴洛克彩窗,一些所谓的民谣是派生自文学作品,比如我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基日达尼地区流传过一首民谣,唱的是一个墓地鬼魂夜里将他喜爱的人劫持到马背上。
地方传说也一样。有些仅仅是地理因素使然,但有时也是文学想象中的某个主意使人们心机一动。时不时地就有人说起,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斯塔山和三一山脉看到了“大脚怪”,说一个又是猿又是人的家伙留下了巨大的脚印,像是一种“雪人”(yeti)。这也许出自淘金者的篝火闲谈,但我怀疑这个传说与附近镇子上记者们的利益有关。那地方平淡无奇,了无特色,没有什么能比一个野人近在咫尺更令人兴奋。
每年5月,卡拉维拉斯(Calaveras)都要举办一场跳蛙比赛。如果不是马克·吐温用他的小说《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使该县扬名,没人会听说这个地方。比赛地点取在内华达山脚下、萨克拉门托东南的天使营小镇附近的田野里。在马克·吐温写他的小说的时候,那儿只有开采金矿的营地;他把他听来的一段逸闻写成了一个短篇。如今,当地有了这么一个不太广为人知的节日。尽管如此,当一只青蛙打破了纪录,报纸上还是会有所报道。届时那里会停满汽车和轻型飞机,因为养蛙人(主要是学校里的男孩子们)和蛙迷甚至会从邻近的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赶到那里。如何才能让青蛙跳跃?你得跺脚吓唬它。我以前不知道青蛙们本领高强。一只好的参赛青蛙可以跳出十九英尺远。最棒的青蛙们跳出的距离需要一英寸一英寸地丈量才能分出高下。我们把维克塔·维尼茨卡博士(Dr. Wikta Winnicka)也带到那里。所以那应该是60年代中期的事。她是约瑟夫·维特林同父异母的姐妹。她玩得很开心。我们开着沃尔沃一路旅行,后来有人生病,我们才只好停下来。我们穿越了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又继续向北,穿过俄勒冈和华盛顿,直抵加拿大,期间我们曾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露营。
文学与地点。对华沙的某些居民来说,博莱斯瓦夫·普鲁斯[1]的长篇小说《玩偶》(1890)有一种栩栩如生的真实感。两次大战中间那段时期,有人在位于克拉科夫郊区街(Krakowskie Przedmie?cie)的一幢公寓楼的墙上钉了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玩偶》主人公斯坦尼斯瓦夫·沃库尔斯基曾在此居住。”
CAMUS, Albert(阿尔贝·加缪)。他出版他的书《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时,我一直关注着人们在巴黎对他的所作所为。他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人们不允许他那样做,因为“反帝”(即反美和拥护苏联)的阵线有一种强制性。在萨特的《现代》杂志上进行的那场丑陋的讨伐中,发起攻击的主要是萨特和弗朗西斯·让松,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加入进来。那是在1951年,正好也是我与华沙决裂的时候。针对加缪,萨特写道:“如果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2]。”
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他为伽利玛出版社工作。该出版社有他这样一位同盟者十分重要。我的《伊萨谷》由让娜·赫尔施(Jeanne Hersch)翻译成法文,加缪读了打字稿很喜欢。他告诉我,我的小说让他想起托尔斯泰有关其童年的写作。
我与伽利玛出版社的关系并不融洽。由于我获得了欧洲文学奖(Prix Littéraire Européen),他们出版了我的《权力的攫取》,随后又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但后一本书从没上过书店的书架。我不无理由怀疑是负责图书发行的人出于政治原因联合抵制了这本书。他们根据加缪的推荐出版了我的《伊萨谷》,但据出版社财务处的人讲,这本书根本就没卖出去过;与此同时,有人从非洲给我捎来了一本该书的第四版。加缪死后,我在出版社就没了帮忙说话的人。根据我与他们所签合同中规定的出版社优先选择权,我把塞迪尔(Sédir)翻译的《故土》交给了他们。但是当时负责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狄俄尼斯·玛斯科洛(Dionys Mascolo),一个共产党员,把它交给了耶日·里索夫斯基(一位当时正住在巴黎的波兰共产党员),要他评估这份书稿,实际上是希望他把这份手稿枪毙掉。这就像19世纪时要求沙皇的驻外使馆评估那些政治流亡者。里索夫斯基写了一份恭维的书评。他们出版了这本书。此后,我决定不再和这家出版社打交道。
我记得同加缪的一次谈话。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问我,以我之见,要是他把他的孩子们送去领第一次圣餐是否合适。当时我刚去巴塞尔拜访了卡尔·雅斯贝斯[3]回来。我曾问雅斯贝斯我是否应将我的孩子们培养成天主教徒。雅斯贝斯回答说,他作为一名新教徒对天主教教义并无偏好,但必须根据孩子自己的信仰培养他们,只要给孩子们接通圣经传统,以后他们会自己做出决定。我差不多是以同样的说法回答的加缪。
CAPITALISM, The End of(资本主义的终结)。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在30年代,世界变得太荒谬,难以忍受,人们无法不去寻找一种解释。我们说服自己:不管怎样,非理性是一种例外,当制度改变之后理性就会占据上风。毕竟,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失业者排队等待施汤;独裁者在体育场正面看台上咆哮并攫取权力;军备竞赛成了给人们提供工作、推动经济的唯一手段;战争没完没了地燃烧——在中国,在非洲,在西班牙。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忙于嘲笑民主,而波兰正在贫困的边缘上艰苦地生长,穿过乡村田野的道路上尘土飞扬。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这一切负责;不曾遭受周围愚蠢所污染的理性,等待着它的时刻的到来。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这就是我作为理性的朋友,当时面对波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
CARMEL(卡梅尔)。
若你在人生几世之后前来寻找此地,
或许我手植的丛林只会剩下几棵树
依然挺立。
(罗宾逊·杰弗斯,《岩石山居》)
树木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这里面向大西洋,地价后来变得奇贵。杰弗斯的后人抵挡不住诱惑,将这块土地出手卖给了开发商。但是他亲手建造的那座岩塔依然矗立,依然是被他称作“岩石山居”(Tor House)的房子。它也是“岩石山居基金会”的会址。
我曾是杰弗斯诗歌的捍卫者,曾不无困难地力图证明一种今天简称为“非人道主义”的东西的正当性。这仅仅是因为,杰弗斯在一个人们连想都没想到过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已在深思熟虑地反对现代主义。他拒绝始于马拉美象征主义的对诗句的加压浓缩,他决定直截了当地表达他的哲学观点,这些无非就是后现代主义。他这是打了个大赌。卡梅尔这地方使我伤感——因为那些他手植的树木,以及声名的无常。毕竟,在20年代,杰弗斯曾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德怀特·麦克唐纳,且以此人为例,视杰弗斯远远高于T.S.艾略特。而今,尽管他依然拥有得其三昧的诗歌崇拜者,但他已变得像“一个业余妇女”——也就是说,一个丑妇。用马烈克·华斯科的一句聪明话来说:他只是给一些业余爱好者看的。
现在就对他的作品盖棺定论还为时过早;它们还需要经过时间天平的反复衡量,尽管从语言的角度维护他那些长篇诗体悲剧大概不无困难。但是,这个以手中之笔反对一切的人,即使是在失败的时候,也有一种高贵之气。
他至少有一位忠实信徒:威廉·艾弗森(William Everson)。此人有一段时间在奥克兰做过多明我会的专职修士,以“安东尼努斯修士”(Brother Antonius)为笔名写作。我曾去位于夏伯特路的修道院拜访过他,也曾将他的几首诗翻译成波兰文。他出版过几本诗集和一本论述杰弗斯哲学的专著。在这本专著中,他大概将杰弗斯过于拉向了自己一边,这意味着杰弗斯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科学世界观”和尼采——被遮蔽了,而他的泛神论狂热被推到了突出的位置。
CENTER and periphery(中心与边缘)。塑成我们文明的一切——《圣经》、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否均出自权力的中心?不总是这样。有比耶路撒冷更强大的首都,而小小的雅典很难与埃及一比高低。确实,罗马帝国给了我们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君主制的法国催生了古典悲剧;英格兰王国,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诗歌杰作涌现于以唐朝皇帝的年号命名的时代。但是,西欧半岛,尽管分成大大小小许多国家,也应视作一个中心,那里出了但丁、塞万提斯、巴洛克音乐、荷兰绘画。
创造的冲动从一国游走至另一国,是件极其神秘的事。由于缺乏明确的动因,我们便用承袭来的Zeitgeist(时代精神)一词指称它。当我们用它在我们自己身上检验时,它显示出强大的说服力,因为欧洲分成创造的西部与模仿的东部(它重复西欧的形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波兰的纪念性建筑重复的是舶来的风格。的确,它们一般都是由来自弗兰德斯、德国、意大利的建造者所建。其教堂绘画总的说来也是源自意大利。一个巴黎人也许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何必要看几位波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既然我知道他们模仿的是哪些原作?
让我们将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一点儿。一位盎格鲁-爱尔兰旅行家描述过1813年的莫斯科。他注意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读法语,写法语,认为这可以理解,因为用一种野蛮的语言和一种野蛮的字母根本写不出东西。同一位旅行者,在骑马去华沙的路上经过诺沃格罗代克(Nowogródek),他断言这个单调、丑陋、不友好的地区永远不会产生像斯特恩[4]或伯克[5]那样的天才(不过他也许在街道上撞见过还是少年的密茨凯维支)。
俄国上流社会从模仿法国作家开始,但不久以后他们不仅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东西,而且用这种语言创造出了伟大的文学。诚然,这个事例为那些将智识活动与权力中心联系在一起的人提供了支持性的说法——俄罗斯文学诞生于彼得堡,那是帝国的首都。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创造力——地域风光、种族、一种无法描述的民族精神、社会结构,等等,但总的说来又说不清道不明。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欧居民的脑子里都刻着一套有关文化中心与边缘的根深蒂固的成见,这套看法在道德上既不中立,也不单纯。德国人确信斯拉夫文化低人一等,将斯拉夫人作为“次人类”大批屠杀;而在法国人的反美主义中,包含着一种对粗野牛仔的蔑视。然而今日,科学和艺术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人们很难不虚心接受这一事实。
在这一领域,成见挥之不去,与此同时,成见也在瓦解。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有年迈的文化,有年轻的文化。这即是说,其语言或已被长久耕耘,或刚被短暂开发,姑且以此为例。既然我用语言工作,我明白发展的各阶段是不能跨越的。我期望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不过我却受制于我的前辈介绍给波兰语言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对它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CHIAROMONTE, Nicola(尼古拉·恰罗蒙特)。在我脑海里,这个名字总是与我对伟大的思索联系在一起。我认识许多名人,但我将名望与伟大区分开来。尼古拉并非大名鼎鼎,他的名字只在他的朋友圈中意味多多。即使是他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报道和文章,也能很好地展示他不可思议的思维理路。他的思想本于希腊哲人,始终关注公共领域,并试图就人道主义者对polis(城邦)的义务作出规定。他的一生,就是在我们这个混乱无序的20世纪介入政治的一个例子:他投身各种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转变成意识形态的奴役。恰罗蒙特对历史和历史真实超级敏感,但他拒绝一切意识形态。他离开意大利是因为他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派一边,任马尔罗[6]中队的飞行员,但他并没有成为共产党的同道。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德怀特·麦克唐纳和玛丽·麦卡锡的非共产党左派群体尊他为大师和导师。他在《党派评论》和《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见解。他后来回到法国,最终于1953年重返意大利。其后,他与伊尼亚齐奥·西洛内[7]合作编辑了《当代》(Tempo Presente),肩负起反对当时由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主导的公共舆论的责任。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有段时间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曾出任过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著有小说《芳丹玛拉》(Fontamara),并被政治“电梯”抬升到声誉之巅。出于道义立场不同,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他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名字既不见于法西斯的意大利,又从反法西斯的报纸上消失。后来,法西斯倒台,他与恰罗蒙特编辑的《当代》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知。对我来说,尼古拉和西洛内代表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正直动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意大利人。
CHURCHES(教堂)。人们去教堂是因为他们是彼此分隔的人。他们希望,至少有片刻时光,能从那包围着他们并被称作唯一真实的现实中脱身,进入到另一种现实之中。日常现实坚硬,野蛮,残酷,难以忍受。人类之“我”有一个柔软的核心,无时无刻不在怀疑它能否适应这个世界。
天主教教导我们,环绕着我们的世界是暂时的,神子通过对世界法律的屈从取消了世界法律。此世界的王子取得了胜利,他也因此而失败。我们做弥撒便是再一次否定这无意义、寡仁慈的世界;我们所进入的是一种以善、爱、宽恕为要的境界。
如果去做弥撒必须具备坚定的信念,必须具备一种觉悟,即我们生命中的所作所为符合宗教对我们的要求,那么所有热衷于去教堂的人都配得上“伪君子”和“法利赛人”的称谓。事实上,坚定的信念是一种稀有的礼物,至于做礼拜这一行为,它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因此,去教堂的并不就是上帝的选民。
是否去教堂做礼拜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对于教义问答手册的了解,甚至对于所谓信念之真理的稔熟,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尽管它们不无益处。
CITY(城市)。我对城市这一现象想得很多,但不是想那种愚蠢的口号“Miasto, masa, maszyna”(“大都会、大众、机器”——波兰先锋派的口号)。我曾经生活在其大无比的大都会,巴黎、纽约,但我的第一座城市却是一座外省的省城,与一座村庄几乎没有不同,当然,还是有所不同。正是那座城市为我的想象提供了材料。我可以想象出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其他城市则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启蒙时期或浪漫主义时期的维尔诺。那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从下水道一直流到道路中间的污水,人们不得不穿行其间的尘土,不得不蹚过的泥泞。但是上流社会的男女(我是不是最后一个听到过人们在日常语言中说“阁下”这种词的健在之人?)并不是搬到城里去度过晚年,而是住到了他们在安托考尔(安塔卡尔尼斯)的庄园里,因为他们觉得在那儿能享受到居家的自在,而且不必走远路去参加每日弥撒。四十座教堂钟声大作之时,无数妓院中的女人们正在接待官员和学生——也就是说,事物无分高低,一切同时进行,而不是像回忆录中美化的那样。当然,法国士兵在大教堂广场扎营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那帮人穿着最奇怪的服装——什么都穿,斗篷式长袍、十字褡,仅仅是为了多少能挡点风寒。瘟疫肆虐之后,有了露天医院和数千具掩埋的尸体,然后是某种安宁的回归。教授们会去巴克什塔街上作为共济分会据点的罗默家族的宅第,开始出版《街道新闻》。在紧邻圣约翰塔的犹太区狭窄的小巷里,犹太人也在忙着自己的事:面对来自南方的哈西德[8]分子对律法章句显示出的不恭,伟大的加翁[9]发起了斗争;他保留着对于瓦伦汀·帕托茨基[10]的记忆,后者是一位正直之士,先在阿姆斯特丹改宗犹太教,后被烧死在维尔诺的火刑柱上。加翁也讲述军官格拉代(Gradé)的故事。这位军官隐藏在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里。加翁讲到他怎样从伤病中恢复,决定成为一名犹太人,他行了割礼,打算娶这家主人的女儿为妻。这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位将成为意第绪语诗人。他就是海姆·格拉德[11](Chaim Grade),系“年轻维尔内”[12]小组成员,与我们的“灾祸派”关系友善。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是活的,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今天、昨天、前天,同时存在于城中,连1655年也是如此——人们在多明我会教堂的地下室下面发现了大量骷髅,骷髅们身着古波兰贵族外罩袍(kontusze)和丝绸长袍,这证明俄国军队在短期占领维尔诺期间进行过大屠杀。1992年也依然存在,那是我离开五十二年之后重返维尔诺,我写下一首关于穿过一座幽灵城市的诗。
就像那些西里西亚[13]的城市,维尔诺历史上一直摇摆在两种文化之间。首先是旧罗斯,也许是从诺夫格罗德(Novgorod)来的商人们在此定居。他们用木头建造了相当数量的东正教堂,现已荡然无存,很有可能是被焚毁的。维尔诺过去的名字是维尔纳(Wilna),源自小小的维尔纳河。我年轻时这条河被称作维伦卡(Wilenka)。当杰代米纳斯[14]由特罗基迁都至此时,城市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因为大公的子民主要是东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尤其因为古白俄罗斯语为官方文献用语,而且《立陶宛法规》(Statuty litewskie)也以该语言写成。但是,自从立陶宛统治者受洗之后,城市变得越来越罗马天主教化。教堂先是盖成了哥特风格,后来又盖成了巴洛克风格。这表明了波兰对它的影响。维尔诺以及周边地区的波兰化贯穿了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它与开始出现的俄罗斯化发生了冲突。维尔诺郊区的村民已渐渐从说立陶宛语改成说波兰语,但如果立陶宛始终是一个苏联共和国,很有可能他们会接受俄语。我不应该隐瞒我对东方的恐惧。在我脑子里,东方的形状有如一个深不见底的陨石坑或沼泽地的大旋涡。就此而言,我大概算那个地区波兰人的一个典型。沙皇的历史学家们狂热地出版各种文献以展示这座城市的东斯拉夫特质,如果不是一种绝对的俄罗斯特质的话。但是立陶宛情感的再生和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兴起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与此相似,被称作“简单用语”的当地语言,就像白俄罗斯语和波兰语一样,屈从于俄罗斯化,因为它们都是斯拉夫语言。只有立陶宛语是非斯拉夫语言,[15]还能够做出成功的抵抗。
CONGRèS pour la Liberté de la Culture(文化自由大会)。就此我可以写出整整一本书,但我没这个兴致。毕竟,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所谓“自由派阴谋”的书。这是冷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插曲。情况是这样的,战前,马克思主义在纽约影响相当大,而那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主义者正在活生生地相互吞噬。随着战争的爆发,美国情报机构(战略管理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雇佣了一大批NCL(non-Communist left,或称非共产党左派)的纽约左翼分子。他们明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欧洲。战争一结束,再无人关心共产主义对欧洲人心灵的掌控。随后,OSS的雇员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人(战略管理局更名为中央情报局),并且有采取行动的手段。然而,1950年在西柏林召开的反共大会,其倡议却来自阿瑟·库斯勒[16]。他在30年代曾是著名的维利·明岑贝格麾下一名共产党办事员。库斯勒为明岑贝格的宣传中心干过。现在,在与党决裂之后,在巴黎,他有意要创建一个类似的自由意识形态中心。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和其他一些纽约人支持他。大会在西柏林开过之后,他们决定将中心总部设在巴黎,并为它取了一个法文名称。所以说,“大会”(le Congrès)是那些经历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头脑搞出来的东西;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头脑,才明了斯大林体制的危险,因为他们是西方唯一一批一直渴望了解共产主义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简而言之,大会主要是由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创立的。约瑟夫·恰普斯基[17]和耶日·杰得罗依茨(Jerzy Giedroyc)参加了柏林的成立大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对大会早有了解。
当时无人知道是谁向大会提供的资金。人们传说掏钱的是一些大商人,而他们也确曾到场与会。但是到了1966年,有关中情局参与此事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而那几个商行原来不过是走前台的。不管怎么说,大会在巴黎的运作,能让人闻出大把金钱的味道,并且这味道只来自不远的地方。而法国人一门心思沉浸在他们的反美情绪中,完全拒绝参加大会。
如今回顾此事,我必须说,“自由派阴谋”是必需的和正当的。苏联人曾花费天文数字的金钱用于宣传,而大会是对于这种宣传的唯一抗衡。大会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报刊:在巴黎出版有《论证》(Preuves),由瑞士人弗朗索瓦·邦迪(Fran?ois Bondy)主导编辑方针,在伦敦是《冲突》(Encounter),在澳大利亚是《象限仪》(Quadrant),在罗马是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和尼古拉·恰罗蒙特[18]编辑的《当代》(Tempo Presente),用德语出版的是《月报》(Der Monat),用西班牙语出版的是《万花筒》(Quadernos)。他们想把《文化》杂志也纳入这一网络,但被杰得罗依茨所拒绝,尽管加入网络能够缓解他的财务困难。
在这伙人中我感觉很别扭,因为我太压抑,太痛苦,最要命的是,我太贫穷。贫穷一眼就能看穿富人将自己包裹其中的脂膏肥油。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拿着高工资,他们是巴黎的有钱人。也许到今天,我对迈克尔·乔塞尔森[19]的看法会更公平一点,那时候一切都靠他。可我当时不喜欢他的自以为是和他的雪茄烟。那些人对他们自己的错误总是健忘的。错误之一便是将他们奢华的办公室开在巴黎最昂贵的地段,蒙田大道。我同大会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清此事,我想补充一点,即美国人曾拒绝给我这么个人发签证。当然,对这件事大会不需要负责,尽管如此……
要说乔塞尔森缺乏坚定的信念,那是毫无根据的;正相反,作为大会的主管,他把他的生命都献给了大会。此人不简单。他生于塔林(Tallinn),父亲是一位说俄语的木材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一家移居德国,那是俄国侨民的一个大据点。他在那儿上了大学,然后有几年,他成为了巴黎一位成功的商人。此后他又移民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于战争期间入伍。他能流利地讲四种语言;我相信他也懂波兰语,但他不承认。我后来发现,他为了不得不装扮成另一个人而不是做他自己,承受了巨大的折磨。参与大会的欧美学者和作家来来往往,不知道是谁花钱资助他们,而乔塞尔森则被禁止泄露任何内情。出于自己兴趣的需要,他在写一本有关拿破仑战争中俄国军事领导人巴格雷申(Bagration)的书。这使他得以将兴趣集中在俄国,并且在一位被羞辱的英雄身上找到认同。他的心脏也出了毛病。离开大会以后,他定居日内瓦并在那里死去。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康州河谷)。我第一次迷上康州河谷大约是在1947年,当时我是去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做一个讲座。我在维尔诺的教授曼弗雷德·克里德尔曾在那里短期执教。附近农村里住着许多波兰人。在爱尔兰人开始移居到大城市以后,波兰人便填充进来。我第二次去那里是因为我的朋友珍妮·谢龙科(Jane Zielonko)在那所学院教书。多年以后,我在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教过一学期书,住在约瑟夫·布罗茨基家里。每一次到那里,我都置身于秋日的辉煌,难以形容的多彩的叶簇——正因为此,那座河谷对我而言始终是天堂,有醒人的寒冷和不同层次的金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克里德尔、珍妮、约瑟夫——他们如今都成了幽灵王国的人。不久,托拉·伯加卡(Tola Bogucka)也将加入到这些幽灵当中。我曾在克拉斯诺格鲁达[20]爱上过她,再在北安普敦遇上她时她已是一名精神病学家。
CRUELTY(残酷)。在本世纪波兰知识界的文化特征中,有可能存在一种对恐怖笑话和黑色幽默的趋好。这应归因于发生在欧洲某地区的历史事件。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出现在像《大头针》(Szpilki)这类杂志或卡巴莱酒馆里的幽默,都颇为残酷。诗人雅努什·明基维奇(Janusz Minkiewicz)和什维亚托派乌克·卡尔皮尼斯基(?wiatope?k Karpiński)是表现这一特点的佼佼者。在战争岁月里,习以为常的搜捕和处决、人命的不值钱,都加强了这种倾向。各种讲外国人的滑稽段子,很可能与人们的缺乏理解以及某种反感心态相符合。当然,我们也不该忽略西方文学和电影中的虐待狂因素对我们的显著影响,这与市场催生的对惊世骇俗的趣味不无关系。就在战前不久,放映过一部萨查·基特里[21]的电影,开场是一个送葬场面:十一二口棺材走在前面,后边跟着一个孤零零的男孩,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幸存者。除了这个男孩,他们一家人晚饭时都吃了有毒的蘑菇。而这个男孩是因为干了坏事,被罚不准吃饭。不过,当南斯拉夫导演马卡维耶夫[22]将摄自卡廷惨案[23]遇难者尸体的真实照片用进他的超现实风格喜剧片时,他就做得太过分了。
《等待戈多》在巴黎初演时,观众看到波佐折磨他的奴隶“幸运”(Lucky)便爆出笑声。坐在我边上的哲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被惹恼了:“他们在笑什么?在笑集中营?”
由于感同身受而导致的描述的加强;出于对残酷世界的报复而进行的强化描写——这二者之间边界何在?萨德[24]侯爵小说的核心不正是这样一种报复心态吗?我怀疑我自己深受波兰人对于恐怖笑话的轻薄心态的影响,我想我得找个法子治好这个病。
在维尔诺的学生和文学圈里有一位著名的年轻人,长相英俊,出身殷实之家,在北方布拉茨瓦夫地区(Brac?aw)的某个地方世代拥有土地。他甚至自费出版过一个剧本,印刷精美。碰巧那是在苏联军队开进维尔诺不久,而立陶宛刚刚结束了它的中立,我们三人——他、他的美丽的妻子,还有我——坐在一起左思右想:走还是不走?走,就要冒巨大的风险。不走,就是成为苏联公民的命运。我决定越过边界,虽然如果不是扬卡在华沙,我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会害怕。而他们则留了下来。
雅努什·明基维奇(Janusz Minkiewicz)靠着表演他的“悍妇”(Xantippe)卡巴莱在维尔诺活了下来,他回到德国占领下的华沙以后,根据上面这一对的经历编了段恐怖笑话,在地下文学夜间聚会时读出来逗笑。不曾经历过苏联统治的人不能真正体会那种巨大的恐惧。因此,勒谢克·B.为了逃避流放而决定去工人文化补习班上讲马列主义,在他们听来或许实在可笑,因为勒谢克对马克思根本就摸不着门。他被约瑟夫·马茨凯维奇[25]写进了小说《通往乌有乡之路》。约瑟夫以他为例讲述当时人们都用了什么法子活下来。雅努什·明基维奇将此故事进一步演绎:德国人来了,勒谢克声称自己是白俄人(没人知道这是否属实),还得到了一处房产。此后他就拿着根鞭子到处转,并且威胁农民:“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共产主义!”(还是没人知道这是否属实。)他吃晚饭时被人从窗外开枪打死了。谁开的枪?从小说中看好像是农民干的,但当时在那个地区活跃着一个苏共武装小分队,很厉害,人们也可以怀疑,勒谢克与白俄当局合作,而苏共的人当时正与之战斗。
那些被迫落入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制度掌心的人们,用尽各种办法以求自保。一个人若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就不会容忍将他们的经历用作玩笑的材料。我后悔我曾在某处复述过明基维奇讲的故事,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以便有所挽回。
CURIOSITY(好奇)。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拿镜子折射阳光的事,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好好想过这件事。光线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移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光线便消失了。从这样一种观察中大概可以看出小科学家朝演绎推理方向进步的智力倾向,当然并不一定如此。如此运作的世界会使他完全着迷。说实在的,无论你面向何方,到处都能使你产生相似的惊讶。世界收藏着无数细节,无不值得注意。
如此组织起来的世界妙趣无限;崭新的发现会层出不穷。这就像一次穿越迷宫之旅,当我们穿行的时候,迷宫也在悸动,在变化,在生长。我们独自进行这一旅程,但同时也参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参与各种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的发展,以及科学的完善。驱策我们的好奇心不会满足,既然它不会随时间流逝而稍减,它便是对于死亡趋向的有力的抗拒。不过,说实话,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步入死亡大门时同样怀着巨大的好奇期待,急切地想去了解生命的另一面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好奇的反面是厌倦。没有什么还有待认知,日光之下已无新事——所有导致这一结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被厌倦或病态所左右的。
先生,你能否使我确信,当我们一天老于一天,还会有更新鲜的景象向我们展开,就像旅途中我们每经过一个新的转弯所看到的那样?我能使你确信这一点。一切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还是不一样。毫无疑问,我们是在变老;这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在弃我们而去,我们的听力日渐迟钝,我们的视力越来越弱。但我们的头脑变得敏锐了,这是我们年轻时所不具备的,它弥补了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所以,当头脑也被年纪打败,追随感官沉沉入眠,就更值得同情。
那些由于对知识的饥渴而跨到死亡边界之外的思想者和诗人令我尊敬,令我产生共鸣。斯威登堡的天堂是建立在无止境地获取知识并学以致“用”(usus)的基础之上的,否则皇家矿业协会勤勉的评估员该如何设想天堂?七十岁的威廉·布莱克[26]去世时唱着赞美诗,他坚信——不只是相信,而且还知道——他将被载向永恒的知识的猎苑,那里再不会有能量或想象的荒废。
倘若有那么多人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努力地想要发现、触摸、命名、理解一个有着无数维度的难以捉摸的现实,那么好奇心一定是一种强大的激情。那把我们说成是一张纸上的二维形影的人何其聪明:很难跟平面人解释高于这张纸一厘米、身处三维空间之中的什么东西,更别说存在于其他维度之中的东西了。
注释
[1] 博莱斯瓦夫·普鲁斯(Boles?aw Prus, 1847—1912),波兰文学史上的一位领袖人物,主要作品为四部长篇小说:《哨所》《玩偶》《新女性》《法老》。
[2] 加拉帕戈斯群岛,又名科隆群岛,属厄瓜多尔,被称为“生物进化的博物馆”,保存不少罕见物种,达尔文曾于1835年上岛考察。
[3]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对现代神学、哲学、精神病学等领域均有深刻影响。
[4]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小说家,著有《项狄传》和《感伤的旅行》等。
[5]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l797),英国政治家、思想家,著有《法国革命论》等。
[6]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小说家、社会活动家,著作《人类的命运》获1933年龚古尔奖。二战期间参加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部队的总指挥。
[7]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 1900—1978),意大利记者、作家。曾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31年退党。
[8] 哈西德(Hasidim),希伯来文意为“虔敬者”,犹太教神秘主义团体,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波兰,到19世纪其教徒已占东欧犹太人半数。反对过于尊重律法的传统犹太教,强调普通人内在的神性。
[9] 加翁(Vilna Gaon, 1720—1797),犹太教圣人,犹太法典研究者,非哈西德派犹太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领袖。
[10] 瓦伦汀·帕托茨基(Walentyn Potocki, 1700—1749),犹太传说中的波兰贵族,因放弃天主教改信犹太教被罗马教廷烧死。其生平为加翁传播。
[11] 另见本书GRADE一节。
[12] “年轻维尔内”(Yung Vilne),意第绪语,相当于波兰语的“青年维尔诺”,为了区别起见,译为“年轻维尔内”。
[13] 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西里西亚在中世纪曾先后隶属于波兰、波希米亚、奥地利、普鲁士等国。
[14] 杰代米纳斯(Giediminas, 约1275—1341),立陶宛大公,使该国疆域从波罗的海扩张至黑海,并建造了立陶宛首都。
[15] 立陶宛语属印欧语系的波罗的海语,使用拉丁文字母。
[16]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记者。1931年加入德共,后因反对斯大林主义退出。1940年出版小说《正午的黑暗》,轰动一时。
[17] 约瑟夫·恰普斯基(Józef Czapski, 1896—1993),波兰艺术家、作家、波兰家乡军军官。1939年波兰战役后被苏军俘虏,是少数从卡廷惨案生还的军官之一。二战后流亡巴黎,是《文化》杂志的创始人之一。
[18] 另见本书CHIAROMONTE一节。
[19] 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 1908—1978),美国记者、中情局员工。曾是巴黎文化自由大会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络员。
[20] 克拉斯诺格鲁达(Krasnogruda),米沃什的外祖父库纳特(Kunat)家族在立陶宛的庄园。另见KRASNOGRUDA一节。
[21] 萨查·基特里(Sacha Guitry,1885—1957),法国作家、演员、电影导演,生于圣彼得堡。1920年代法国最受欢迎和多产的电影人之一。
[22] 杜尚·马卡维耶夫(Du?an Makavejev, 1932— ),南斯拉夫电影导演、编剧,以六七十年代拍摄的开创性影片闻名,作品饱受禁映非议。
[23] 卡廷惨案,1940年春苏联在卡廷森林对被俘的两万余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等进行的有组织的屠杀。1990年苏方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责。
[24] 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小说家,以色情文学著称。著有《美德的厄运》、《激情的罪恶》等。
[25] 约瑟夫·马茨凯维奇(Józef Mackiewicz, 1902—1985),波兰作家、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员。
[26]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