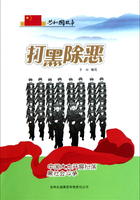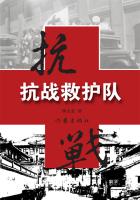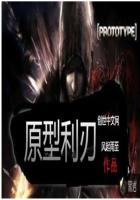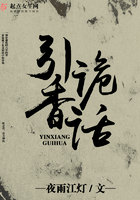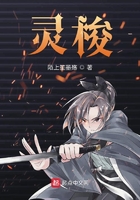FAME(声名)。倘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某个高度俯瞰,那么梦想成名这一人类的愚行就会显得可悲并且值得同情。尽管有人无此弱点,这事还是让我们感到惊奇。很久以前,一个人有可能知名于邻里,知名于乡间,知名于他生活的那个县。那时没有报纸、广播和电视来传播某人的不同凡响,虽然时常也有壮汉、怪人和倾国倾城的美人儿,声名远播至本县以外。比如说,饕餮怪物比托夫特(Bitowt)便在整个立陶宛鼎鼎有名。另一位老爷,帕什凯维奇(Paszkiewicz),或者叫帕什卡(Poszka),名声略逊。他用立陶宛语写诗歌颂他庄园里的一棵橡树,为这棵树取名为鲍伯利斯(Baublis)。不过这棵橡树的大名还真的留传了下来,密茨凯维支将它写入《塔杜施先生》,使之名垂后世。歌谣总能使一些名字成为不朽,即使是那些不起眼儿的希腊小国国王的名字,也因《伊利亚特》而永存。他们往往是些战争英雄,尽管由于荷马我们也记住了海伦和卡珊德拉的名字。
自从个体的人变成亿万大众的一员,并且与大众一样无名无姓,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报纸上、银幕上看到影星和运动员,他感到自己的籍籍无名是一种痛苦。他渴望以某种形式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这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激情,为此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在这儿!”他在一本发行量极小的薄薄的诗集中这样喊道;他写下意在为自己打开知名度的小说;我们或者也可以猜测,那些异常之举,包括犯罪,往往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到行为者的身上。
然而,这种游戏与其说是他与大众人群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他与他身边的环境,他的家庭、同学、所归属的职业圈之间的关系。我不妨在此说说我自己的经验,说说我在维尔诺求学和文学活动的开始。在预科学校,我的作文好像写得还不错,但我已记不得什么了,除了早年间对生物学的兴趣。我也曾在一次文学比赛中获奖,凭的好像是一首十四行诗,但对此,我仍是零记忆。然后是上大学,写作班,“灾祸派”,急切地希望博得同行的赞许。这种赞许是我所需要的。至于那些不懂诗歌的公众,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怎么看呢?我想要得到的是行家对我价值的肯定。我曾将行家这一头衔赠予我的几位朋友。
渴望得到认可是人的基本需要,你可以从这个入手来研究各个不同的社会,问一问人们都用什么手段来确保其雄心的实现——爵位、荣衔、封地、金钱?交战的士兵勇于拼杀,难道不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在自己的队伍中即使不能争先,至少不能落后?
声名的本质在于它虚无缥缈。如果人们说到一个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么这个大名有什么意义?说到底,这就是每一座大城市里的大多数纪念碑的命运;它们变成了符号,而内容却蒸发了。人的数量越多,越能见出声名的专业局限性;这就是说,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会知名于其他天体物理学家,一名登山家会知名于其他攀登过众多山峰的人们,一个象棋大师会知名于其他象棋大师。多元的文明唆使人们区隔成不同的小团体、俱乐部、小圈子、秘密社团的分会、诗歌读者会,甚至更狭窄:俳句爱好者或五行打油诗爱好者、摄影师或皮划艇赛手。当然,诺贝尔奖会带来某种规模的声望,但一个人不应该忘记,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为什么某人会获奖,因为在人群当中,诗歌读者的比例并不大——不同国家的诗歌读者群也只是略大一点或略小一点。
FEDOROWICZ, Zygmunt(齐格蒙特·费多罗维奇)。圆圆胖胖的费多罗维奇是国家党的活动家,在战争时期的地下活动中他尤其活跃。他是维尔诺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预科男校的校长。这是一所人文预科学校,也就是说学校教拉丁文。与我们学校教学水平相当的是伊莱萨·奥耶什科娃预科女校,也偏人文,还有莱勒维尔男子预科,不教拉丁文。与这些学校几乎同样孤高排外的,还有教会创办的学校——耶稣会创办的男校和拿撒勒修女会创办的女校。那些以密茨凯维支、斯沃瓦茨基和爱泼斯坦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排名较差,还有那些不以波兰语而以意第绪语或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以及一所教立陶宛语、一所教白俄罗斯语的学校,排名也靠后(后者作为“共产主义的温床”不断被停课整顿)。
对我来说,旧时的维尔诺不仅是一座记忆之城,而且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政治问题。当年的童军活动被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支配。有两支著名的童军——黑十三团和天青第一团。我非常急于参加天青第一团。我通过了考试,得到一枝金百合[1]。我年龄虽小,却具备了成为一位好公民的一切条件。但是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维尔诺,我感到非常惊讶。1919年,整个城市弥漫着天主教和爱国主义氛围,到处回荡着钟声,欢迎波兰枪骑兵把它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2]人们感激毕苏茨基,在中立陶宛共和国[3]时期还投票并入波兰(犹太人和立陶宛人没有参加公民投票)。作为一名温和派民族主义者,费多罗维奇的活动并不突出,那是毕苏茨基的追随者得势的时候。这一点从他们的新闻喉舌,保守的《词语》报和开放的《维尔诺信使报》就看得出来。民族主义者的《维尔诺日报》发行量较小。
这座城市已经习惯了“被困孤堡”的状态,人们最看重的是一个人是否忠心,是否时刻准备着参加英勇的战斗。事实上,在德国占领期间,爱国主义教育和童军运动就在不屈不挠的地下抵抗组织中结出了果实,这也导致苏联军队进城之后开始大搜捕,并在泊那里[4]处决了大批犯人。一座“被困孤堡”的心理状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一门心思总想着敌人,到处都发现背叛的行为。敌人被一一确认,根据敌对的不同程度,有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还有犹太人(因为他们1919年的时候向着俄国人)。
城市的武装力量是家乡军。这支军队捍卫的是1939年以前的波兰疆域。当它发现包括盟军在内无人承认其战前的边界时,便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地方主义者”被指控为叛国贼,因为他们竟敢提醒人们这块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他们这样做,是要抹去“永恒的波兰维尔诺”的形象。
1936年对《不拘礼节》(Po prostu)杂志一干人等的审判造成了城市舆论的分裂。这伙人脱胎于“灾祸派”集团。大多数右翼分子指责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实际上,波兰共产党一直小心监督着《不拘礼节》杂志)。
在立陶宛当局控制城市以后,[5]约瑟夫·马茨凯维奇的《每日新闻》报又被指控曾与占领者合作,因为他忠于“地方主义”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后来针对这位作家的诽谤指控(说他与德国人合作)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出自最初对其背叛的猜疑。但是地下“民族主义者”费多罗维奇与奥霍茨基(Ochocki)坚持指控,不肯罢休。
《每日新闻》并非立陶宛当局治下唯一一份波兰语报纸,同样出版的还有《维尔诺信使报》,它被认为是波兰的喉舌。该报编辑卡齐米日·奥库里奇(托马什·赞共济会分会会员)头脑开明,后来去了伦敦,编辑责任就落到了我在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的同学、绰号“黑铅”的约瑟夫·斯维齐茨基(Józef ?wi?cicki)的头上。他后来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一个劳改营并死在那里。在费多罗维奇之前出任过我们预科学校校长的是热尔斯基(?elski),我相信他与费多罗维奇持有相似的观点。许多毕业于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的学生后来都出了名。我应该列出其中几位的名字:切斯瓦夫·兹戈热尔斯基(Czes?aw Zgorzelski),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波兰文学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马(Stanis?aw Stomma),一位天主教记者和法学教授;托罗·戈卢别夫(Tolo Go?ubiew),一位小说家;扬·梅什托维奇(Jan Meysztowicz),著有数部有关20世纪历史的著作;小说家塔杜施·孔维茨基(Tadeusz Konwicki);以及这部词典的作者。
FEUER, Kathryn(凯瑟琳·弗尤厄)。一位研究俄国的学者,我在伯克利的同事。她主要讲授托尔斯泰,是一个聪慧、和蔼、为人着想、富于学院气质的人。她出身于一个说法语的加拿大家庭,因此也就是一个天主教家庭。这种家庭出来的姑娘怎么会研究上了俄国?首先,她不得不反抗其家庭和教区,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面向东方眺望黎明。我并不确定她脑子里的幻象是何时消亡的——是因为莫斯科的肃反还是因为希特勒-斯大林协定?但是她的方向既定,就意味着去研究俄国文化,写一篇硕士论文,学习这种语言,并在某条路的某一段上认识了她的马克思主义丈夫,路易斯·弗尤厄。丈夫的思想随之很快发生了剧变,追上妻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然后拿到博士学位,并在伯克利为他们夫妇两个人都谋到了教职,他自己成了社会学教授。他们俩真是一对可怜的反抗者,像吉卜赛人一般,却被准予从事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在伯克利当教授。他们不习惯稳定的家庭生活。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路易斯会胡乱捣腾他们的壁炉设施。这是我去拜访他们时发现的。依我之见,生炉子是一门知识,应该用专门的东西引火,然后把木柴架上去,可路易斯在炉膛里烧报纸。
凯瑟琳对苏联体制了如指掌,并且强烈关注生活在那骇人听闻的专制体制之下的奴隶们。她和路易斯读过《被禁锢的头脑》的英译本,完全理解这本书,因为,可以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们。我不知道我其他的教授同事们如何看待这本书,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这本书。格列布·彼得罗维奇·斯特鲁韦(Gleb Petrovich Struve),巴黎一位俄罗斯侨民活动家的儿子。他与苏联现实从未直接打过交道,尽管作为曼德施塔姆[6]诗歌的出版者,他熟悉这些问题。对俄国人你不能一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当校方在考虑要不要给我终身教职时,学校里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要是说,《被禁锢的头脑》的写作目的在于为左派辩护。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将亚历山大·瓦特请到伯克利来的主意出自斯特鲁韦。他在牛津大学一个研讨会上见识了瓦特的魅力。不过,斯特鲁韦不是唯一的倡议者。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凯瑟琳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她对瓦特极其上心,而我也帮了点小忙。瓦特旅行起来有困难,因为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有不适。名义上,他是由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邀请来的。当时的主任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对瓦特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是他想到要为瓦特的谈话录音。
1968年“革命”期间,凯瑟琳和路易斯离开了伯克利,因为路易斯所在的系视他为一名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嗤之以鼻。其他几所大学雇用了他们。他们最终落脚在弗吉尼亚大学。我去那儿拜访过他们。
凯瑟琳已经过世,但我经常想起她,她是一个结合了智力与善心的人——我们还能向一个人要求什么呢?大概这种结合不可能不受惩罚,因为我觉得她并不快乐。我并不是在这里分发月桂花环,所以我不会略而不提她酒喝得很厉害(我经常陪她喝)。她后来发展成酗酒,直到生命的终结。
FRANCE(法兰西)。对法兰西的热爱塑造了我生长其中的文化,尽管这种热爱不是双向的。或许这种不平等被部分地遮盖起来了。只是渐渐地我才相信,我这一部分欧洲在法国人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这一点得到了阿尔弗雷德·雅里[7]的简单确证,他在剧本《愚比王》里借愚比王之口说:“在波兰,那就是说在乌有之乡。”
在学校里,我们被灌输拿破仑的传说和朝圣者们的浪漫主义。实话讲,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那些来自农业国家的不幸的朝圣者是多么孤绝。就像他们的后继者,一些在灵魂里珍视弥赛亚神话,肉体却奔赴里维埃拉或蒙特卡罗度假的地主。法国像一块磁铁般吸引着知识界的势利眼。法国——不是德国,不是意大利,不是英国——是西方文化的同义词。正因如此,1940年法国的失败给被占领的华沙带来了天大的沮丧,这被解读为欧洲的终结。这难道不是欧洲的终结吗?欧洲重建所需要的力量是欧洲所不具备的。
我为我的西方式的势利眼感到害臊,但我是这样被教育成人的。在巴黎的两次逗留弱化了我心中作为文学和艺术国度的法兰西的形象,同时强化了另外一个形象,即,在这个国家,每个苏[8]都要被算计到,流大汗的波兰移民劳力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有一首诗写的是勒瓦卢瓦-佩雷这个地方的失业者的工棚。不过,不论那里的条件如何,我对法语的熟练掌握在30年代后期和战争期间对我的阅读还是至关重要。在我的文学圈子里,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书的影响力不容置疑。在拉斯基的马里坦爱好者圈子里正好有个人,我想,是玛丽亚·恰普斯卡,我从她那儿得到了一份马里坦的《穿越灾难》(à travers le désastre)这本书的打字稿。这是马里坦到美国后写的东西,由人从荷兰偷带过来。该书旨在反对与德国人合作,支持戴高乐和自由法兰西。我翻译了这本书,1942年以《沿着失败的道路》(Along the Roads of Defeat)为题,地下出版了个小开本。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我捍卫了遭到德国人污辱的法兰西荣誉。我应该为此获得荣誉军团勋章,尤其是因为巴黎午夜出版社的法文地下版比华沙版晚了一年半或两年。
我提及此事是为了弱化人们对我反法态度的印象。我无意掩盖一个事实,即我隐藏着一份受过伤的情感。这份情感产生于战后岁月我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的存在。即使法国知识分子后来承认他们犯了巨大的政治错误,我的态度也没什么两样。他们错误的程度使我不再相信任何后来的“主义”,如果它们源自巴黎。
那么,人们是否应该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法国人的观点),即法国对于非法国人来说会是一个精彩的国家?我对这个国家怀有一种矛盾心态:由于个人生活的剧变我曾被踢到一边,但我对法国文化又心怀感激,同样使我心怀感激的还有几个人,外加巴黎的几条街道和几处风景。
FRENCH(法语)。我是一个见证人。那是几十年前我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一开始,上流社会的人都能说点儿法语,哪怕只够在仆人面前交流以免他们听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里,大学预科学校开设法语课和德语课,由学生们任选一门。不用说,我选了法语。在文学方面,两次大战期间,人们还是将注意力放在法国上,尽管青年一代的法语水平已经变得可疑,而且也不那么容易弄到书。本质上,法语出版帝国——那些沿着伏尔加河、多瑙河和维斯瓦河售卖的黄色封皮小说——在1914年便走向了终结。
一次大战以前巴黎作为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这里是美国那些自我放逐的文学家、艺术家首先落脚的地方,也是波兰艺术家、文学家落脚的地方。可以把“巴黎波兰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名单视作一个不存在的学院选举出来的院士名单。应该有人做个调查,看看“小小绿气球咖啡馆”[9]在多大程度上照搬了巴黎卡巴莱歌舞厅的形式。在德国占领期间,雷昂·席勒[10]和泰奥菲尔·特奇尼斯基在钢琴伴奏下唱给我们这帮人的歌,用的是法国旋律。其中一首著名的歌曲如此唱道:
大风窗外笑,
妈的,生活已烂掉。
还喝吗?不喝了,
我要重新做人在清早!
博埃(Boy)的翻译是法国文学在波兰影响的最高成就。两次大战之间的诗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1]经由亚当·瓦吉克(Adam Wa?yk)的翻译获得了声誉。那些诗歌催生了这样一些诗人:约瑟夫·切霍维奇(Józef Czechowicz)、安娜·斯维什琴斯卡(Anna ?wirszczyńska)、米沃什——这还不算克拉科夫的先锋派。
我在学校里法语学得不算上心,但课本引发了我的好奇,使我受到影响。我在其中发现了约阿希姆·杜·贝莱(16世纪诗人)的一首诗。我非常喜欢,便以这首诗为榜样写起诗来。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模仿的是利奥波德·斯塔夫[12]的诗歌。
只是到后来,到1935年春天,在巴黎,我才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这种语言。那时每天早上,我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去位于拉斯帕伊大街上的法文协会上课。那是一所正规学校,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对像我这样报了cours supérieur(高级班)的学员。语法讲解,听写,文学讲座。几个月后有一次高难度的笔头考试,然后是一个名头过于响亮的毕业证书。过了这一关,一个人便有了在学校里教法语的资格。这样折腾一番对我很有用;我后来意识到,我是我这一代作家中极少数通晓法语到这种程度的人之一。这对我的阅读好处多多。作为《南方手册》[13]月刊在波兰的唯一读者,或几乎是唯一的读者,我得以了解晚近的文学发展。不过,最使我受益的还是对法国宗教哲学家,比如路易·拉韦尔及其他神学家的阅读。他们的散文保留了那种古典的平衡与清晰,这是为法文协会的教师们所称道的。不过很快,学者和哲学家们的法文便屈服于一种惊人的快速转变,好像要因此印证法语在欧洲崇高地位的丧失。法语的文风变得含混,缠绕,充斥着专业术语,攀升到胡言乱语的高度,而胡言乱语是声望的保障。
华沙的法语学院开在斯塔什茨宫里,毁于德国人的炸弹。我和斯坦尼斯瓦夫·迪加(Stanis?aw Dygat)受雇从瓦砾堆中拯救图书,这更大规模地增加了我的法语阅读。这种阅读大概应和了贡布罗维奇在旺斯说过的一句话,他总是习惯性地把话题引向哲学:“奇怪,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
我会选择1938年作为每一个华沙人都开始学英语的年头。法语的时代,就像此前拉丁文的时代,从1914年开始,经过短暂的反复、间歇,终于在欧洲走向了终结。把这种转变解释为Zeitgeist(时代精神)的一时兴起,要比归因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军事支配容易得多,而这种支配就要到来。
FROST, Robert(罗伯特·弗罗斯特)。他被尊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我写他不是出于崇敬,而是因为我惊异于这样一个人物居然成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国家怎能产生三位如此不同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罗伯特·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生于1874年,是保罗·瓦莱里(1871)、利奥波德·斯塔夫(1878)和博莱斯瓦夫·莱什米安(1878)的同代人,前后差不了几年。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他的知识结构已经成形。那时的美国远离欧洲,而欧洲的文化之都在巴黎。我可以用比较的眼光看待弗罗斯特,因为,正如我所说,我了解那些与他完全不同的诗人——法国诗人和波兰诗人。不只是欧洲人视美国为一个肤浅的物质主义的国家;她自己的公民也这样看。如果他们看重文化的价值,他们的目光便充满渴望地越过大西洋。当弗罗斯特还是个年轻人时,他也在伦敦待过几年,在那里出版了《波士顿以北》(1914)。这本诗集也为他在美国赢得了认可。但他整个非凡的生涯,是在他回到那金色小牛皮一般的土地上之后建立起来的。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改变了服装,戴上面具。他把自己弄成个乡下人的模样,一个新英格兰农民,用简单的口语化的文字写他身边的事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在地里挖土,没有任何大城市背景!一个自力更生的天才,一个与自然和季节打着日常交道的乡村贤哲!依靠他的表演和朗诵才能,他小心维护着这个形象,投合人们对质朴的乡村哲学家的喜好。他的朗诵总是吸引大批听众。在他的暮年,我亲眼见过这位吟游诗人:蓝眼睛,刷子般坚硬的白头发,体格坚实,他的坦诚与质朴应该得到倾心和信赖。
事实上,他完全是另一种人。他的童年是在旧金山而不是波士顿郊外的农村度过的。在他谋过的不同生计中,他也曾在新英格兰经营过几年农场——那是白人在美洲大陆殖民的最老的一片土地。他感受那里的风光、乡民和语言;他了解他们的工作,因为他自己就干过那些活计——除草、挖地、伐木。不过,他的读者欣赏他诗中的田园风味,而这仅仅是他的假面。假面之后隐藏的是对人类命运的灰暗的绝望。
他具有强大的才智、非凡的理解力,熟读哲学。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竟能将自己的怀疑主义隐藏在始终摇摆矛盾的态度背后,因此他的诗歌是以一种和蔼的智慧加以欺骗。法国诗人会怎样读弗罗斯特?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有趣——比如说,保罗·瓦莱里。瓦莱里大概会对那些由一个,你知道的,由一个笨蛋、一个牛仔笔录下来的那些来自日常生活的小戏剧故事嗤之以鼻。与此同时,人们得记住,不论两位诗人的意愿与知识如何,他们都与当时的语言状态和语言趋势相连,只不过在法语中这一趋势是自上而下,而在美国英语中,是自下而上的。
弗罗斯特曾热情地阅读达尔文,与19世纪的科学世界观进行过内心斗争。注意,达尔文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了解他的发现对其同代人的影响。对弗罗斯特而言,这就意味着与爱默生决裂,与美国人所持有的大自然具有良善之力的信念决裂,并接受仅由机遇导引的个人生活的虚妄本质。这即是说,他仔细思考过进化论,并且借鉴了他对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阅读。但我不想探究他的哲学。我想说的只是,莱什米安的诗歌也具有一种类似的怀疑主义的基调,而他谣曲般的质朴也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内质则不同。他那些神明和另外的世界,是对虚幻的摩耶面纱[14]的有意描述。保罗·瓦莱里同样具有怀疑论世界观。他设法营建出自我创造的头脑,这头脑赞佩它自己的创造。不过,在莱什米安那里,大自然采用了童话的外观,其中云集着异想天开的生灵,敞开在诗歌想象的宇宙里的,几乎是一座基督教的天堂,这种想象被其自身的美所救赎。瓦莱里用水晶建造的、自主的智识大厦,也是在其完美的诗歌格律中得以终极实现。《海滨墓园》中有几行诗始终与我相伴。那么,我要问,为什么我会觉得弗罗斯特如此烦心和令人沮丧?
不是因为他自我掩饰。他决定要做一位伟大的诗人,无情地谴责他的对手,但他也知道,凭着他的哲学癖好他无法成就其伟大。很简单地,他分辨出了什么将成为他的力量所在:新英格兰乡村和他鉴别出英语口语变体的超级耳朵。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他熟悉的东西上,贴近他那看似如此的地方性。他的诗歌并不抒情,而是悲剧性的,因为他那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叙事诗都是些小悲剧,或者说,它们是描述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说教性的。我觉得这使人扫兴。
将诗歌和隐藏在它背后的诗人的传记放在一起来想想,就会落入一个无底洞。读弗罗斯特的诗歌,谁都不会读到他自己的伤痛和悲剧;他不曾留下线索。他一直对一系列令人惊骇的不幸,包括家人的死亡、发疯、自杀,保持沉默,好像这是对清教传统的确认,因为清教传统要求将私人生活隐蔽在寡淡的门脸背后。这一切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沉浸在他的东西里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独特存在感遭受到了威胁。倘若人类个性的边界流动不定,以至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并且没完没了地尝试新衣新帽,那么弗罗斯特怎么就能一成不变?真正了解他是不可能的,我们只看到他直奔声誉这一目标的坚定努力,以此强行报复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失败。
我承认我不喜欢他的诗歌。我称他伟大,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话,包括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布罗茨基是把他当做一位格律诗大师来看待的。弗罗斯特说过,写自由体诗就像打没有球网的网球。而我,完全站在惠特曼一边。
弗罗斯特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应该补充一点,他不曾弱化人类生活的残酷真相,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而倘若他的读者和听众不明了这一点,那对他们来说更好。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写的是人在面对自然时的极度孤单。这对他来讲完全无关紧要,尽管他也希望得到一些理解的迹象。人不仅在自然中孤单,人孤单是因为每一个“我”都与其他人相隔离,好像他是宇宙中唯一的统治者。他徒劳地寻求爱,而他所认为的回应仅仅是他自己的希望的回声。我引用下面这首诗是因为它也展示了弗罗斯特的寓言方法和说教方法:
它的大部分
他曾经以为他独自拥有这世界,
因为他能够引起的所有的回声
都是从某道藏在树林中的峭壁
越过湖面传回的他自己的声音。
有天早晨从那碎石遍地的湖滩
他竟对生命大喊,它所需要的
不是它自己的爱被复制并送回,
而是对等的爱,非模仿的回应。
但他的呼喊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除非他的声音具体化:那声音
撞在湖对岸那道峭壁的斜坡上,
紧接着在远方有哗哗的溅水声
但在够它游过湖来的时间之后,
当它游近之时,它并非一个人,
并非除了他之外的另外一个人,
而是一头巨鹿威风凛凛地出现,
让被弄皱的一湖清水朝上汹涌,
上岸时则像一道瀑布向下倾泻,
然后迈蹄跌跌撞撞地穿过乱石,
闯进灌木丛——而那就是一切。[15]
注释
[1] 波兰童军的军徽图案为金百合。
[2] 一战期间,维尔诺和立陶宛其他地区均被德国占领;1918年德军撤退后,维尔诺被苏联红军占领。1919年,毕苏茨基的波兰军队夺回了城市。此后,城市的控制权又多次易手。
[3] 1920年,维尔诺市及周围地区成立了中立陶宛共和国。1922年公投之后,整个地区归属波兰,直到1939年苏联入侵。
[4] 另见本书PONARY一节。
[5] 1939年9月,苏联侵入并吞并维尔诺。10月,立陶宛当局同意苏联在其国内设立军事基地,以此为条件换取维尔诺回到立陶宛。
[6]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Osip Mandelstam, 1891—1938),深具影响力的俄苏诗人,阿克梅派诗人代表,曾饱受斯大林体制的摧残。
[7] 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 1873—1907),法国象征主义作家。
[8] 苏,旧法郎的货币单位。
[9] “小小绿气球咖啡馆”(Zielony balonik),克拉科夫颇具传奇色彩的卡巴莱酒馆,文人艺术家频繁光顾的处所。
[10] 雷昂·席勒(Leon Schiller, 1887—1954),波兰戏剧和电影导演、批评家。
[11]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先驱人物。
[12] 利奥波德·斯塔夫(Leopold Staff, 1878—1957),波兰现代派诗人。
[13] 《南方手册》(Les Cahiers du Sud),法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文学刊物。
[14]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不止一次提到摩耶面纱。摩耶(Maya)在梵语中意为“幻”,尼采用以指人类存在其中的表象的现实。
[15] 本诗译文引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弗罗斯特集》(上),第424—425页,译者曹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