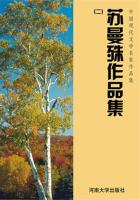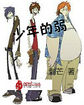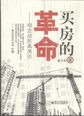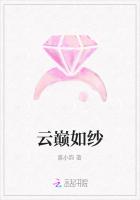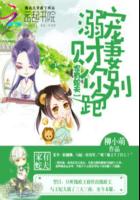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六:石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的农村,谷仍是用石磙碾下来的,米是用石碓舂出来的,面粉是用石磨磨出来的。石磙、石碾、石磨、石碓……不知道出现于何时,但可以想象,它们陪伴人类走过了十分漫长的岁月。
石磙是用来脱粒的。稻谷、麦子、豌豆、胡豆等等作物,就是靠石磙的碾压,籽实才能从禾杆上掉下来,成为粮食。石磙有两种:一种是布条磙,大约两尺长,一头稍粗一头稍细、中间钻有圆孔。另一种是组合磙,由三个厚约五六寸的石饼组合起来,中间亦有圆孔,用木棍穿连起来。
打谷是石磙最主要的用途。一般是这样:人们将从田间背回来的稻子均匀地铺开在稻场(院坝,鄂西一带称作稻场)上,晒到太阳偏西,禾杆枯焦,这时就把牛牵出来,把石磙套上去,让石磙从里到外一圈圈碾压。
石磙在碾压时,相互碰撞,发出砰隆砰隆的声音,稻场上也立刻飘出一种裹着青草味的谷香。石磙碾压一遍。大人们便用杨杈(一种“人”字形的木质工具)把碾压过的稻草翻过来,这时稻场上已落了厚厚一层谷了。
打场一般都在太阳下山之后,往往会持续到夜间。这时月亮升了起来,照着拉着石磙的牛和翻动着稻草的人们。这时候,人和牛以及影子活跃在山村的院坝上,组成一幅充满喜悦和恬静的山村丰收图。而我们,常常会在石磙转过去的时候,大胆而恣意在稻草上追逐、打滚、蹦跳,挥洒着山娃子们快活无拘的野性。
石磨,有大磨和小磨(手磨)两种。大磨与北方的磨略有不同。北方的大磨,磨盘上是一个石磙,利用石磙在磨盘上碾压,而把要磨的东西碾碎;南方的大磨,是两块磨盘,磨盘的一面有密集的磨齿。两块磨盘扣在一起,上面一块中间有一圆孔(俗称磨眼an),粮食从此进入磨中。磨盘的两个方向上装有木桩(磨手),以便和动力联结(马、牛和大磨联结的那些的工具叫做“套”,人一般用扁担、或一种专门磨杠。这算是大磨的附属设施吧)。大磨一般用来磨小麦、玉米,以马、牛或人拉动上面的磨盘。大磨的直径一般在两尺左右,因为要有马、牛或人转动的空间,因而一般摆在专门的房里。这间房被称为磨房。
大磨一般是大户人家的,一般是需要较多的麦面和苞谷面的时候(如过节,过事)。一般农家,只有手磨,必不可少。
推大磨,需要赶磨。所谓赶磨,就是驱赶拉磨的牛、马,或者为它们驱赶那些死皮赖脸追逐着它们的蚊子。赶磨者一般由小孩子来充当,他们手中拿着一匹捶软的棕叶,在牛和马的身后亦步亦趋,时不时往牛和马的屁股后面挥一下。
磨面时一般是一边磨,一边筛。马蹄得得几声响,磨一转动,一股新麦的香味顿时弥漫起来,雪白的面粉像雪一样一片片贴着磨盘落到干净的磨板上,眨眼间整个磨盘下面就出现一道雪白的线,再推几转,面粉一点点增多,慢慢地变成那种像落满了积雪的山峰。这时,头上包着毛巾的母亲或者姐姐就会用撮瓢把面粉撮起来,端到摆在磨房角落里的一只大腰盆前面,倒在事先准备好的络筛里。她们摇动络筛,精细的粉末便落入盆底。
我就赶过许多次磨。现在想起来,它似乎蕴含了某种特定的意味。
小磨的用途更广泛,除了磨苞谷、小麦,还用来“推浆”:譬如磨黄豆打豆腐、磨玉米浆做浆粑粑,磨玉米浆熬糖,梭(剥)谷壳、荞麦壳等等。
小磨的体积小,也是上下两块磨盘,它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架上,人站在一边,用磨抓子(一种“丁”字形的木质工具,它一头放在磨手子里,另一头被推磨者抓在手里)推动磨盘。一边有人坐着,往磨眼里添加要磨的东西(喂磨)。
推手磨需要一定的体力。想一想,我大约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能推手磨了。我记得母亲不断地要我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而我,当时却以自己能推动手磨为骄傲。或许我在显示我的劳力不错。
印象最深的是舂米。大约是过年前吧。姐姐们把谷子用手磨“梭”(将谷壳剥离)了,就大袋小袋的背着去舂。碓是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碗形的碓窝埋在地面以下,一根木梁上绑上一个石柱(俗称碓脑壳),木梁下面有一个支点,人站在碓窝的另一端,踏动木梁,让碓脑壳翘起,落下,翘起,落下……把米舂“熟”(从手磨里梭出来的米粒,表面不白,不易煮。经过碓舂之后,米变得雪白,透亮)。
可能是要过年的缘故吧,我们去舂米的时候,那里等候了很多人。她们(一般是妇女和小孩)在那里说笑。自然就开始了一种劳动的协作。不管是谁的米,都会帮忙踏动木梁。看起来,碓脑壳像一只啄米的鸡……
石器是人类开始时最主要的工具,考古学家从石斧的刃口上判别人类生存的时代。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换一句话说,人类的进步进化,是从利用石器开始的。
直到从石头里面炼出铜、炼出铁,人类才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有了另一种文明。从而,以用从石头中提炼出来的铁器,开始了对石头的雕琢,和土地的征服,开始让人类的生活变得轻松和精致起来……
石器伴随人类行走了几千年上万年,作为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的石器现在却越来越稀少。而以制作石器为生的石匠也已几近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我五月份回到老家,终于打听到村里还有一个石匠。于是租了一辆摩的去了。
当然,在此之前,我曾经搜寻过那些我熟稔的石碓、石碾、石磨等等,可是已不能如愿。现在保存得比较完好的是人们甩在屋前屋后的手磨。而石碓和碾槽、碾盘已难觅踪迹了。
乡村石匠主要就是打制石磨、石碾、石碓、石磙。脱粒机、打米机、粉碎机、干湿磨的出现和普及,石磙、石磨、石碓、石碾已不再为人所用,因此,在我去找石匠的时候,心里想着,他,可能是末代石匠了,或者说是最后的石匠了。
他叫郑光华,我问他现在还打石头吗?他说打。我问打什么,他说主要是打碑,有时候,也给人家打一打建房的水脚石。
打碑,已经是石匠最主要的业务了。这是不是石匠最后的挽歌,是一种无奈的谢幕?
郑光华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学石匠的。那时他14岁,他学石匠的动机很简单,“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因为他们一家五兄弟,家大口阔,生活很困难。他想吃饱饭。
相比其他的手艺人,石匠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的作业点常在野外,同种田种地一样,要受风霜雨雪之苦,而且,还需要足够的劳力和悟性。所以,一般的人,不愿意学石匠。
但郑光华却铁了心要学。他想石匠这门手艺,虽然辛苦,但毕竟比种田的收入高,还且也不会失业。于是,他装了“盒”(一种长约两尺宽一尺的长方形木盘,用以放置礼品,礼品一般以烟、酒、糖、面条、猪腿、鸡蛋等,广泛用于拜师、谢师、求亲等),在盒里放了一套衣裳。
首先就是学劈石头。因为石匠要打制器具,首先要有材料,这跟别的艺人也不一样。别的艺人,材料都是东家自备的,而石匠要自己去取料。因为,只有石匠才能辨认哪种石头可以打门槛,哪样的石头能打磨。这是一方石山,上面长满了荆棘。他们先要把荆棘除掉,然后仔细地辨认石头,是青石,还是老娃石、掉灰石、响班琴(这些都是石匠称呼的石头名称,不知它们究竟是怎样的石头),如果正是他们需要的那种石头,就开始取料。
口诀是这样:“掏三钻,打穴眼(an)”。即,先用钻子打眼,约一尺远一个,把眼打好后,把铁锲子打进去,然后用力敲打铁锲子,让铁锲子把石头“胀”开。
取石头,行话叫做“发青山”。如果是建房取大门料,还要先看看日期,择吉日。
和所有手工艺人一样,石匠带徒,一开始师傅不会教你做什么东西,而是熟悉规矩,干杂活,等干到一定程度了,才让你摸家伙,教你使用工具。
石匠的工具主要有:墨斗、曲尺、五尺、龙骨(装置钻头的套子)、锤子、钢钎、扁钻、小钎子。
墨斗是一种丈量工具,由一个墨盒和一个小转轮组成。墨盒里面装有棉花之类的填充物,让墨汁浸透,转轮上绕着很长的线,线从墨斗中拉出,自然就粘了墨汁在上面。这样,要取材料或将材料取直时,就弹线。将两点固定,把线绷起,然后弹下来,一条又直又细的墨线就落在石头上了。因为石头有时候是黑色的,因此,石匠的墨斗,常常用红色的印油。
曲尺和五尺也是丈量工具,它们更多地用于打制器物的时候,上面有精准的刻度。曲尺的作用是量角,要把方形的器物打周正,必须保证角是直角。而五尺是石匠用得最多的计量工具。相传是祖师爷鲁班所传。传说它可以避邪。走夜路,只要带上五尺,火焰很高,神鬼也要避让。
石匠最多的工具是钻头和铁锲子。它们有很多型号,打制不同的器物或在不同的时间里选用。而小钎子就是雕刀,主要用于在石上雕刻。
石匠的工具并不复杂,但用起来却很费力,因为它的对象是笨重而坚硬的石头。所以,没有摸过钻子的人,一开始,钻子上去是钻不动石头的(他们的说法叫“不巴”),只有将钻子的角度,锤子的力度协调合适以后,钻子才可以按人的意志工作。
郑光华学取石料,学了一阵。很辛苦。可是,为了学到真艺,晚上,他不休息,给师傅家里推磨。师傅觉得他能吃苦,爱钻研,教得很认真了。
开始叫他打门墩(放置于石门槛两头,用于固定门槛和大门枢纽的物件),郑光华好像懂了,抄起家伙打起来。师傅也没怎么管。打好一看,完了,打的“顺风”(门墩像鞋一样,左右各一,开口不同。“顺风”就是没分左右)。师傅气得挝了他两耳光。
石匠的手抽在人的脸上,可想力量是不会小的。郑学华两眼直冒金星,想哭。可是怪谁呢。怪自己呀。自己怎么就不知道门墩是一左一右呢?
这回算是吸取教训了。
石匠除了打磨、石磙、碾子、门槛以外,还有一项业务是钻磨(当地上也称为“蚕磨”),
为什么要钻?一是石磨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磨齿龉了,石匠要通过钻、剔等方法,将磨齿打锐利。二是新磨不合适,上面的磨盘与下面的磨盘不能咬合,不能推东西,或者东西推不烂,或者推起来特重。这都要请石匠来钻磨了。
这是在东家家里进行的。一般而言,东家要为石匠准备丰盛的饭食。所以这是石匠最轻松最喜欢的事情。在缺粮吃的时候,有人供吃喝,有工钱,而且又不需要抡大锤。这就很不错了。
因此,石匠很在意别人对于钻磨技艺的评价。因为当时一个村子里有好几个石匠。只有磨钻得好,才有人找你干。而有时候即使用心也难免出问题。这时,石匠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而会说石头有问题,或者说钻磨那天,有什么高人搞“板眼儿”等等。
搞什么板眼?如果推不出面来,石匠就会说,这磨被别人封了口。
其实,这是钻磨有窍门。有口诀:“一指黑,二指白。”什么意思?是说磨沿的宽度(这当然是指内沿),磨沿两指宽时,磨出来的东西就白,磨沿只有一指宽,磨出来的东西就是黑的。其实道理很简单,磨沿宽,东西放在里面碾压的时候就长,才会细,就白了;窄了,东西碾不碎就落出来,所以黑。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磨推不出面来呢?一是磨沿不能太宽,二是赶齿的走向与弧度。磨齿,不管大磨还是小磨,都是八方齿,大磨一方齿是13~15根,小磨一方是7~9根。大磨有两根赶齿,在磨里被碾压的东西,出得快还是慢,与赶齿有很大关系。如果赶齿的走向不对,东西就不能顺利地出来。
当然,决定磨好不好推还有一些因素,如磨齿的深度、锐度、走向等等。
钻磨是石匠最简单的业务。以此观之,石匠大概也不那么容易当吧。
钢磨(干湿磨、磨面机)普及后,农家用不着再请石匠打石磨、钻磨了。人们不再记得起来石匠了。只有在吃馒头、吃大米饭的时候,才会说起石磨:哎,机械推的面到底没有石磨磨出来的好吃;米也没有石碓舂出来的米香……
那么,郑光华,这个想一辈子吃石头饭,在大山里锤炼出了一身侍弄石头的绝计的石匠,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打碑!
农村立碑(墓碑)的风俗勃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原因是农村因为实现生产责任制,得到休养生息的农民们手里有了一些余钱,也应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吧。
墓碑的材料是石头。因而,石匠有了用武之地,石匠也就保留了下来。要不然,我现在也很难找到郑光华了。
郑光华的房前屋后都摆有一些石料,都是打墓碑用的。他的作业方式是这样。哪家要打碑,就先到他这里来预订。然后他就去取石料,请车运到家里,在房子外面搭个棚子,作为他作业的地方。打碑一般要打七块石头,大约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最难得打的是碑面子。它是墓碑的主体部分。首先,要用钻头把表面钻平,然后磨光。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个人配合。程序是先把碑面摆到一个牢实的木架上,然后用夹棍夹住一大块砂石,几个人抬着大砂石,在碑面来回晃动,一边有人往上浇水。开始用糙石,然后再用细石,直到把碑面磨得光滑如镜。一般地,磨这么一块碑面,需要六个工。
现在,因为有了球磨机,磨碑面就变得简单一些了。
碑面磨好,就能往上面刻字、雕花了。
这时石匠会告诉东家,要刻碑了。但石匠不会急急忙忙刻起来,他要将情况告诉东家。因为有规矩:这时候东家要给石匠封喜钱。
喜钱就是一段“红”(红布、红绸之类)搭在碑面上,或者是一个揩汗的毛巾。
收了喜钱,石匠就会把罩在碑面的东西揭开,请先生在上面写字。写字的先生,可以由东家请,也可以由石匠代请。
先生把碑文写好了。石匠就开始刻了。
郑光华说,刻字是打碑最难的。要靠手里的力度来控制字的轮廓和锋芒。用力要均匀。尤其是不能刻错。一笔错了,又要重新磨掉,再从头来。
还有一个难题是要雕画,就是在上面雕龙刻凤。这不能请人来画。谁会画呢?只有自己学画。郑光华说,为了学这个,他费了不少工夫。
碑打好了,还要立碑。东家会挑选一个日子,把几块碑石都运到事先选好的地点(一般为墓地)立起来。这时石匠就会说几句吉祥的话:“此墓此墓,听我嘱咐,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子孙万代,步步高升,万代发祥。”
这才算把一座碑打好了。多少工钱?八百块钱。
打一座墓碑,三十天左右,八百块钱,每天只有二十多块钱。郑光华说,这是他家庭的主要收入。他一年下来,大约可以打八到九座碑,可收入六千多块钱。
郑光华今年43岁。已经从艺近三十年,是个老石匠了。我问他现在有没有人跟他学艺,他说没有。因为这个事蛮苦,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而且在外面打工,比这强。
我拿起一把钻子仔细端详,似乎看见了原始人在莽莽森林中奔突,拾起石块向前面的一只香獐掷过去,看到他们为了切割香獐的大腿,迷茫地寻找着锋利的石块,用一个石块去打击另一个石块……
当然也会想起打谷场上的嬉闹、舂米时的欢笑、以及那响彻在春夜里手磨的声音……
似乎一眨眼间的事情,从人类用石头去获取野兽野果到石器终于退出工具的行列。
想一想,一种伴随我们走过几千年的东西,就这么没了吗?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2007年8月